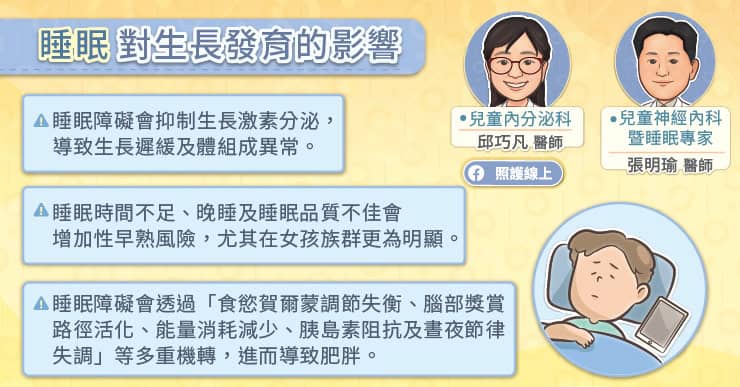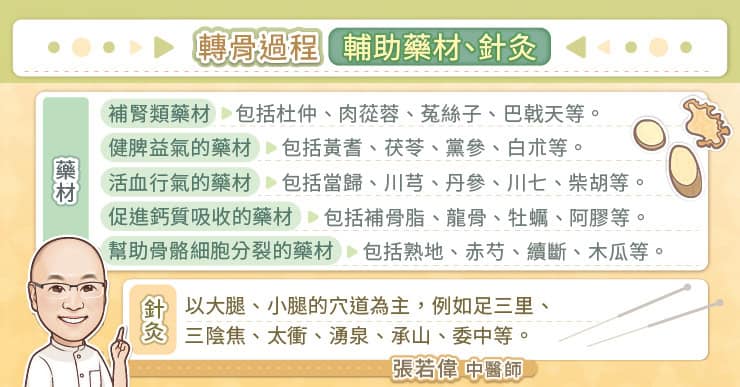- 作者 / 彼得.渥雷本
- 譯者 / 王榮輝
當我們擁抱一棵樹,沒有任何電氣作用發生——因為我們和樹木具有相同的電壓,這是截至目前為止可以確定的。然而,樹木難道不能至少以其他某種方式,來感知人類的觸碰嗎?
它只是想保護自己
有一種可能發生在幼樹身上的現象—— 向觸性形態發育(thigmomorphogenesis),即植物在被觸摸後,生長會變得較為緩慢。舉例來說,只要每天撫摸自己種植的番茄幾分鐘,就會造成減緩增高且形成較粗的莖軸的現象。
風也會在植物身上引發相同的行為模式:較低的高度能降低風作用在根部的槓桿力,此外,較粗的莖也更有益於穩定番茄株。這當然也適用於動物擦身而過時所造成的活動,因為較不穩固的植物便容易因此曲折。因此,番茄或其他小型的樹木很有可能在它們的遺傳清單中,有著對這種接觸(不僅僅是對風)的反應。
科學家發現,被如此觸碰的受試樣本會產生更多的茉莉酸(jasmonic acid)。這種酸不僅會改變高度的增長,還會刺激植物,促使莖條變粗,讓植物更加穩固。特別是太少受到光線照射的室內植栽,往往會有根單薄、不穩固的主幹,這種現象就更明顯。

如果期待擁抱一棵樹後能獲得正面的回應,那麼以上這些資訊肯定令人大失所望。因為,前述的反應其實只是某種防禦策略,用來對抗不利於植物的外部影響。此外,如果樹木得要從中察覺些什麼,必然要能感受壓力,應該要能感受到圍住其樹皮的手臂。一定程度的壓力敏感度確實是有,只不過範圍、大小不盡相同。舉例來說,如果有棵相鄰的樹木或有根金屬柱壓在某棵樹的樹幹上,這棵樹就會開始繞過障礙物生長。不過,所施加的力必須很大,尤其還要持久——人類的擁抱無法滿足這兩個因素。特別是大型樹木,還具備厚實樹皮,這些樹皮在較外圍的區域裡僅由死去的細胞組成,因此所能有的感覺,恐怕和我們的頭髮差不了太多。
如大腦一般的樹根,討厭壓力
相反地,我們倒是能在另一個完全不同的區域找到很多感覺,那就是樹根:樹木會利用具有類似大腦結構的根尖在地底延伸,根尖會觸碰、品嘗、檢查並決定,往哪與如何繼續前行。譬如說有塊石頭擋住了路,感知構造就會察覺到它,從而另闢蹊徑。因此,愛樹者所尋覓的觸感不是在樹幹上,而是在土地裡。如果聯繫能成功,那麼樹根該是第一個位址。此外,樹根還有其他的優點,不僅相對易達,而且有別於樹在地面上的部位,它們連在冬日裡也一樣活躍。只不過,樹根既不喜歡壓力、也不喜歡新鮮空氣;所以,硬把那些脆弱的構造從地下掘出來沒有什麼意義,因為光在陽光下待上十分鐘,就宣告了樹根組織的死亡。

不過,最新的科學知識倒還有其他可供參考的建議,例如樹木的脈搏。脈搏?樹木當然沒有人類的這種心臟,但也需要類似的東西,否則樹木體內最重要的一些流程便無法運作。
樹木也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血液之於人類,正如水之於樹木。關於如何將水運上樹冠,這一切究竟是如何發生的,迄今仍是未解之謎。
任職於匈牙利蒂豪尼(Tihany) 巴拉頓湖沼學研究所(Balaton Limnological Institute)的安德拉斯.茲林斯基(Andrάs Zlinszky)博士,倒是讓這個幽暗的謎團露出一絲曙光。早在幾年前,他就和來自芬蘭和奧地利的同事一起觀察到,樺樹會在夜間休息:科學家在無風的夜晚裡用雷射測量樺樹,發現樹枝下垂達十公分;而隨著太陽升起,樺樹會再度甦醒,研究人員便稱此為樹木真正的睡眠行為。

這項發現顯然讓安德拉斯.茲林斯基大為振奮,因為他又繼續與同僚安德斯.巴弗德(Anders Barfod)研究了另外 22 種不同的樹木。他再次發現到樹枝的起伏,只是節奏會有所不同;樹枝不僅會在晝夜變化時發生起伏,每三到四個小時,也會有所起伏。採取這種策略的原因會是什麼呢?科學家把目光聚焦於水的運輸上——樹木會在這些時間間隔裡進行泵水運動,這合乎邏輯嗎?畢竟,其他的研究人員在此之前已經確定,樹幹的直徑會定期縮小 0.05 公釐,藉以再次擴大。科學家是否發現了某種脈搏的蹤跡,其會藉由收縮將水逐步向上推送?這是不是一種緩慢到我們迄今都未曾察覺的樹木脈搏呢?茲林斯基與巴弗德提出了這種假設,作為對自身觀察的合理解釋,從而也將樹木往動物界推了一步。
遺憾的是,每三、四小時一次的脈搏跳動實在太慢,即便是最最敏感的人,在擁抱樹木時也不可能感受到,因此我們在這裡也不會發現任何可感知的樹木信號。
植物聽得到我們說話嗎?
接下來,我想再仔細觀察一下與樹木聯繫的最後一種可能,那就是:我們的聲音。這是人類最重要的溝通工具,有不少人會嘗試與樹木或自己所栽種的室內植株交談。「嘗試」是什麼意思?意思就是:他們這麼做,而且期望植物能以某種方式回應。此外,也有一些葡萄農會在果園裡播放各式各樣的音樂,而且認為自己知道,哪一種音樂類型有助提高葡萄的產量。
在所有這一切的背後,是否存在真相的核心——植物究竟能否聆聽?

對後面那個問題,我可以大聲地回答:「能!」早在幾年前,研究人員就對阿拉伯芥(Arabidopsis thaliana)做過這方面的實驗。研究結果顯示:阿拉伯芥的根部會依循頻率為 200 赫茲的敲擊聲定向,並朝相應的方向生長,同時也能產生如摩斯電碼般運作的聲響。
豌豆可以分辨聲音的真偽?!
西澳大學(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的莫妮卡.加利雅諾(Monica Gagliano)發現,豌豆可用根部聽到在地底下流淌的水,為此在土地裡埋了三根管子:第一根管子裡只有錄音帶播放出的沙沙聲、第二根管子裡有實際的水流、第三根管子裡則有人為的流水聲——受試植物並未受到愚弄,只會扎根於真正的水上;但如果它們不渴,就不會表現出任何活動。然而,這真的算是聆聽嗎?加利雅諾及其團隊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根部應該確實有受到潺潺聲響的刺激,這也正是他們所觀察到的。
植物(從而也包括樹木)是聽得到的。正如人類,它們也會針對性地運用自己的能力。就像我們之所以很少聽到超音波,是因為我們並不需要,植物同樣也只會去傾聽那些對它們來說重要的事物,例如地下的流水。然而,前面所提到的,那些播放古典樂來刺激葡萄生長的報導,該怎麼解釋?那些和樹木說話的經驗談,又該怎麼說?如果冷靜地進行科學觀察,那麼根部的聽覺能力對此恐怕毫無貢獻,因為它們是埋在地下的,所以相對受到了良好的隔音。因此,我們必須環顧其上的區域,仔細審視樹幹、枝條與葉片,可有任何對聽覺有反應的跡象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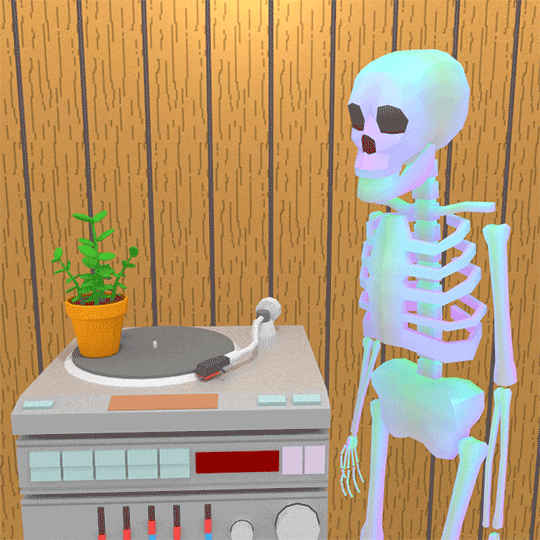
被阿拉伯芥已讀不回
西德廣播公司(WDR)的一個團隊在利希研究中心(Forschungszentrum Jülich),讓向日葵持續數日暴露於不同的聲響下,其中也包括了古典音樂。結果顯示:暴露於不同聲響下的植物之間,並無任何生長差異。也許音樂是錯誤的切入點——應該尋找對植物來說真正重要的聲響。
譬如說毛毛蟲的啃咬聲,又會如何呢?這對綠色植物來說,意味某種致命的危險。這正是美國密蘇里大學(University of Missouri)所研究的主題:研究人員將毛毛蟲置於阿拉伯芥的樣本上,藉助微小的雷射反射鏡探得同樣也讓莖有所震動的那些微小波動。如果研究人員利用這些波動去欺騙其他未受蟲害的受試植物,它們就會產生出在遭受攻擊時,會特別大量產出的防禦物質。相反地,對相同頻率的風聲或其他聲響,受試植物則是「無動於衷」。
所以阿拉伯芥是聽得見的,這也完全有道理可循。透過聲音的警告,甚至可以在一定距離外提前察覺危險,進而做好相應的準備。特別重要的是:它們會忽略不會構成威脅的聲響——這可能包括了人類的言語,還有各種不同類型的音樂。真可惜!要不然,那些報導農作物能欣賞古典樂和搖滾樂的新聞,其實還挺美妙的。
不過,在音樂中是否存在著近似毛毛蟲啃咬的部分,倒是有待釐清。如果真是這樣,那麼這種事情或許就能說得通了;不過,如此一來,莫扎特的音樂就不是被植物所欣賞,而只是遭到誤解罷了!

我完全可以理解與樹木交流的必要性。坐在這些龐然大物底下,撫摸著樹皮,安全感倍增;如果對於我們的存在、甚或我們的觸碰,樹木能有什麼主動或被動的回應,那麼這一切就都圓滿了。我不會否認,這種事情是可能的;只不過,至少保守的科學,迄今對此尚無證據。
不過,即使這是事物的最終狀態,難道一定非得要有個回應不可嗎?難道不會是,人類與樹木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裡?畢竟,在樹木存在於地球上的那些年年歲歲中,我們人類存在的時間僅僅只占了 0.1%。雖然樹木顯然對所有的這一切無感,但反過來說,在人體裡卻肯定會有某種反應;關於這點,我將在後頭進一步的說明。就目前的情況來說,如果我們在與樹木接觸時能有良好的感覺,而且,在最好的情況下,能讓樹木好好過著它們的野生生活,這暫時也就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