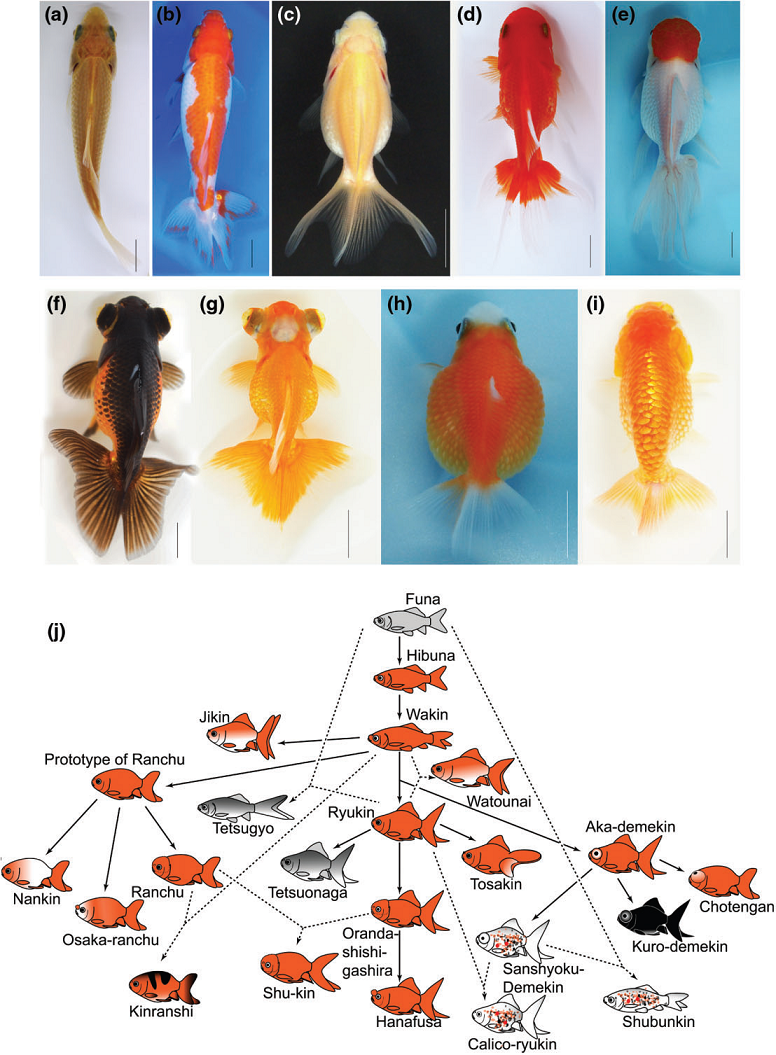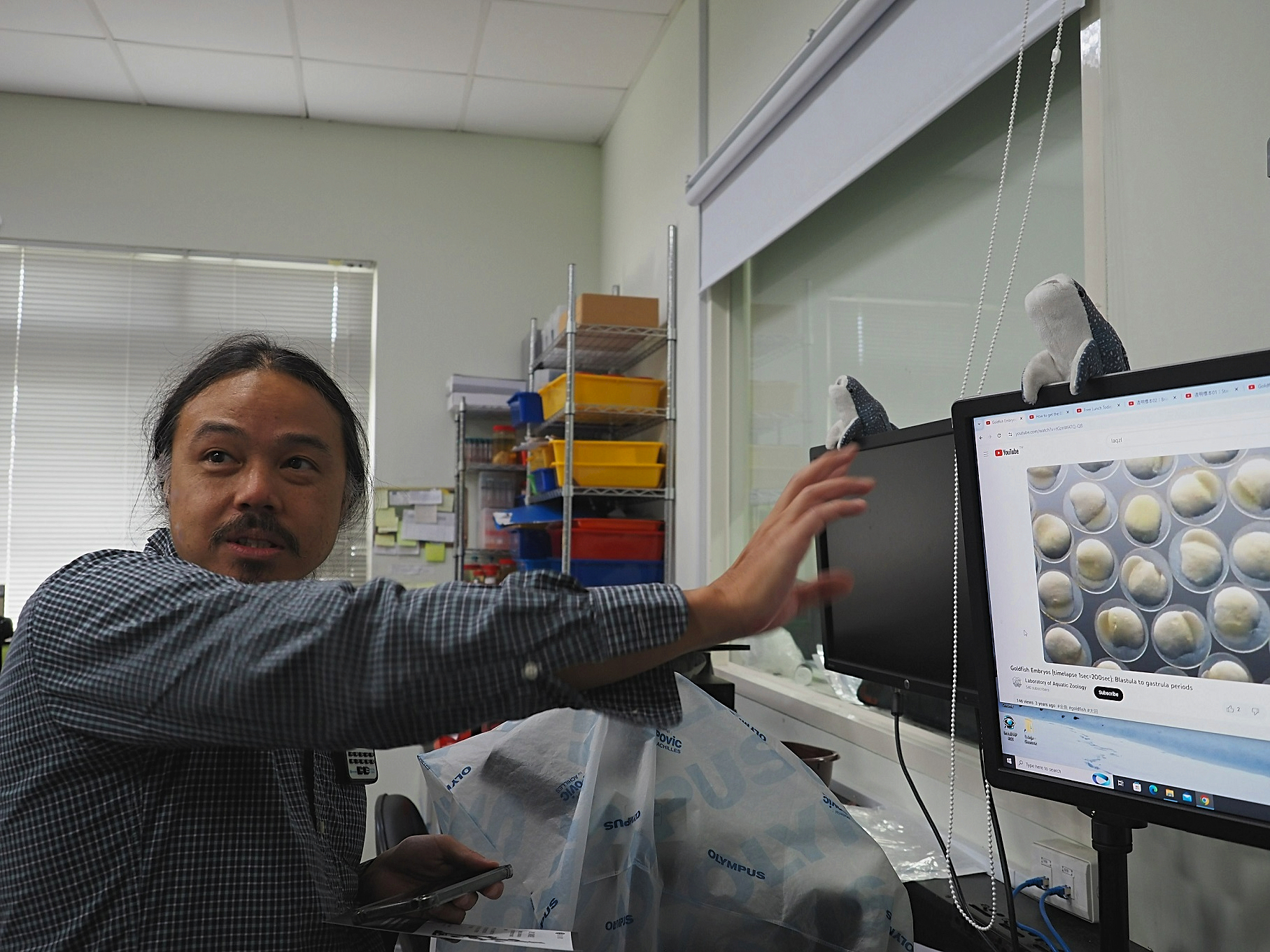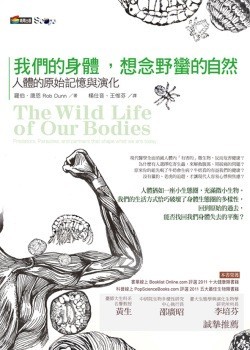
──羅伯‧唐恩,《我們的身體,想念野蠻的自然》
文 / 林書帆
單車提倡人士Dan Burden認為:「人體在先天上並不適合時速超過二十四公里的移動。我們的視覺歷程、理解力與反應力就是單車的速度,高於這速度的活動都違反了人類的演化。而我相信以人類的速度來過生活的人,會比較快樂,這樣的快樂是高速達不到的。」加拿大作家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寫道,人類總是想過更快的生活,以致於把靈魂拋在了後頭。文明與科技的突飛猛進,無非是建立在想要「更快」的慾望之上。
在古生物學家眼中,我們之所以是現在的我們,是六億年來演化的結果,然而人類從第一塊鐵到製造出第一顆氫彈,只花了三千年的時間,從此我們可以說是活在兩個時間軸裡:一邊是演化緩慢的尺度,一邊則是現代文明的突飛猛進。大腦(心智)告訴我們,人類是地球上所有生靈的主宰,但身體卻沒有忘記野蠻的自然。借用愛特伍的話來說,被拋在後面的是我們的身體。羅伯‧唐恩(Rob Dunn)這本《我們的身體,想念野蠻的自然》(The Wild Life of Our Bodies)講的就是身體被拋在後面的後果。比如我們用抗生素和獵槍把細菌和掠食者消滅淨盡,卻沒有考慮到牠們其實是我們共生演化的夥伴,失去與其他物種互動經驗的現代人,反因此得到許多文明病,如克隆氏症、焦慮症及闌尾炎。
「共生演化」這個概念,是在1965年由保羅‧埃利希與彼得‧拉文所提出,也是這本書的核心立論,其中我最感興趣的兩個例子,是人類與微生物以及蛇的共生演化。電視上的優酪乳廣告,或許已經多少讓我們認識到細菌也有所謂的「好菌」,不過把寄生蟲吃回肚子裡治病,應該還是會讓絕大多數的人感到不可思議。生物多樣性一詞出現在媒體中已有一段時間,但目前大多數的情況似乎還停留在以可愛的明星物種作為訴求的階段,至於鉤蟲在人體生態系中的地位,大概只有被克隆氏症折磨的人才能體會。人們或許會認同野生動物「保留區」的存在,卻對自己腸道的「再野化」感到猶豫。如同作者所言:「人類承認自己是地球上極度精密複雜的物種之一,但同時又幻想著物種之間複雜精密的交互作用,只會發生在其他生物的生態圈中,或其他生物的體內。」
事實上微生物對人體的重要程度,甚至讓我們演化出專門做為牠們庇護所的器官──闌尾。不過除了這些有趣的研究,書中關於微生物的章節還傳遞了兩個很有啟發性的訊息,即科學的領域並非完全客觀,一樣會受人們的主觀認知所左右。主流醫療界之所以長期忽視微生物與人體的微妙關係,採取不分青紅皂白趕盡殺絕的方式,是因為一名機械工程師詹姆斯•瑞尼爾斯(James Reyniers)於一九三五年成功創造出史上第一隻無菌白老鼠,並據此推論人類不需要微生物也能存活。這項結果主導了微生物研究領域及一般大眾的想法,導致長期以來人們認為必須殺光細菌。
然而瑞尼爾斯的推論有一個很大的漏洞──無菌動物必須生活在控制完善的封閉實驗室中。科學並不只是嚴謹的實驗過程,在此之前我們會先問問題,而思考方式則關係到我們會採取什麼樣的「預設立場」──人類是生態圈的一員,或不需要其他物種也能活得很好。另外作者指出學術象牙塔的問題:每個專家的「非本科知識」往往相當有限,彼此使用的術語又各不相同,連神經學家之間要相了解都很困難。對生態學家來說,物種之間的互利共生早就不是新鮮事,如果一個醫生或微生物研究者對生態學稍有涉獵,或者就能跳脫主流醫療的成見也不一定。
靈長類對蛇的恐懼有很深的演化根源,所以人會怕蛇很正常,只是每個人程度不一。當一隻蛇長條狀的身影映入眼簾的第一秒,專司恐懼的杏仁核對我下達後退的指令,但下一秒額葉區就告訴我這是對人類不具毒性的青蛇,我才能鎮定的留下他的倩影。不過另一次遇到眼鏡蛇的情境就完全不同,首先佔據我腦海的念頭是,如果他不讓路該怎麼辦?不過他只淡定的瞄了我一眼就走掉了,整個過程頂多十秒鐘,事後反而很惋惜錯過拍照的機會。有趣的是,當時我其實並不百分之百確定他是不是眼鏡蛇,所以我的反應有一半算是來自漫長演化過程中的直覺(生活在非洲雨林中的坎貝爾猴也有分辨不同蛇種的能力)。靈長類學者琳恩‧伊斯貝爾也有這種「身體比眼睛先『看』到蛇」的經驗,按照她的推論,我們的眼睛之所以會演化出與我手上的Canon450D並無二致的細膩成像能力,使我能分辨出赤尾鮐與青蛇鱗片相異的質感;全彩色覺則讓我得以欣賞他翠綠的色澤,這些都是我們與蛇共生演化的結果。早期靈長類為了能辨識出靜止不動的蛇需要良好的視覺,警告同伴的需求則促成了語言,而視覺和語言能力的發展又是大腦擴張的核心,這其中的關聯最終使我們成為地球上最聰明的生物(是不是最有智慧另當別論),這麼說來,引誘亞當夏娃去吃知識之樹果實的動物,沒有比蛇更適合的了。
「當我們演化出可以看到蛇的視力時,我們也彷彿發現了蘋果,踏上通往意識、工具、力量的道路。」這是不可逆的過程,羅伯‧唐恩認為,「人類之所以為人類是因為我們選擇了掌控世界」,或許有些矛盾,正是因為我們有能力大幅改造自然、掌握其他物種的生殺大權,溫和人類中心主義或其他倫理觀才會隨之產生。雖然有些時候人類消滅其他物種是因為大腦的偏見,但完全服膺身體或感官的指引並不能扭轉已經造成的錯誤,因為我們已經不可能放棄讓我們「超速」的工具與文明。我們的老祖宗或許很難去愛蛇,但我們可以做到這一點,只要我們將改造自然的力量,運用在改造我們的心智。
Ronald Wright在他的著作《失控的進步》裡寫道,人類「只在演化成智人的路上走了一半,聰明但鮮有智慧。」聰明讓我們製造出工具,但如何妥善使用它則要依靠智慧。我們仍走在演化的路上,未來是否能成為名符其實的「智人」,我相信這樣的考驗將是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