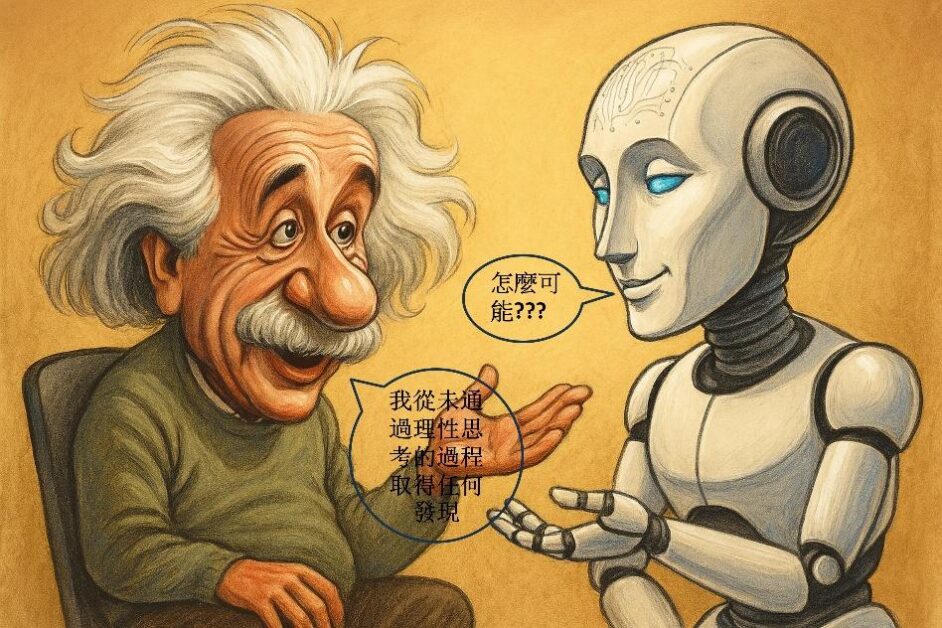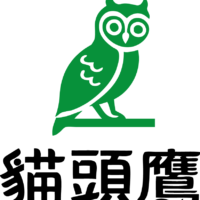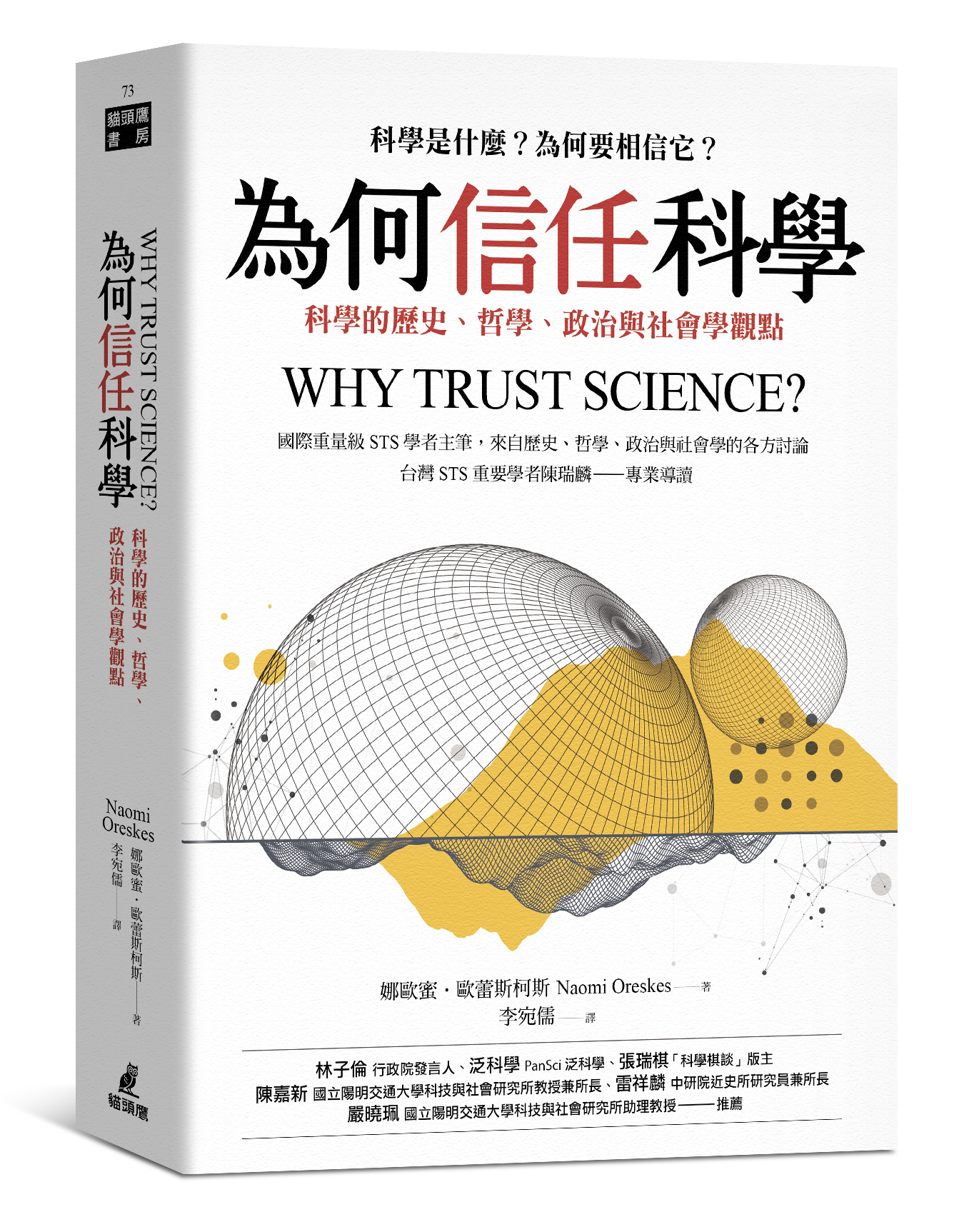- 作者:克萊兒.瓊斯(Claire Jones)
本文編譯自《自然》,原文為〈Careers and controversy before the First World War〉
從《自然》於 1869 年發行後的一百多年以來,女性對科學的貢獻常被貶低,不管是期刊還是學界皆是如此。在《自然》發行至今的 150 年間,可以從中注意到科學做為一項「職業」的面貌漸漸地對大眾展露,但當研究從家庭走向學會組織時,女性變得愈來愈難被看見,歷史敘述角度也總是由男性主導。
我研究的目標是找出女性所面臨的阻礙,以及她們又是如何在此般情況下獲得接受科學教育的機會,並在學會、期刊和大學中移除這樣的阻礙。雖然我所關注的有限——主要是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的英國——但這是《自然》前五十年的核心地帶,而且不論好壞,大英帝國都在這個時期提供了科學研究的背景。
不管我們在科學故事裡多努力的找尋,女性多半在其中缺席。追溯這些平凡女性(她們不全都是女英雄)的科學路,就能夠知道我們往科學勞動力上的性別平等走了多遠。

科學是男性的天生專利?她們早已悄悄踏足於此
如果你認為,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前都沒有女性能在科學領域上開展事業的話,是可以理解的,大多數的人都有「「科學原本就是沒有女性存在(female-free)的區域」的誤解。然而,在像《自然》這樣刊登科學研究的平台出現以前,科研女性往往需要進行各種偽裝,好維持她們的研究,甚至在《自然》發行後的早年間也還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當時的科學界說不太上是對女性友善的就業環境,嚴重的偏見和歧視嚴格限制了女性的機會。然而,透過認清那些儘管受到阻礙仍然貢獻於學界的女性,便能夠破除「科學天生就是屬於男性」的迷思。

在 19 世紀初,女性會藉由那些看起來「較適合女性發揮」的空間以進入科學領域。比如說像是面向孩童和普羅大眾的科學寫作、科學插畫或是翻譯等等,這些工作既不會威脅到男性也符合理想的女性氣質。
像是麥可.法拉第 (Michael Faraday),便將他自己因受到啟發而投身科學歸功於英國自然科學作家珍.瑪西特 (Jane Marcet) 1805 年的著作《Conversations on Chemistry》。而瑪麗安娜.諾斯 (Marianne North)也是一位著名的植物學家、插畫家與發現者。再更往後的還有天文學家艾格尼茲.克勒克 (Agnes Clerke),她在 1880 和 1890 年代成功發展她天文領域暢銷書作者的事業,更於1893年獲頒英國皇家科學研究院的阿克頓獎 (Actonian Prize)。

路遙且艱——科學學會的阻攔與抗爭
在《自然》剛發行的時候,大部分的科學學會都僅限男性加入。1991年,美國加州史丹福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 California) 的科學史學家隆妲.施賓格 (Londa Schiebinger) 便留意到,300年以來,英國皇家學會 (Royal Society) 裡唯一長久存在的女性是保存在解剖學櫥櫃裡的一具骨骸。
學會和其他菁英的科學組織一樣,一直到 1945 年,也就是在《性別失格(撤除)法》(Sex Disqualification (Removal) Act 1919) 頒布的 26 年後,才允許女性加入。雖然此法案早在 1919 年便裁定:「個人不得因性別或婚姻而被剝奪資格⋯⋯以加入任何社團法人(無論是通過皇家憲章還是其他方式成立的團體)。」
《自然》對於法國科學院 (French Academy of Sciences) 1911 年否決物理及化學學家瑪莉.居禮 (Marie Curie) 的加入——就算她在八年前便獲得諾貝爾獎——表示斥責。
「這是不能理解的……就任何正義上的道德原則而言」《自然》寫到,「就因為居禮剛好是女性,所以她那些傑出科學成就所贏來的榮譽就應該被否認。」

女性也同樣做出反擊。在 1900 年前後,由演化植物學家瑪麗安.法夸森 (Marian Farquharson) 領導的團體所努力協商出的成果,獲得了加入科學學會的許可,在成員間激烈地辯論過後,有 11 位女性在 1905 年獲許加入林奈學會 (Linnean Society),然而學會對此進行了報復,拒絕了法夸森的加入申請,直到 1908 年那些異議已經逐漸消失,她才得以入選。
情況總是在提出女性是否要加入學會的疑問時變得異常嚴苛。當英國皇家地理學會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在 1900 年前後思考這個議題時,學會會員與理事會成員的熱烈爭論在《泰晤士報 (The Times)》的讀者投稿區爆發。由於學會的排斥,阻礙了女性使用網路資料、藏書,和獲得獎學金與合作的機會,這也讓女性的事業版圖與男性有著極大的不同。

為什麼會對女性有著嚴厲的反感?
一個原因是科學自身往往傳授這樣儘管現在已經不被承認的概念:性別在智力上天生的差距會限制女性對於科學的適應程度。達爾文認為,演化上的競爭導致了男性在智力上和女性在情感上的高度發展。結果,人們便將女性的加入視為降低學術研究難度、損害學會菁英地位的威脅。由於對演化論的擁護而有「達爾文的鬥犬」之稱的生物學家及人類學家湯瑪斯.亨利.赫胥黎 (Thomas Henry Huxley),便極力阻止女性加入倫敦地質學會 (Ge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和民族學會 (Ethn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明確地表示對學會地位與威望的維護。
對於「男性與女性腦部造成顯著存在的智力上不足」的思想根據理論,就像吉娜.里彭 (Gina Rippon) 在她 2019 年的書《The Gendered Brain》中所表露的,她用科學推翻了這些想法,里彭批評道,現代的演化心理學和對腦部的研究總在尋找性別間的差異,並在發現差異時僅考慮生物學解釋。

然而,這些觀點所造成的影響,對將這樣想法內化的那些女性和廣泛的科學界而言,都不容忽視。著名的數學家和天文學家瑪麗.薩默維爾 (Mary Somerville),在她去世後於 1874 年出版的《Personal Recollections, from Early Life to Old Age, of Mary Somerville》一開始中談到:「他沒有創造力⋯⋯上帝的那份榮光並沒有授予『女性』。」刊登於《自然》的一篇書評認為薩默維爾的才能「完全是罕見的」,因為「女性並非自然上就適應於涉及高度歸納和分析過程的科學研究」,儘管她獨特的科學天分,該書評極力地指出她依舊是「具有非常好地女性氣質的 (beautifully womanly)」。

薩默維爾不只翻譯了皮埃爾.西蒙.拉普拉斯 (Pierre-Simon Laplace) 出了名艱澀的著作《Traité de Mécanique Céleste》(即 1831 年發行的《Mechanism of the Heavens》),她的注解筆記也擴充了整個作品,她的書被採用為英國劍橋大學的標準教科書。甚至「科學家(scientist)」一詞,其實是 1840 年代劍橋大學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UK) 的教師威廉.惠威爾 (William Whewell) 為像薩默維爾這樣「自然哲學家(natural philosopher)」或「科學人(man of science)」所創造的。
那些被遺忘的領域,是她們掌握的機會
比較新成立的學會就沒那麼挑剔,這些學會在接近 19 世紀末各項科學開始專門化時大量增加,為業餘愛好者、教師和女性成立的協會也慢慢出現,而當然,有些女性會在這些學會中擔任重要的角色。
舉例來說,就有許多人活躍於英國天文協會 (British Astronomical Association, BAA),包括參與考察、任職於理事會與編訂期刊。伊麗莎白.布朗 (Elizabeth Brown)便是協會的始創成員:她領導了 1881 年成立的利物浦天文學會 (Liverpool Astronomical Society, LAS) 的太陽部門 (Solar Section),而 LAS 也在 1890 年發展成為 BAA。

天文學之所以為女性提供了特殊的機會,可以說是因為其他科學的專業化,逐漸將研究從家中轉移到那些排除女性的學術機構,進而才遺留下了這個領域。植物學也是如此,以其自從 18 世紀起便是女性追求的職業就能知道它受歡迎的程度。
同樣的還有古植物學,更是在 20 世紀初的十幾年內都強烈地以女性為導向,在這段期間進行研究並出版的女性古植物學家包括:瑪格麗特.班森 (Margaret Benson)1、艾格尼絲.阿爾伯 (Agnes Arber)2、亨德琳娜.史考特 (Henderina Scott)3以及瑪麗.斯托普斯 (Marie Stopes)4。
在下一篇中,我們將繼續看見女性在科學領域的處境,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的女性科學家該如何進入其他研究領域,她們又持續面臨著什麼樣的懷疑與挑戰呢?
註解:
- 班森是倫敦大學皇家霍洛威學院 (Royal Holloway, University of London)的講師。
- 阿爾伯畢業於劍橋大學紐納姆學院 (Newnham College, Cambridge)。
- 史考特主要在家中進行研究和協同工作。
- 斯托普斯是曼徹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的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