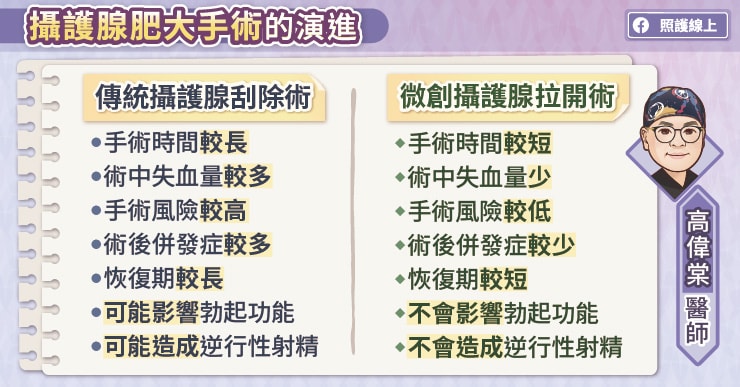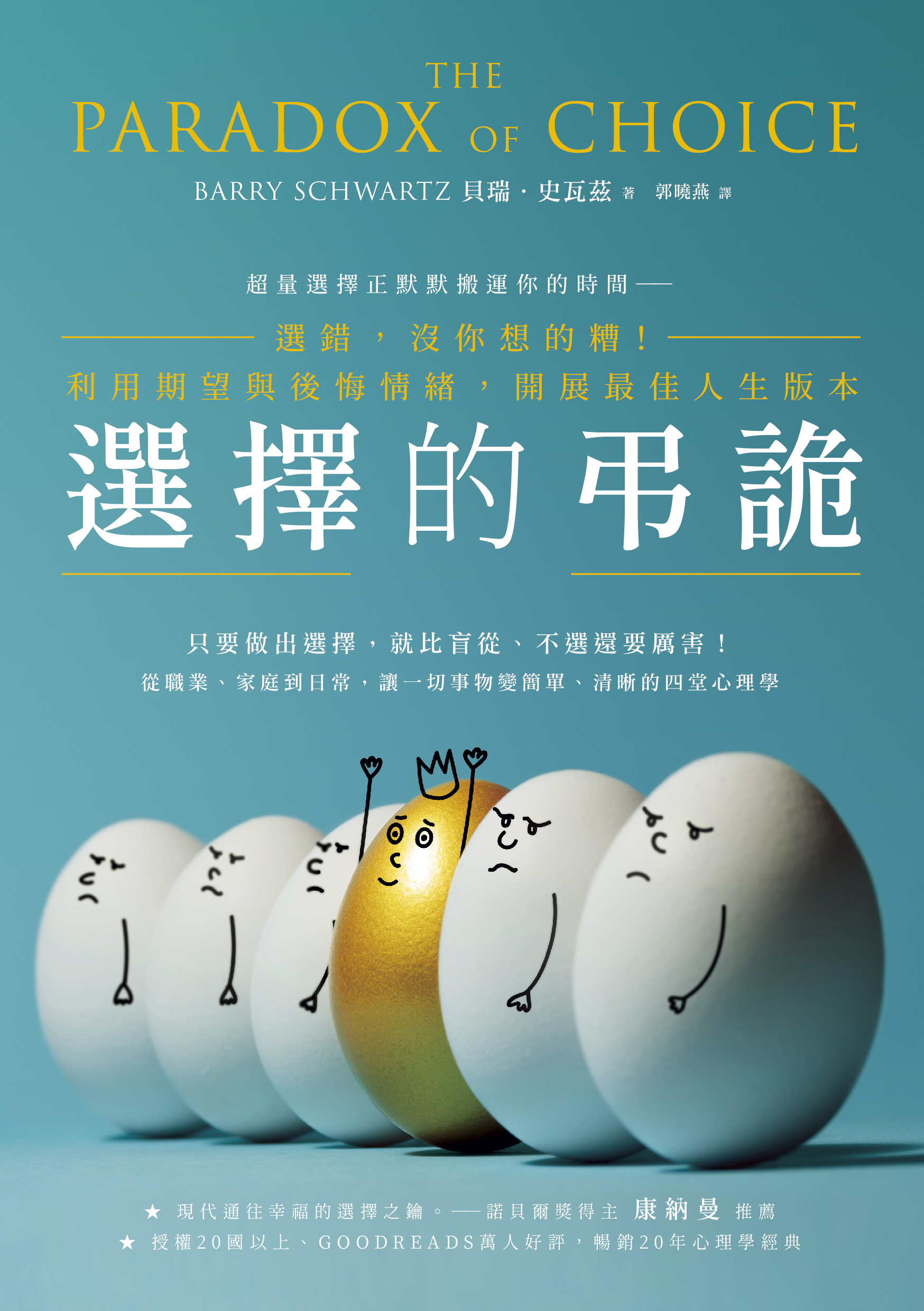牛津大學的一項大腦醫學成像研究顯示:對治療持悲觀態度可使強力止痛劑徹底喪失效力。
參與者進入核磁共振掃描儀。 牛津大學的一項大腦成像研究顯示:對治療持悲觀態度可使強力止痛劑徹底喪失效力。 在鎮痛劑給藥方式未改變的情形下,患者對治療信任水平的變化使其經歷的痛苦水平隨之變化。
相比之下,本研究中的對治療持樂觀態度的志願者接受鴉片類藥後,其生理或生物化學鎮痛效應隨即倍增。
這項有關安慰劑效應及其反向效應,即「反安慰劑效應」的研究已發表於《科學—轉化醫學》(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 研究發現,在所有治療中,醫生可能需要考慮患者對治療有效性的信任水平,同時需要考慮適應該患者的最優藥物。
牛津大學大腦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中心的艾琳•特雷西(Irene Tracey)教授(本研究由其率隊)說:「醫生不應該低估患者負面期望對臨床效果可能產生的重要影響。」
比如說,慢性疼痛患者通常會到處求醫問藥,但多種藥物的嘗試結果又經常使其希望落空。 如果患者帶著這種負面的經驗來看醫生,心裡又滿是世上已無藥可以減輕其痛苦的念頭;那麼作為醫生,在臨床採用任何有效減輕其痛苦的藥物前,都必須處理好這種負面情緒(否則將可能事倍功半甚至徒勞無功)。
安慰劑效應描述了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形下給予不含有效藥物成分的「藥片」或給予假治療時患者病情得以改善的情況。 這種效應是極為真實的生理效應,並非只是患者主觀上感覺「好多了」。 而反安慰劑效應則反其道而行之:患者對治療的懷疑與不信任使其恰恰看到了更糟的治療結果。
此前的研究已經探索了安慰劑效應的相關基礎:比如說服用糖片或用鹽水注射確實可以引發真實的(生理)響應。
本項新的研究由醫學研究委員會與德國研究贊助人提供資金。 實驗證明:調控患者對治療方案的信任水平,可影響其對有效藥物的響應。 這一實驗通過對該調控方式具體過程的探索而使相關領域向前邁進了一步。
牛津大學研究小組與來自位於德國漢堡—埃彭多夫的大學醫學中心、劍橋大學與慕尼黑工業大學(TUM)的同事聯手對這些效應進行了研究。 研究對象為22名健康成年志願者,其接受的藥品為鴉片類,實驗人員調控其在不同點可能接受的疼痛緩解的(信任)期望水平。
志願者被置於核磁共振掃描儀中並以熱輻射加熱其腿部(增強熱輻射使之到達開始感到疼痛的水平——每個自願者在1到100的這個範圍內評估其疼痛程度,評估結果為70)。 同時進行靜脈置管,準備注射強力鴉片為自願者減痛。
首次操作行程啟動後,在參與者不知曉的情形下,研究小組開始注射鴉片,旨在觀察(實驗對象)不知情或(研究者不了解其對治療的)信任水平的情形下藥物效力。 這樣,原來的平均評估疼痛程度從位於66這個刻度下滑到55這個刻度上。
然後研究者告知志願者:給予(鎮痛)藥物注射(但實際上未作變化,志願者繼續接受同劑量鴉片)。 這時平均疼痛率繼續下降,到達39這一刻度。
最後,在研究者的引導下,志願者相信已被停藥;研究者同時警告志願者疼痛可能加劇(實際上並作變化,仍以相同方式繼續給藥)。 結果志願者疼痛強度提高到64。 也就是說,其疼痛水平跟實驗開始時未接受任何鎮痛藥時一樣。
研究者運用大腦成像來確認參與者有關疼痛減輕的報告情況。 核磁共振掃描顯示:大腦痛覺網絡會根據志願者每個階段的期望水平作出不同範圍的響應,與志願者所報告的疼痛程度相吻合。
這就表明,志願者心中期望水平變化時確實存在不同程度的痛苦經歷,儘管鎮痛劑的給藥水平始終恆定。
特雷西教授說,這些研究結果已從一小組健康的志願者中觀察到,其效應由短時、非持續的(針對參與者對療法的信任及期望水平的)調控所致。 關鍵是在任何治療中都不能低估這種信任(期望)效應的力量,醫師需要掌握調控的具體方法。
在臨床實驗設計方面可能也有一些啟示。 臨床實驗常常設計為候選藥與安慰劑的對照實驗,以期觀察候選藥是否優於安慰劑。 「應該控制實驗對像對任何臨床實驗的(信任)期望效應。至少必須使負面期望最小化,以保證實驗中的藥物的效力未受其影響。」
本文來自 科學松鼠會資訊小分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