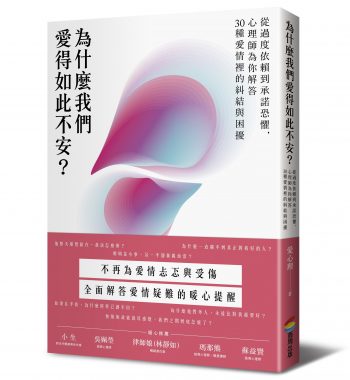撰文╱葛瑞布耶爾(Ann M. Graybiel)、史密斯(Kyle S. Smith)
翻譯╱林雅玲
重點提要
- 我們重複某個行為時,大腦裡的紋狀體會參與形成特定的習慣迴路,讓習慣成為自動化的一個單元(稱為「集組」)。
- 然而,另一個腦區「新大腦皮質」(neocortex)會監控這個習慣。利用光訊號調控實驗大鼠的新大腦皮質,就能阻斷一個習慣,甚至能防止習慣形成。
- 研究人員正在釐清這些大腦結構如何運作,希望能開發藥物、行為治療以及簡單的技巧,來幫助我們控制習慣,無論是好的或壞的習慣。
我們每天都在重複數量驚人的習慣行為。大多數這些習慣,從刷牙到駕駛在熟悉的道路上,我們都能以「自動導航」的模式進行,好讓大腦不會因為專注於每個刷牙的動作或不斷微調方向盤的細節而負荷過度。有些習慣(例如慢跑)可以幫助我們維持健康,但是經常從零食櫃拿零食吃就不一定了。而歸類為強迫行為或成癮的習慣(例如暴食或吸菸),則可能會威脅我們的健康或生命。
雖然習慣是我們生活裡重要的部份,科學家探究大腦如何把新行為轉變為習慣時,卻遇到很大的挑戰。少了這些知識,專家就無法藉由藥物或其他療法幫助人們戒除壞習慣。
如今,新技術讓神經科學家破解我們「儀式行為」背後的神經機制,科學家已能辨認出所謂的習慣迴路,也就是大腦裡負責建立並維護習慣行為的區域與連結。從研究獲得的見解,幫助神經科學家釐清大腦如何建立好習慣、我們為何難以戒除一些平時不易察覺的習慣,或者是醫生和親人希望我們停止的行為。研究顯示,刻意調控我們的大腦也許能控制習慣,無論是好的或壞的習慣。這種美好的說法源於幾個意外發現:即使我們的行為看似自動,其實仍有部份腦區盡責地監督我們的行為。
什麼是習慣?
習慣似乎是一種明確的動作,但是在神經科學上,它們歸屬於一連串的人類行為。
在這行為範疇的一端,是幫助我們騰出大腦空間以進行其他工作的自動化習慣,其他則是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的行為。當我們探索現實世界、社交環境以及內心感受時,就會自然而然形成習慣。我們嘗試在特定情況下表現某些行為,找出哪些行為似乎對情況有所幫助或不需花費太多心力,接著鞏固這些行為,最終形成習慣。
我們在年幼時就啟動這個程序,然而,過程中有得有失。當行為成為一種習慣,我們就越難意識到它的存在,而對這些行為失去高度的警戒監控(例如,我出門前到底有沒有關瓦斯爐?鎖門了嗎?)不僅會干擾日常運作,也可能讓壞習慣悄悄上身。很多發福的人(雖然每次只增加一、兩公斤)會突然意識到自己越來越常光顧超市的零食區或甜甜圈店,而且常常是不假思索就進去了。
檢視自身行為的監控系統隱約失效了,意味著習慣可能演變為類似成癮,看看有些人沉迷於電腦遊戲、網路賭博,以及不斷發簡訊和流連社群網站就知道了,當然還包括酒精和藥物濫用。
重複且具有成癮模式的行為,可能會取代一些過去需要深思熟慮做選擇的行為。雖然成癮必定屬於行為範疇裡的極端例子,但神經科學家也在探討它們是否類似正常的習慣,只是程度較為強烈。有些特定的神經精神疾病也可視為極端型式的習慣,包括強迫症(耗盡心神在某些想法或行為上)和某些型式的憂鬱症(重複循環負面的想法),自閉症和精神分裂症可能也是,此類患者重複且過度專注於某事物的行為已造成困擾。

有意識的行為轉變為不經意的習慣
雖然不同習慣分屬於行為範疇的不同部份,但它們有一些共同的核心特質。舉例來說,習慣一旦形成就很難戒除,儘管告誡自己「別再這樣做」,但通常還是會失敗!部份原因可能是反省的時間點太晚,通常是在我們已經做出行動且感受到後果之後。
這種頑強特質透露出線索,讓科學家得以研究負責建立並維持習慣的大腦迴路。習慣如此根深柢固,我們即使不想做還是做了,部份是因為「增強關聯性」(reinforcement contingency),也就是說,你做了A行為然後獲得某種回報,但要是做了B行為,不但沒有獎賞,甚至會受到懲罰,這些行為的後果(也就是關聯性),推動了我們之後的行為走向。
腦中的生理訊號似乎與這種和增強有關的學習相對應,最早的研究是由現在任職於瑞士夫里堡大學的舒爾茨(Wolfram Schultz)和羅莫(Ranulfo Romo)所進行,如今則有電腦科學家建構模型。特別重要的概念是「獎賞預測誤差訊號」(reward-prediction error signal),意指我們心智評估和預測未來獎賞的準確度。大腦以目前未知的方式計算出這些評估,藉由增加或減少特定行為的價值來形塑我們的預期。藉由內部監控行為以及增減行為的價值,大腦能強化特定行為,把有意識的行為轉變為習慣,即使我們知道自己不該賭博或吃得過多。
我們和其他研究人員對於造成這種轉變的大腦迴路很感興趣,也想了解是否能阻斷它們。我們在葛瑞布耶爾(作者之一)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的實驗室進行實驗,試圖破解參與其中的大腦迴路,以及習慣形成時它們的活性有何改變。
首先,我們需要有一套實驗來判斷行為是否已成為習慣。英國心理學家狄金生(Anthony Dickinson)在1980年代設計的實驗目前仍廣泛使用,他和同事教導實驗室大鼠壓實驗箱的桿子以獲得食物獎賞。
當大鼠學會了這項任務回到自己的籠子之後,研究人員會「貶值」這種獎賞,例如,讓大鼠吃下過多的食物獎賞,或者是在吃完之後給予牠造成輕度噁心的藥物,然後再讓老鼠回到實驗箱,看看牠們是否會選擇壓桿子。如果大鼠在食物獎賞會造成不適的狀況下還壓了桿子,狄金生便判定這種行為已成為習慣。但是如果老鼠意識到食物獎賞會造成不適,而「留心」不去壓桿子(如果我們可以這樣形容大鼠的話),那就是沒有形成習慣。這項實驗讓研究人員得以監控有意識的行為是否轉變為習慣。
在大腦銘印習慣
澳洲雪梨大學的巴倫(Bernard Balleine)、新南威爾斯大學的基爾克羅斯(Simon Killcross)與其他研究人員,利用這個基本實驗的變化型式已找到線索,指出大腦內不同迴路共同引導把有意識的行為轉變為習慣。目前來自大鼠、人類和猴子的實驗證據指出,「新大腦皮質」(neocortex,被視為哺乳動物大腦的優異之處)和紋狀體(striatum,位於大腦中央、較原始的基底核中)之間有多條迴路互相連結(參見56頁的〈習慣形成三部曲〉)。隨著我們進行有意識的行為或習慣,這些迴路也會有不同的參與程度。
我們教導大鼠和小鼠進行簡單的行為。在一項任務中,牠們學會一聽到聲響就開始跑T型迷宮。並根據朝向T型迷宮頂部前進的過程中聽到的「指示音」,牠們會左轉或右轉,接著跑到末端取得兩種獎賞中的一種。我們的目標是了解大腦如何以特殊方式判斷行為利弊,接著標記一連串行為做為習慣。我們的大鼠確實發展出習慣!即使食物獎賞變得不那麼美味,大鼠聽到指示音時還是會遵從。
為了弄清楚大腦如何標記行為成為習慣,我們在MIT的實驗室開始記錄紋狀體部份神經元的電生理活性。我們對實驗發現感到驚訝。當大鼠開始學習走迷宮時,紋狀體中與運動控制有關的神經元,在跑迷宮的整個過程中都是活化的。但當牠們越來越「習慣」後,神經元活性只有在一開始和到達終點時活化,而大部份時間則是維持平靜,就像是整個跑迷宮行為已經成為套組,其中紋狀體細胞會注意到每次的開始與結束(參見上方〈不假思索的行為〉)。這是相當特殊的模式,看來很像是紋狀體細胞具有可塑性,能幫助封包某些行動,留下相對少量的「專家細胞」來處理行為的細節。
這種模式讓我們聯想到大腦形成記憶的方式。我們都知道,要記住一串數字時,以較大的字符單位來記,比一個一個記還要容易,例如要記住電話號碼,用「555-1212」比「5-5-5-1-2-1-2」好記。已故的美國心理學家米勒(George A. Miller)稱此為「集組」(chunk),也就是做為記憶單位的套組型式。我們在迷宮開始和結束時觀察到的神經活動也類似於此,紋狀體就像設置了行為集組(習慣)的邊界標記,因此這中間涉及的評估獎賞過程,我們的大腦應該會將其儲存。如果事實如此,那麼紋狀體基本上會透過這個策略幫助我們把一連串行為組成一個單元:你看到零食櫃,接著自動接近它,最後拿出一包零食來吃,中間「想都不用想」。

研究人員也在紋狀體的另一部份找到「有意識行為的迴路」(deliberation circuit),當人們不是自動做出選擇,而是需要深思熟慮做決策時,這些腦區就會活化。
為了探究有意識行為與習慣的迴路之間的交互作用,我們團隊裡的索恩(Catherine Thorn)同時記錄兩種迴路的電生理訊號。在實驗動物學會任務後,當過程中需根據指示音決定在T型迷宮頂部的轉彎方向,紋狀體的有意識行為迴路活性會變強,這個模式幾乎和我們在紋狀體習慣迴路觀察到的集組模式完全相反。不過當行為完全成為習慣,活性就會下降,這個模式代表當我們(至少大鼠是這樣)形成習慣時,與習慣相關的迴路會增強並發生變化。
下邊緣皮質(infralimbic cortex,大腦前方的新大腦皮質)和紋狀體會一起運作,我們也記錄了該區的活性,結果同樣令我們大開眼界。雖然我們在迷宮開始和結束時觀察到紋狀體中習慣迴路的自動執行模式,不過在剛開始學習的階段,我們在下邊緣皮質只觀察到很小的變化。直到實驗動物經過長時間訓練並形成習慣,下邊緣皮質的活性才有變化。引人注目的是,下邊緣皮質的變化也會發展出集組模式,而且下邊緣皮質似乎是更有智慧的腦區,一直要等到紋狀體的評估系統完全確認某個行為是值得鞏固的,它才會連結到其他更大的腦區來維持這個習慣。
讓習慣暫停!
我們決定利用「光學遺傳學」(optogenetics)這項新技術來測試下邊緣皮質能否即時控制習慣的執行。利用這項技術,我們可以把光敏分子置入腦中的小區域,接著在該區域照光,就能活化或抑制神經元的活性。我們先讓大鼠獲得跑迷宮的習慣並且形成集組模式,接著抑制下邊緣皮質的活性,結果抑制幾秒後(此時大鼠仍在跑迷宮),我們完全阻斷了牠原本已形成的習慣。
習慣會迅速被阻斷,有時甚至是立刻改變,而且即使光照停止,仍可維持對習慣的封鎖。然而,大鼠並未停止跑迷宮,只是原本跑向貶值獎賞的習慣消失了,牠們會跑向在迷宮另一側的好獎賞並且順利抵達。事實上,當我們重複這項實驗,大鼠會發展出新的習慣:無論聽到哪種轉彎指示音,都會跑到好獎賞的那一側。
接著,我們抑制下邊緣皮質的同一個區域,阻斷了新習慣,然而舊習慣瞬間又出現了。舊習慣在數秒內回復,而且不需要再度抑制下邊緣皮質,就能在之後的每次測驗中持續。
很多人都體驗過極力戒除一個習慣,但是經歷一段艱困時間或者僅僅復發一次之後,過去的習慣就會完全回復。20世紀初,俄羅斯科學家巴佛洛夫(Ivan Pavlov)在狗身上觀察到這個現象,他的結論是動物永遠不會忘記根深柢固的制約行為(例如習慣),最多只能抑制而已。我們發現,實驗大鼠的習慣一樣頑固,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可以在行為實際發生時,藉由調控新大腦皮質的一小部份,就能啟動或停止該習慣。我們不清楚這樣的調控影響範圍有多廣,例如,如果教導大鼠三個連續的不同習慣,接著阻斷第三個習慣,此時第二個習慣會出現嗎?如果再阻斷第二個習慣,那麼第一個習慣會出現嗎?
一個關鍵問題是我們能否在一開始就阻止習慣形成。我們訓練大鼠讓牠們剛好能到達T型迷宮的正確終點、但還不足以成為習慣;之後繼續訓練,但每次跑迷宮時就以光學遺傳學抑制下邊緣皮質。經過多天的連續訓練(通常能形成永久的習慣),雖然大鼠會繼續跑迷宮,但從未能形成習慣。接受相同訓練的對照組大鼠(沒有利用光學遺傳學去抑制)則順利形成習慣。
本文轉自《科學人》2014年第150期8月號
SA原文:How the Brain Makes and Breaks Habits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