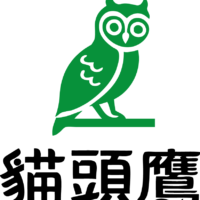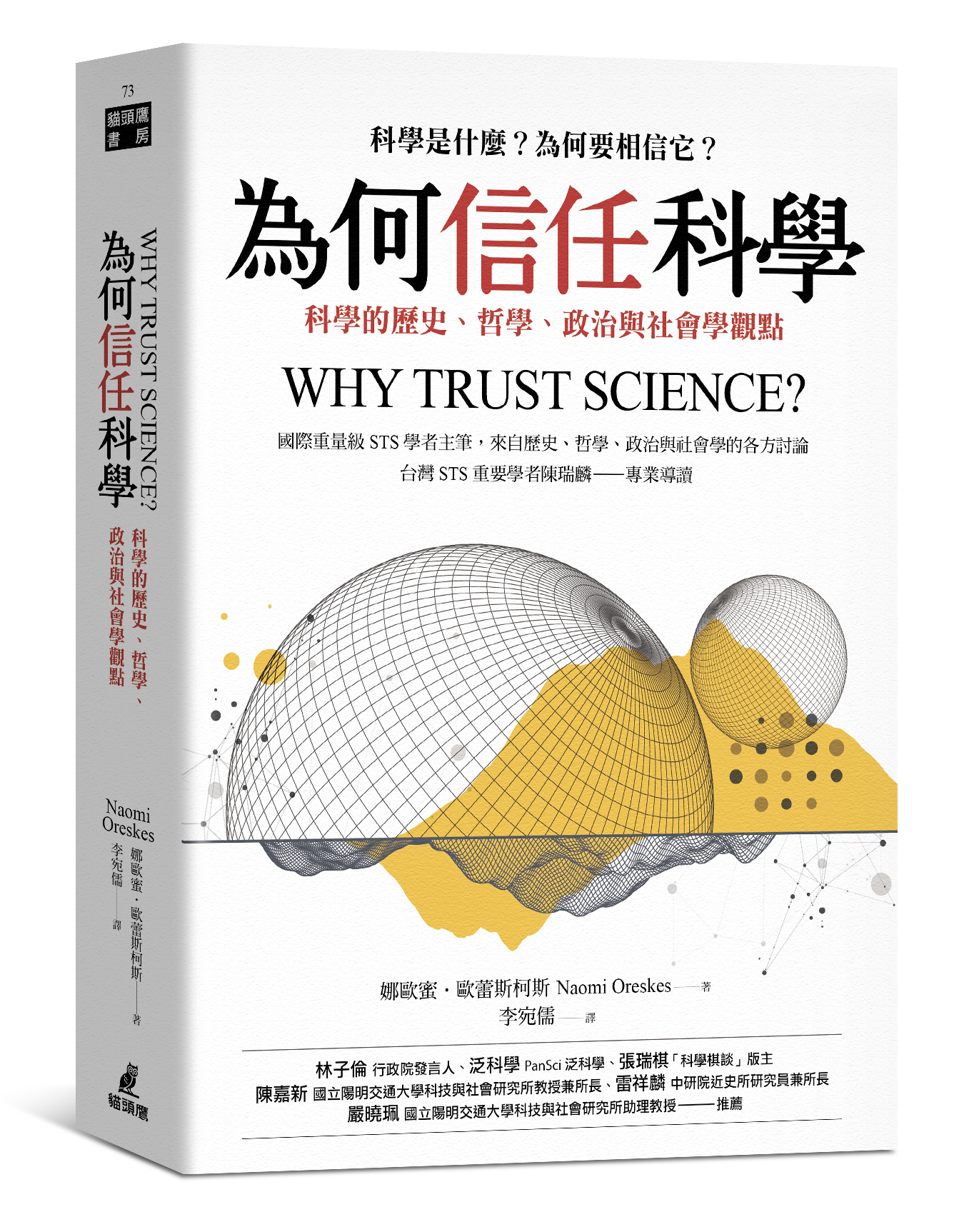柏拉圖曾在他的《理想國》一書當中,用洞穴的比喻描述人們知識的侷限性;而要突破知識的侷限性,似乎唯有透過科學的進展才能達到。然而,現今我們採用心理學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研究結果,真能保證它們都是真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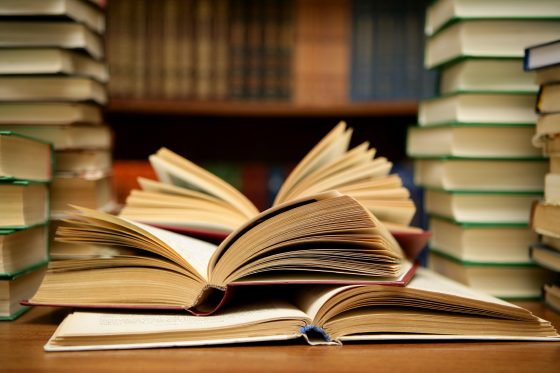
昨天看到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的一篇文章,裡面引述了Science期刊上的一篇研究論文,該篇論文由270名心理學家共同合作寫成,他們重複了過去心理學經典研究中的其中100個實驗,結果發現,過去那100個實驗當中,有97個達到顯著結果,但是在重複驗證的過程當中,卻只有36個達到顯著。
這當中有許多可能的解釋,例如文中提到的出版偏誤(publication bias)──因為實驗資金分配的關係,科學家們傾向研究新的議題,而非重複驗證過去的實驗;或是科學期刊只想刊出顯著、有趣的研究,而得不到顯著結果的研究,科學期刊往往會忽略它們。除此之外,無法排除混淆變項、實驗過程不夠嚴謹都是有可能的原因;甚至是我們在發表論文的過程中,只會發表有做出成效的研究,但是一個在99%信心水準下達顯著的實驗,只要重複操作100次,期望值上就會有一次是顯著的,因此我們看到的,或許是全世界心理學家做了數千次當中,唯一顯著的那幾十次而已,這可以說是肯證偏誤(confirmation bias)的一種。
然而,本文主要並不是要探討實驗方法的部分,而是提出一些關於研究思考的方向。
昨天在看到這篇文章之後,我把它貼在我的Facebook上,並在下面討論做實驗的意義在哪裡?我一個朋友看到之後,就在下面回說「我做研究覺得很爽就好了啊!」。這一句話乍聽之下似乎很不負責任,但這或許會是另一個關於科學研究,我們可以思考的徑路。
事實上,科學研究真的能夠帶給我們什麼嗎?攤開科學史一看,我們幾乎找不到什麼東西是確定的,其實我們難以想像,中古世紀的人為何會迷信地心說如此荒謬的說法,但是若你是一個中古世紀的人,只有當時的科學儀器,活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之下,其實是無法得知地球並非宇宙中心這個事實的,即使地心說受到質疑,托勒密依然提出了本輪與均輪的說法,企圖解釋行星逆行的這個「異例」。因為我們不知道世界的真實樣貌是什麼,所以有的科學家才會秉持著自己所相信的,企圖修復舊有的理論,而非提出新的理論加以說明。
但是,隨著科學的進展,來到了現今的我們,真能確保我們所知的一切就是事實嗎?就好比中古時代的人,以當時的社會、科學背景,並無從突破當時的知識,現今的我們,同樣難以突破我們所見所聞的一切,只能活在現有的知識背景之下而已,而似乎唯有實驗方法的演進,才能讓我們得到更多的知識,而這可能會是一個永無止盡的過程。更進一步的,如果我們採取嚴格懷疑論的觀點,我們根本無從證成任何的事物,就如同笛卡兒所說的,我們唯一能證成的就是自己存在而已,而這個自己是什麼模樣我們也無從得知,因為一切都有可能是魔鬼所欺騙我們的;只要我們透過感官來觀察這個世界,那麼感官可能會受到的欺騙、幻覺、錯覺,我們就永遠都無從避免,所以也有一種可能性,一種無法被排除的可能性──我們根本就不可能對這個世界產生任何的知識。
從這樣的觀點來看,我同學所說的那一句話:「我做研究覺得很爽就好了啊!」似乎就變得很有道理了。
或許,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科學研究,我們研究的目的、追尋世界真理的目的,背後到底是什麼?社會心理學家喬治·凱利(George Kelly)曾經如此比喻人們探索世界的方式,就好像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個素樸科學家(naive scientists)一般,會對這個世界提出假設、驗證假設、駁斥假設、產生新的假設。
尚·皮亞傑(Jean Piaget)也曾如此描述孩子探詢世界的方式──我們會對這個世界產生一些認識,然後把那些知識整理成基模(schema),當我們碰到和過去基模衝突的事件時,我們會試著去修改舊有的基模,或是創造出一個新的基模,來應變外在世界的變化。這兩位心理學家描述了人們探索世界的方式,而這種方式其實就是科學研究的縮影,只是我們這些素樸科學家做的實驗並沒有那麼精確而已。
而人們之所以要如此費盡心思地預測、掌控這個世界,其實就是為了一件事情──「我們在尋找可預測感、可控制感,因為這將帶來安全感。」而我們所追尋的可控制感、可預測感,其實也包含了另一個要素在裡面──我們希望它是越簡單越好的。這也是為什麼哲學理論會有一個「奧坎剃刀原則(Occam’s Razor)」──可以解釋同一事件的諸多理論當中,我們會挑選最精簡、最少假設的理論。即便比較精簡的理論並不一定比較正確,只是在沒有更多證據的情況下,我們通常會這麼做。
其實不只是科學研究,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我們之所以會對許多事情產生畏懼、害怕,正是因為不確定性,在遭受重大創傷的人會產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在發生重大刑案之後我們會急著想要判兇手死刑、在分手了之後我們會產生厭男/厭女情節;或是我們害怕突破舒適圈、害怕探索未知的世界、害怕採取其他的選擇──即使那個選擇或許比當前我們的行為更適合面對外在困境,也都是因為我們追求安全感使然。就如同佛洛伊德在《超越快樂原則》當中所提到的一般,人們追求的並不是快樂,而是習慣,因為習慣將帶來安全感。
也許,做科學研究真的就只是為了自己開心而已,我們有可能可以一步步更逼近真理,也有可能什麼都得不到;追求的理論被反駁修改之後,也許科學家們終其一生研究的成果都化為泡沫,就如同行為主義大師史金納(B.F. Skinner)在其年邁時,他的理論已經被批判的體無完膚了,他仍然堅持他的理論,堅持「你只能改變你的行為,不能改變你的想法(You can’t change your mind, you change your behavior)」,因為對他而言,他的研究就是他信奉終生的信仰,它生命的一大部分了。也許,我們永遠也無法走出《洞喻》當中的那個山洞,但也許,我們是否得到了真理並不是那麼重要,重要的是研究科學的歷程,以及科學帶給了人們更多的可預測感與可控制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