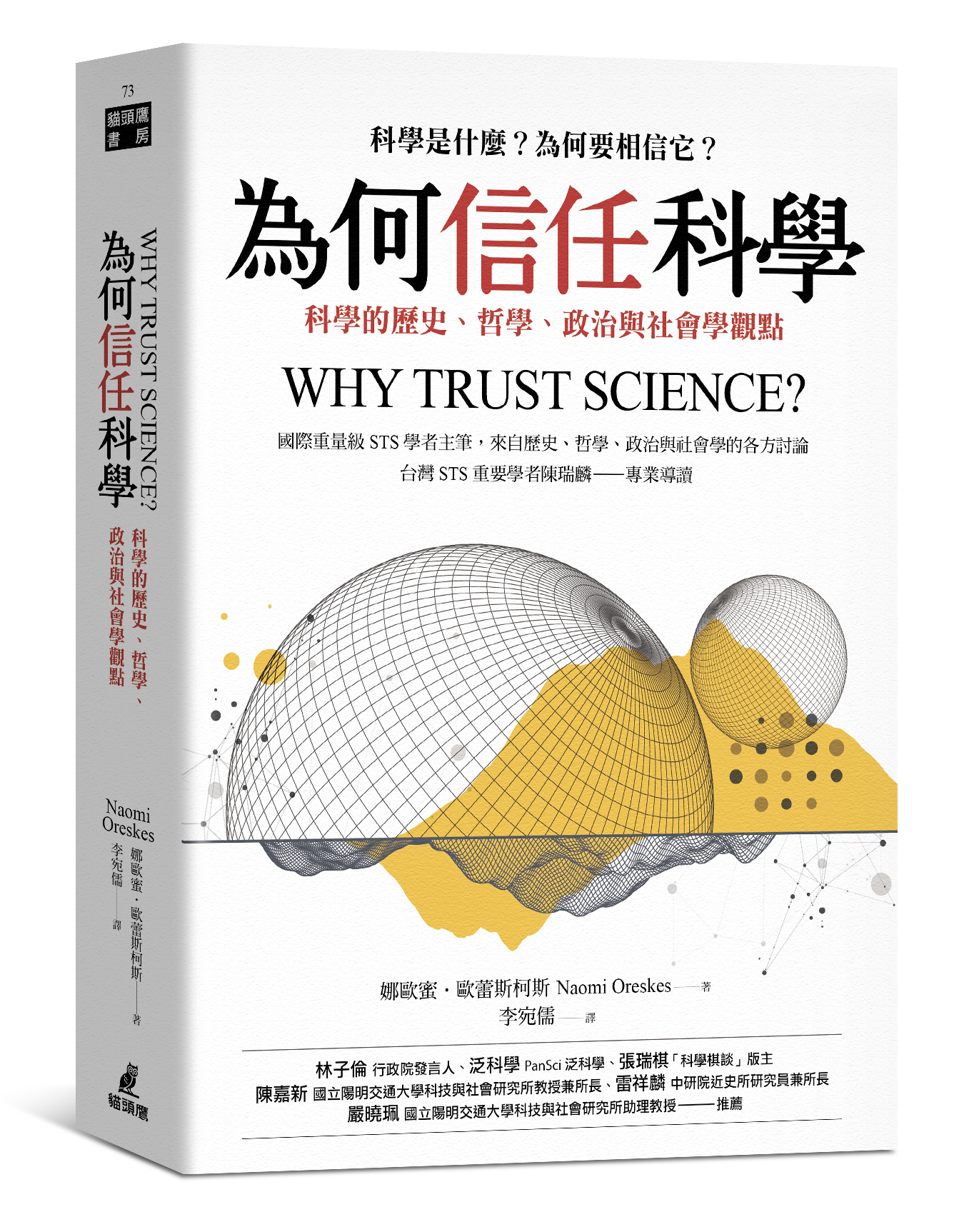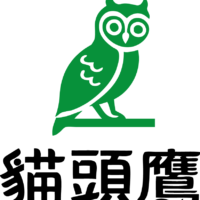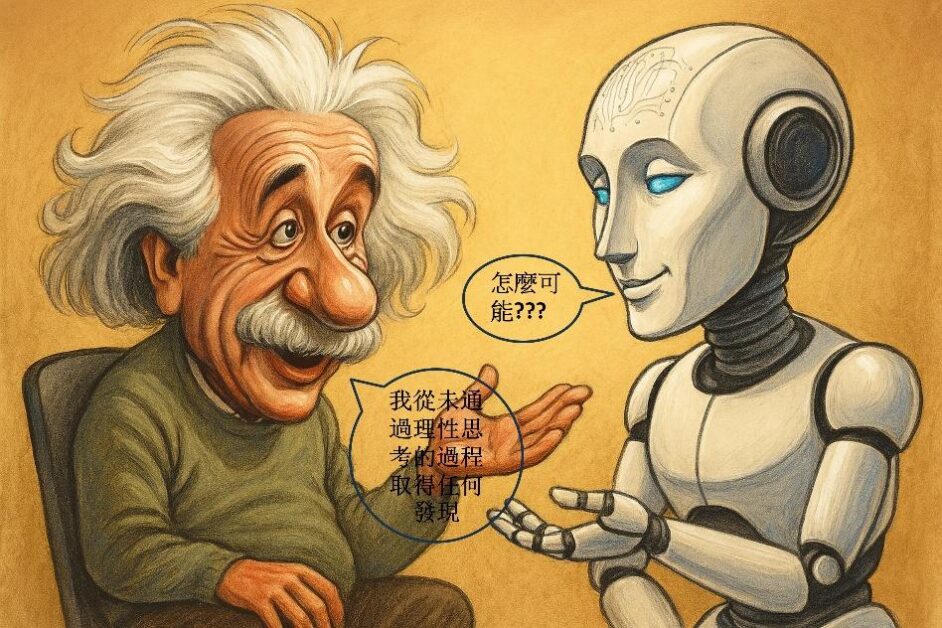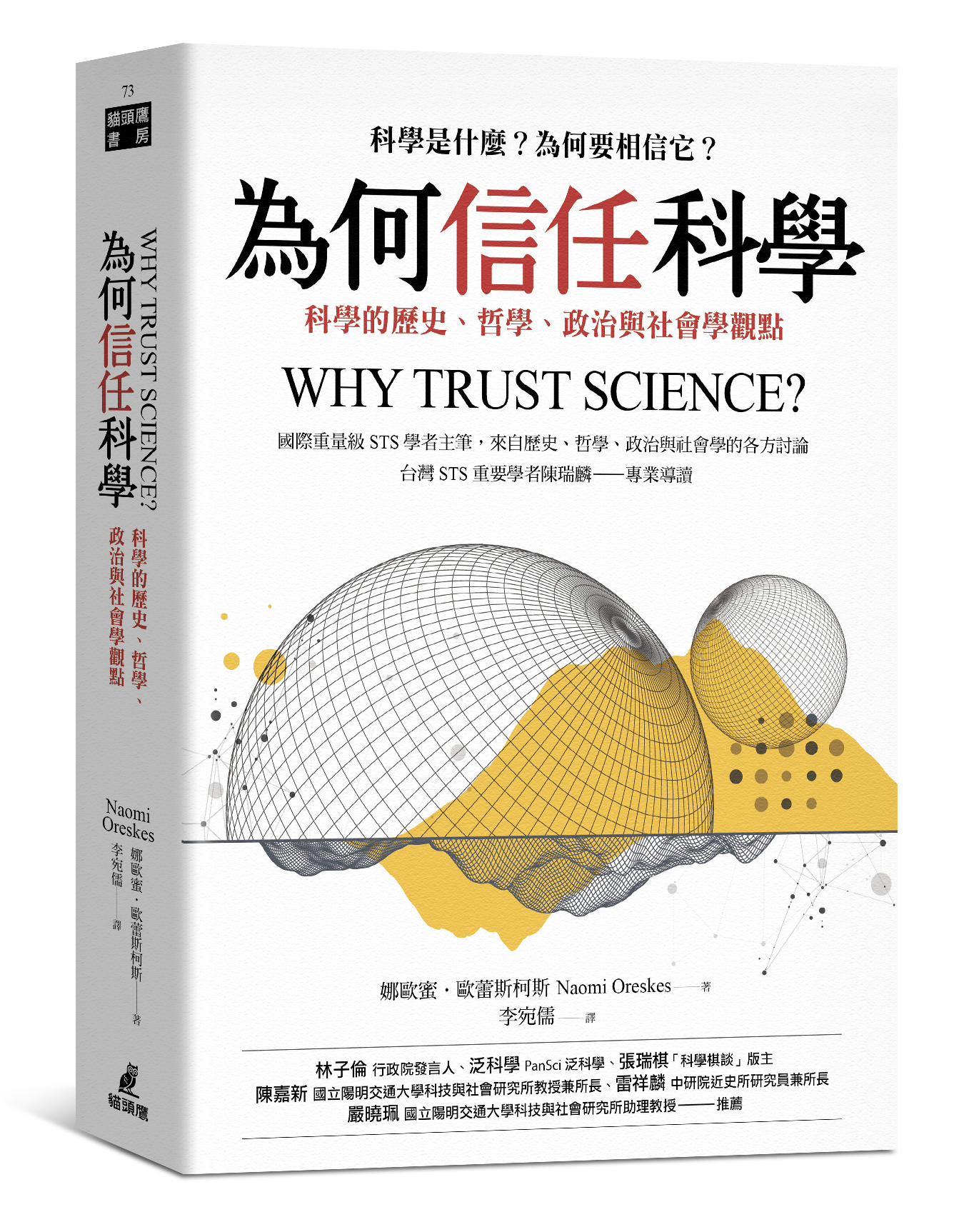科學,一種帕斯卡賭注
如果一個科學主張會對社會、政治或個人造成影響,那在衡量它時,就必須多考慮一個問題:如果錯了會怎樣?接受一個主張最後卻發現它是錯的,有什麼風險?拒絕一個主張而最後發現它是對的,又如何呢?
如果知道服用避孕藥的風險,一位健康女性就可以在憂鬱出現時即時停藥。避孕藥引發的憂鬱通常很快就會消失,對許多女性來說這樣的風險還算輕微,值得一試。同樣地,牙線很便宜,使用牙線每天只需要幾分鐘,如果最終發現沒什麼用處也不會有太大損失。但某些議題就沒那麼簡單了。
想想人為氣候變遷,儘管相關科學研究已經持續了五十年,累積了上萬篇同儕審查的科學論文、數百篇政府及非政府組織的報告,許多美國人仍懷疑氣候變遷的真實性及人類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總統、國會議員、企業領袖、《華爾街日報》的社論都曾表示懷疑,拒絕相信好幾個世紀以來充分發展的物理理論,以及海平面上升和頻繁極端氣候事件等經驗證據。另外有些人則認為,儘管人為氣候變遷真的有發生,但不會造成太大影響,甚至是件好事。
做為一位科學史學者,我知道能量有限理論、優生學、激素避孕藥的歷史,也知道要判斷使用牙線是否有益十分困難,最重要的是我知道地質學家在衡量大陸漂移理論時受到了政治理念影響。我從未預設我們相信科學永遠合理,或通常是合理的,我一直認為這個問題很棒:科學主張的基礎為何?我們應該相信科學家嗎?
信任科學非常重要,但科學家不能期待大眾單憑信任就接受他們的主張。科學家必須解釋他們如何做成這些主張,並承認他們有可能因為忽略或蔑視某些證據而犯錯。如果有人合理指出某些證據被漠視或不合比例的強調,無論這個人是科學家、業餘專家、記者還是飽學的公民,都該考慮他的想法。科學家必須保持開放,明白他們有可能犯錯或忽略某些重要的事情。重點在於,無論科學家有多麼聰明正直,我們相信的都不是科學家,而是相信科學做為一種社會過程,能夠嚴謹地檢驗科學主張。

有些科學結論已經發展完整,不再有人提出合理的懷疑;有些理論則是早就被推翻了。上述論點並非在說科學家應該繼續投入時間與精力,反覆證明或推翻這些結論。如同孔恩在超過半世紀前所討論的,如果說科學可以說是一種進步,那是因為科學家知道怎樣達成共識、往下一步邁進。針對大陸漂移理論的辯論,是在新一代科學家找到了一系列更切中要害的證據後才重新開啟的,這可說是該案例中最突出的一個面向。
我們可以用帕斯卡的賭注來說明這個問題。無論一項科學知識發展得有多完整,無論專家共識有多強大,永遠還是會有不確定之處。因此每當有人挑戰科學知識(不管是出於什麼原因),我們都可以先學帕斯卡這樣問:如果這項科學主張最後證明是對的,忽視它會有什麼風險?相較之下,因應這項主張而行動,但最後發現它是錯的,代價又是什麼? 不用牙線的風險真實存在,但不至於太嚴重;對氣候變遷的科學證據視而不見,代價則太高昂了。
不可諱言,提倡優生學社會政策的人也認為不施行這些政策會帶來極大的風險。當然那只是他們對科學證據的解讀,而如我們所見,這些證據該如何解釋,並未有共識達成。這裡我們又要回頭強調共識。如果可以證明相關領域專家並未達成共識,那公共政策的基礎顯然十分薄弱。這也是為什麼菸草公司長久以來,一直嘗試宣稱科學認為菸草會帶來危害這件事其實沒有那麼確定。如果真的是這樣,他們說菸草管制過於倉促就是對的。同樣地,如果人為氣候變遷還沒達成科學共識,石化產業和自由主義智庫要求更多研究,就是正確的。因此共識研究關係重大,知道共識存在無法讓我們知道該如何面對氣候變遷,但可以告訴我們問題確實存在。
如果確定相關領域的專家已達成共識,下一步呢?我們可以充滿信心地接受他們的結論,以此當作決策依據嗎?我的答案是有條件的肯定。可以,條件是社群有理想運作。這個條件很重要,如同溫恩所說,如果科學想要得到尊重與信賴,那麼「在組織型態、管理方式、社會關係等方面擁有優良的制度,就不只是為了讓科學進入大眾生活而作非必要的渲染,而是批判性社會文化評估的必備元素。」
科學史顯示社群不見得能如理想般達到開放、多元、確實執行轉化型質問,而且通常都做不到(不過沒達成這些理想,影響也不一定會很深刻,有時甚至難以察覺)。歷史學家史塔克指出,美國國家生命倫理委員會建議在審查以人類為實驗對象的研究時,委員會至少要有四分之一成員不隸屬執行該研究的機構,但這個目標很少達成。
我們要如何知道科學社群夠不夠多元、有沒有做到自我批判、讓另類意見有機會發聲?尤其是研究進行初期,有潛力的方法不該太早被否定。我們該如何判斷制度好不好?這裡沒有統一標準。很多科學家對大陸漂移的想法錯了,這不代表現在另一群科學家對氣候變遷的想法也錯了,他們可能對可能錯,我們不能預設立場。
除了檢查高素質的專家社群有沒有達成共識,我們也可以問:
社群中的科學家能接受不同觀點嗎?社群成員是否能代表廣泛的觀點,有不同的想法、理論取向、方法學偏好和個人價值?
是否使用不同的方法和多樣的證據?
不同的意見有沒有機會發聲、被充分考慮和看重?
社群是否對新資訊開放?能否自我批判?
在年齡、性別、種族、族群、性向、國家等面向上,社群的組成是否多元?
最後一點需要進一步解釋,科學訓練的目的是要限制個人偏見沒錯,但所有已知證據都顯示我們沒做到這點,而且可能真的很難。個人偏見很難避免,但可以透過多樣化來校正。不過,真的需要在人口組成上多元,才能讓觀點多元嗎?
關於這個問題最好的答案,是人口多元很接近觀點多元,甚至可以說是能夠促成該目標的手段。一群白人、中年、異性戀男性可能對許多議題看法分歧,但他們也會有盲點,例如在性別或性向上。在團隊中加入女性和酷兒是一個辦法,讓更多本來可能錯失的觀點被納入考量。

這是觀點知識論的基本論點,主要由哈定提出(見第一章)。我們的觀點很大程度取決於生活經驗,比起有男有女的社群,一個全由男性(在觀點知識論上則是全由女性)組成的社群,經驗可能比較狹隘,觀點也可能因此比較狹隘。商業世界有證據支持這點,針對職場性別多樣性的研究顯示,女性加入領導階層有助於公司獲利,但只限於一定比例:60%。如果公司領導階層全部或大部分是女性,這種「多元紅利」就會開始降低。這也的確符合以上論點。
前面提到的問題其實並不容易做到,但如果任何一點沒有做到,通常很容易就會被發現。更常見到的是社群中的某些人性格傲慢、心胸狹窄、自我膨脹(這些實在太常出現了!),但社會學觀點的知識論認為個人的影響不大,重要的是團隊整體足夠多元,公開討論的管道暢通,新證據和新想法有機會傳播。
哲學家道格拉斯論證過,當科學結論帶來的影響不在知識層面,而是關係到道德、倫理、政治或經濟,就無法避免價值觀在不知不覺中影響我們對證據的判斷。(例如自由派可能會比較快接受氣候變遷的科學證據,因為這代表政府可能要干預市場運作,而他們對這點接受度較高。)
因此,一個議題影響社會愈深,研究它的社群就更必須公開且多元。 不過有時候某些議題看似單純、只是知識問題,實際上卻不是。科學家可能會說他們純粹在討論問題的知識面,但實際上不是。這表示無論是什麼議題,科學社群都需要留意多元和開放程度,對新想法保持開放,尤其是得到實證證據支持的想法,或嶄新的理論概念。
例如可以在決定經費補助對象或審查論文時,多加考慮新穎的想法。包容新穎想法最後發現它錯了,應該還是好過因為批判而錯過好的想法。很多科學家非常強調在面對知識時應該表現出嚴厲的態度,實際上還可能流於粗暴,這可能在無意間造成同行不願多言,特別是年輕、害羞或缺乏經驗的科學家。嚴厲很重要沒錯,但保持開放可能更重要。
We have been authorized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o use this conten. 該內容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授權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