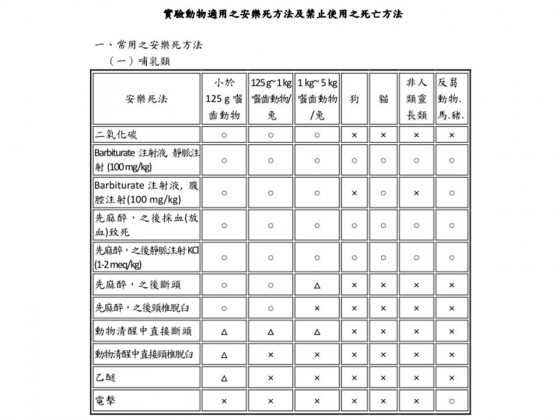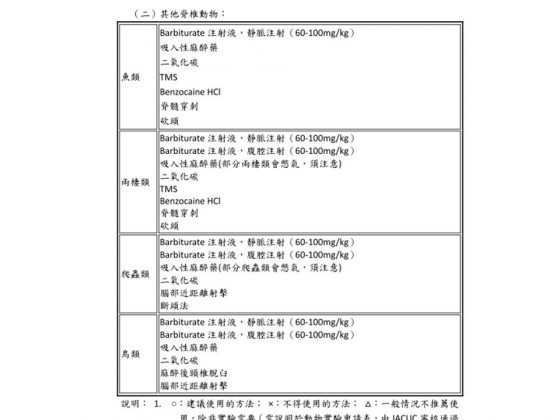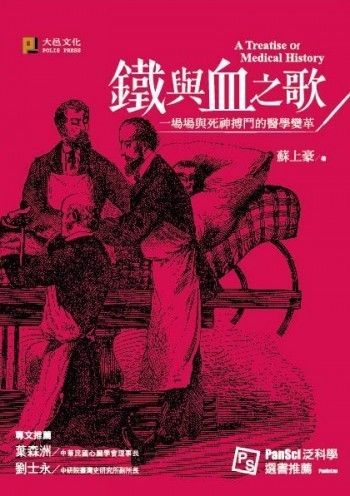
其實,「安樂死」的本意並非如此,它的英文字是由兩個希臘字組合起來:”eu” — good,也就是「好」的意思; “thanatosis” — death,意即是「死亡」,合起來就是”gentle and easy death” —「祥和及輕鬆地逝世」,跟現在英文字典裡的”the act of killing someone painless” —「將某人無痛苦地殺死」的意義幾乎是南轅北轍。
鑑於希臘組合字的艱澀難懂,於是有也有人用「仁慈處死」(mercy killing) 當成是”euthanasia”的替代字,不僅直接,而且也露骨,不需費盡唇舌解釋。
真正第一個使用這個字的人是羅馬帝國的史學家思維托尼亞斯(Suetonius),出現在他有關於羅馬帝國皇帝奧古斯都 (Augustus)的著作《羅馬十二帝王傳》(De Vita Caesarum— Divus Augustus)裡面,一段描述奧古斯都臨終的場景。
幾乎被視為神的羅馬皇帝奧古斯都在彌留時,妻子莉維亞(Livia) 正在旁守候,兩人深情一吻後,他就安詳而無痛苦辭世。這種和中國觀念—「壽終正寢」、「善終」類似的概念,被思維托尼亞斯以「安樂死」來形容,用自創的希臘組合字來描述奧古斯都辭世的情節,才能符合具有「神性」的皇帝面對死亡時應有的待遇。
可惜的是,專注於醫療發展的史料裡,我們卻看到安樂死在歷史的洪流裡成形時,並沒有往類似中國「善終」的方向發展,反而以另一種形式和現代西方的觀念做連結。
歷史學家發現,在古印度,對於沒有治癒希望的患者,通常將其淹死在恆河裡;在古希臘,類似的情形,尤其是極端痛苦、急欲尋求解脫的病人,很容易得到一種解脫的毒藥,連柏拉圖也曾經寫過:「心理與生理極度病重的人,應該讓他們走上死亡之路,他們沒有存活的權利。」至於斯巴達,剛出生的男嬰若被發現有生病及殘障,就會被殺害,以確保他日後不會成為「別人的負擔」。
上述概念,以現今的定義就叫做「主動安樂死」(active euthanasia),有別於「被動安樂死」(passive euthanasia)—指的是放棄所有治療手段,任病患自生自滅。
不過自從羅馬帝國時代開始,這種主動安樂死就被視為是「謀殺罪」,而且當天主教成為主要的信仰後,除了被視為犯法的行為外,上述的行為更被明令禁止,其實最重要的原因是認為上帝才是人類生存的主宰,人沒有隨便終結自己或別人生命的權力。
雖然宗教掌握西方人大半時間的思想與生活,但是在十六世紀,湯瑪斯・摩爾(Thoma s More)的名著《烏托邦》(Utopia) 就提到了安樂死—在烏托邦內,要是病患得了不治之症,那醫師、神職人員及政府的領導人會去找病患談話,希望他能把希望寄託於來世。如果病患同意,他便能得到幫助,在睡夢中無痛苦地死去,至於那些不同意的病患,還是可以得到之前一樣的照顧。
不要以為摩爾贊成安樂死,他的小說是以反諷的方式來表達意見,不是醫師的他只能在小說打造的「理想國」內,以此面對死亡。
同樣的概念也出現 1627 年,另一位知名學者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一本未完成的小說《新亞特蘭提斯》(New Atlantis)裡。培根在書中提到,醫師的職責除了治癒病患外,對於存活無望的病人,也要盡量減輕其痛苦,必要時更要義無反顧讓他們安逸而無痛苦地死去。這種醫療上的狂想,對一個被視為「哲學家」的學者而言,在當時是很前衛的創見,尤其他不喜歡用”mercy killing”這個字眼,反而偏好”palliative”(減輕),來賦予上述的行為意義。
而在達爾文演化學說提出之後,上帝的「造物者」角色受到嚴峻的挑戰,雖然幫助別人自殺在此時仍被視為犯罪,但已經有不少學者相繼提出安樂死的概念,挑戰大環境的禁忌。
例如在 1870 年,知名學者山謬爾・威廉斯(Samuel D Williams),第一次提出「醫療安樂死」(Medicalised Euthanasia)的概念;1889 年,德國的哲學家尼采(Nietzsche)也說,疾病末期的患者是眾人的負擔,沒有權利活在世上;1895 年德國的律師瓊斯特(Jost),曾準備寫一本法律書《殺人的法律》(Killing Law),強調那些無治癒希望的病人想尋死的話,就應該准予他們的請求,因為這些人的生存價值是零。
可以想見,在二十世紀初期以降,各種對於安樂死的論述如排山倒海而來,美國紐約州及奧勒岡州甚至率先提出安樂死的立法,只是最後被駁回;法國醫師弗爾格(Forgue) 也提議,替無法治癒的患者安樂死,在法律上應該被原諒;俄國甚至在 1922 年短暫通過對安樂死的犯罪減刑,不過不久後被國會否決。
無怪乎納粹德國在 1933 年修改醫師宣言,成為德文版的《健康》(Gesundheit)。認為醫師的職責不再是只針對病人的健康,而是為了打造健康的德國—不難想像,這是為了日後屠殺三十五萬不健康、弱智以及同性戀的德國人,以及幾百萬猶太人做好的準備。
接下來的幾十年,甚至到了現在,有關於安樂死的提出及立法倡議不勝杖舉,在此我就不多說了,其複雜與糾結的程度,並非三言兩語可以說完,其探討與論述,甚至可以出好幾本鉅著。
看了這些歷史的演進,其實我很感嘆,原本「善終」、「好死」的安樂死概念,在歷史的軌跡裡,竟然被「醫療的加工自殺」所取代—即使它是利用醫師的專業來協助,減輕末期病患的痛苦。若是思維托尼亞斯地下有知,可能會從墳墓裡出來破口大罵濫用他發明組合字的學者。
我是對「仁慈處死」很有意見,因為醫師在這方面的幫忙是為了減輕病患死亡的痛苦,並非為了促成病患死亡。但是把這種概念類比安樂死讓人更不舒服—要知道在死刑執行方式的改進上,的確有醫師為了讓死刑犯「減少痛苦」而死去,費心改良了行刑工具。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法國的斷頭臺”Guillotine” —這其實是一位醫師的名字。
在法國大革命前,對於死刑的執行是以車裂(breaking wheel)為主(有點類似中國古代的五馬分屍),犯人常在痛苦中哀嚎一段時間才死去,由於太過殘忍,所以法國國會議員,同時也是醫師的約瑟夫・依尼斯・吉爾汀(Joseph Ignace Guillotin)在 1789 年 10月 10 日,提出了對於死刑的六點改進建議,同時希望國王路易十六廢除車裂之刑,改以其他方式替代。
法王路易十六從善如流,廢除了車裂,而改以斬首做為執行死刑的方法,不過犯人被處決時死狀也是相當淒慘,因此國會在 1791 年成立了特別委員會,由國王的御醫、知名的外科醫師安尼・路易士(Antoine Louis)負責(吉爾汀也是委員會其中一員),並且在德國工匠托比亞斯・須密特(Tobias Schmidt)的幫助下,從十三世紀就在英國使用的執行死刑工具哈利法克斯絞架(Halifax Gibbet)得到靈感,改良成現今大家熟知的斷頭臺。
據說,剛開始刀刃容易「卷刃」,略懂工藝技術的法王路易十六還親自參與改良,把它改成斜四十五度角,取代原來的半月型,讓死刑的執行在一瞬間就能完成,以減低犯人的痛苦,達到仁慈處死的目的。
1792 年 4 月 25 日,斷頭臺第一次使用就是處決惡名昭彰的江洋大盜尼可拉斯・雅克・比爾帝(Nicolas Jacques Peiletier)。不僅如此,在法國大革命之後的恐怖統治期間(Reign of Terror),它也出盡鋒頭。一堆王公貴族,連法王路易十六本人,還有知名學者、革命黨人被帶到今日巴黎的協和廣場處決,因而斷頭臺被暱稱為「吉爾汀夫人」(Madame Guillotine)或是「國家的剃刀」(the National Razor),估計有好幾萬人被斷頭。
斷頭臺自此被稱為”Guillotine”,讓不是設計人的吉爾汀醫師的後代背負極大的惡名,曾經要求法國政府將其易名,但是未獲批准,於是他們被迫改名易姓,免得再和這個殺戮工具扯上任何關係。
另一個現代執行死刑的要角—藥劑注射(lethal Injection)也是由醫師所設計,目的當然希望和斷頭臺被發明一樣,減輕死刑犯行刑中的痛苦。
這種利用化學藥劑執行死刑的概念,首先是在 1888 年由紐約的醫師朱里亞斯・孟特・布萊爾(Julius Mount Bleyer)提出,不過當時他的想法並不如你我想像那樣高尚,只是認為這種方式花費比較便宜,不需像其他死刑那樣勞師動眾。
美國執行死刑的方式從十九世紀也經歷了多次變革,從絞刑、火槍隊槍決、坐電椅、進毒氣室等等,目的也是所謂仁慈處死,但常有一些失手,如槍法不準、電椅起火燃燒、犯人在毒氣室哀嚎,促使了醫師提出了更「人道」的方式。
1977 年,在美國奧克拉荷馬州的醫師傑・契普曼(Jay Chapman)建議一種較為人道的執行死刑方式,就是利用三種藥劑先後注射,讓死刑犯能較不痛苦死去,這種俗稱「雞尾酒」(cocktail)的方式,得到了曾經是奧克拉荷馬大學醫學院的前麻醉科主任史坦利・杜曲(Stanley Deutsch)的認同,教士比爾・懷斯曼(Bill Wiseman)則向當局提出立法的要求,很快獲得通過,而德州在 1982 年也仿效此一立法。不久此俗稱為「契普曼實驗方案」(Chapman’s protocol)的行刑方式,便處決了第一個死刑犯。
化學藥劑處死的方法,從 1982 年以來,雖然有美國三十幾個州,和其他諸如菲律賓、中華人民共和國及越南的跟進,但是其實施時也是狀況百出:有犯人打了兩次藥,如同被凌遲一樣,哀號了三十幾分鐘才真正死亡;也有找不到犯人靜脈,因此延遲了死刑,犯人的辯護律師還據此提出違憲的訴訟;還有犯人最後雖然死亡了,卻也在過程中苦苦掙扎,對獄卒親口講述等死的痛苦⋯⋯讓減輕痛苦的死刑,在外人看起來一點也不慈悲。
從有著「壽終正寢」與「善終」概念的安樂死,談到有醫師介入的「醫療安樂死」,最後再論及醫師設計的人道死刑執行方法,相信不是只有我,讀者們可能會覺得混淆,甚至有些人會感到錯亂,誰會想到身負救人使命的醫師竟因為慈悲的理由,變成加工自殺、仁慈處死的參與者與設計者?
至於你問我感想為何?我只有簡單一句話,任何一種「慈悲的殺戮」我都沒有興趣參與。上天有好生之德,從醫二十幾年,鑽研「救人」的方法都來不及了,哪有什麼興趣去發明「助人好死」的方法!
摘自泛科學2014八月選書《鐵與血之歌:一場場與死神搏鬥的醫學變革》,大邑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