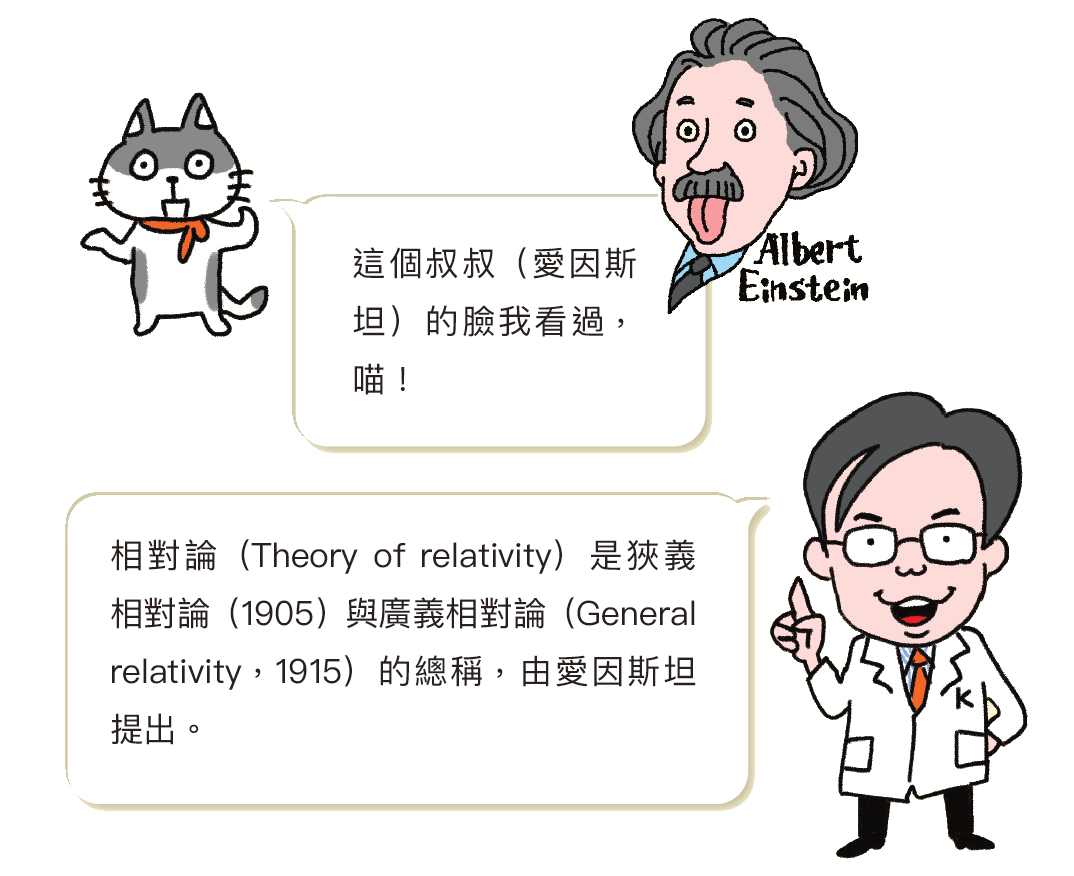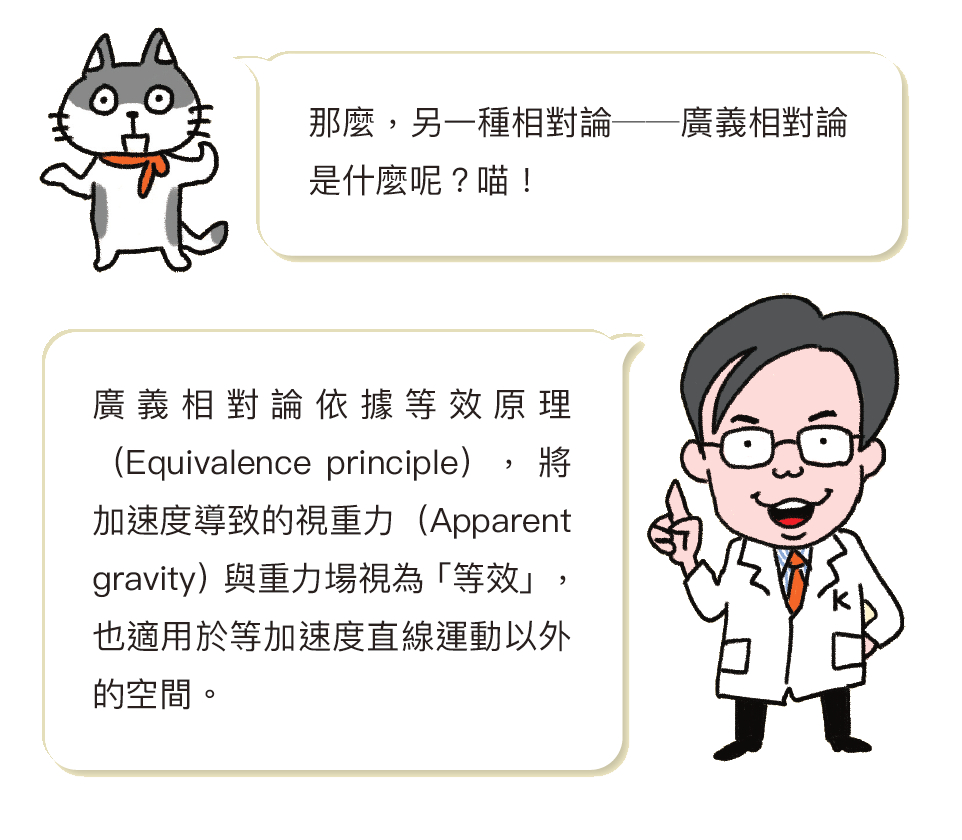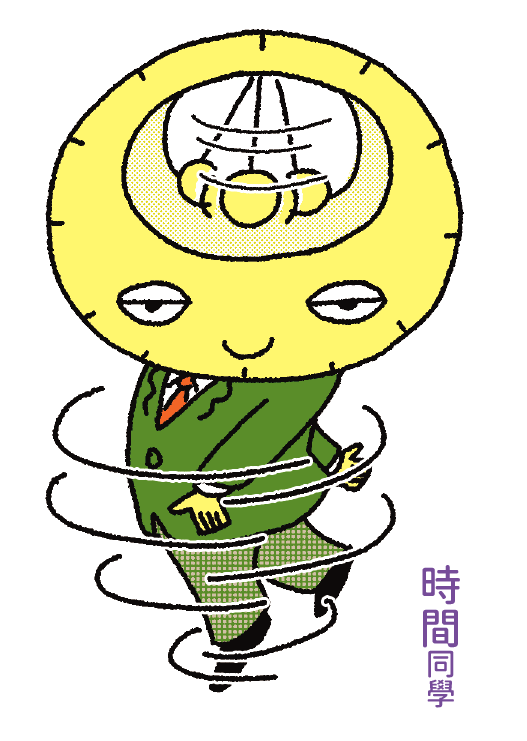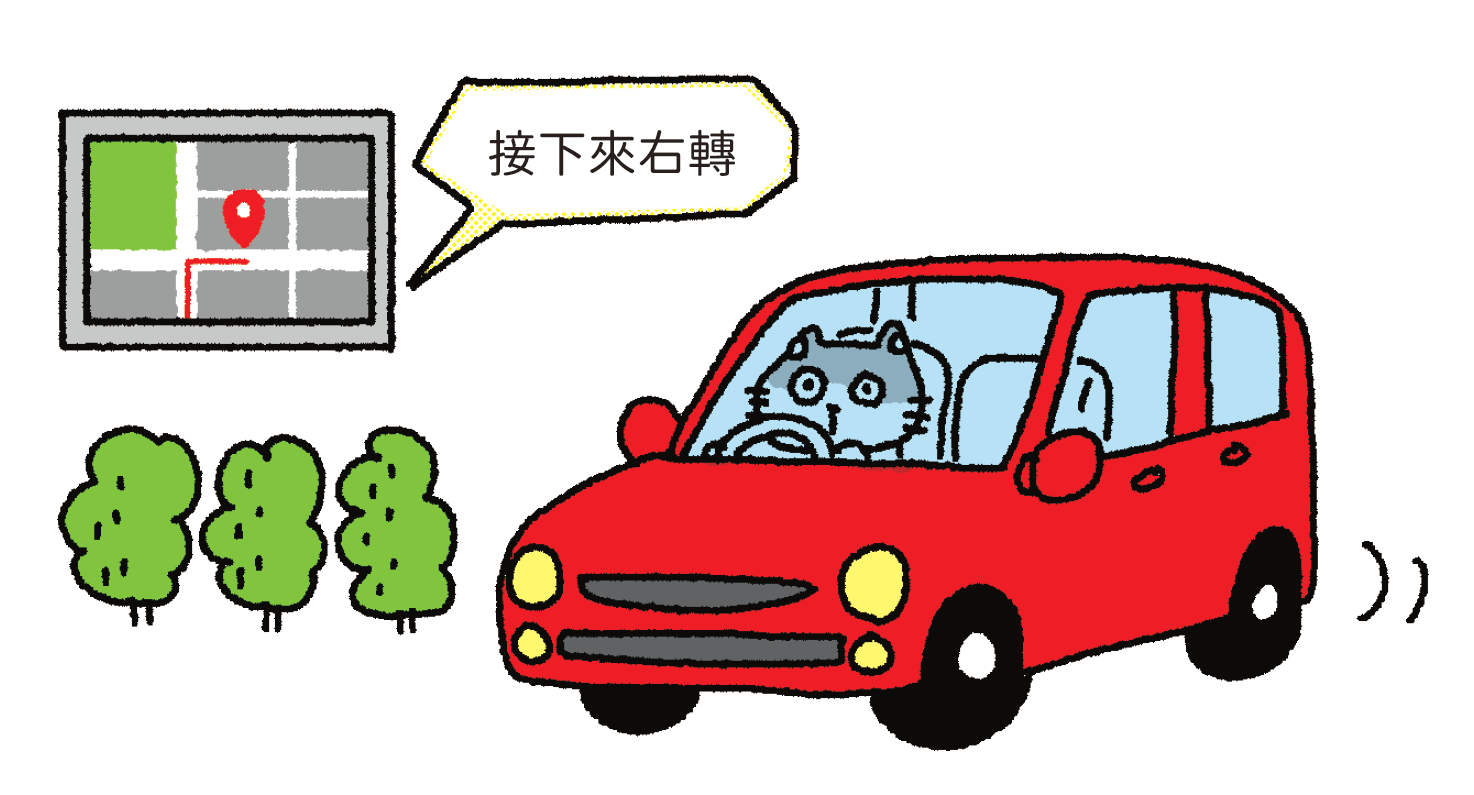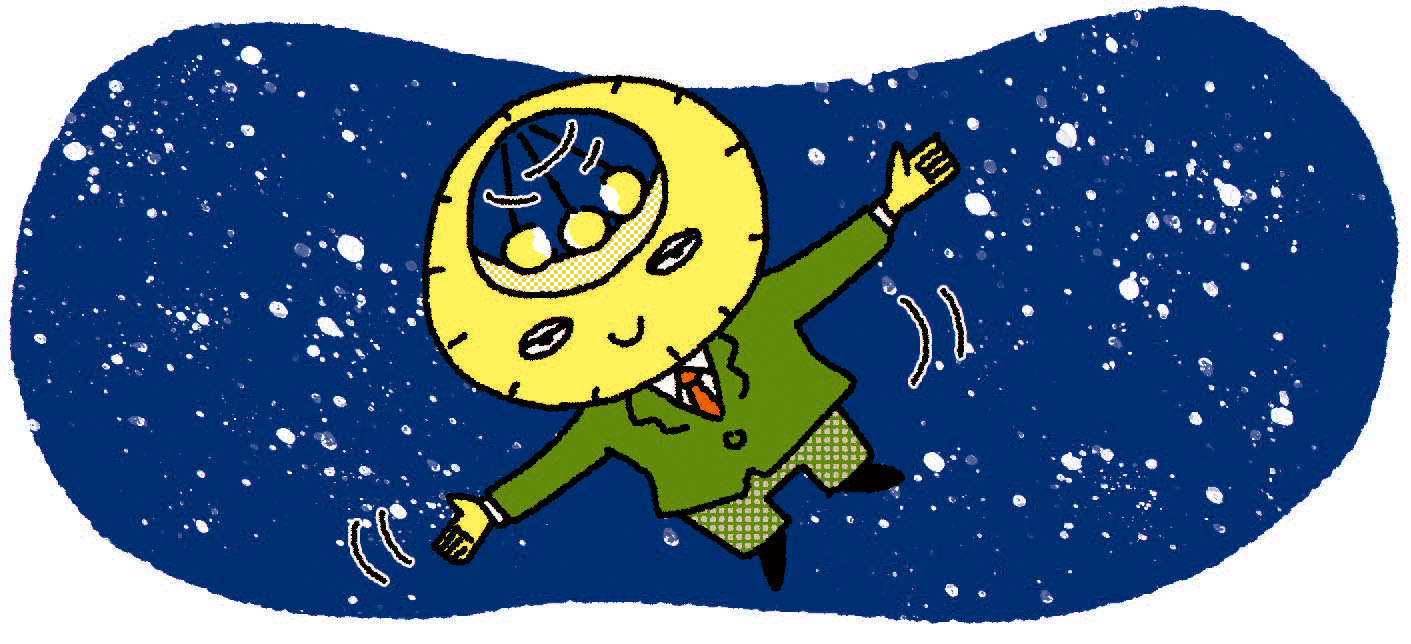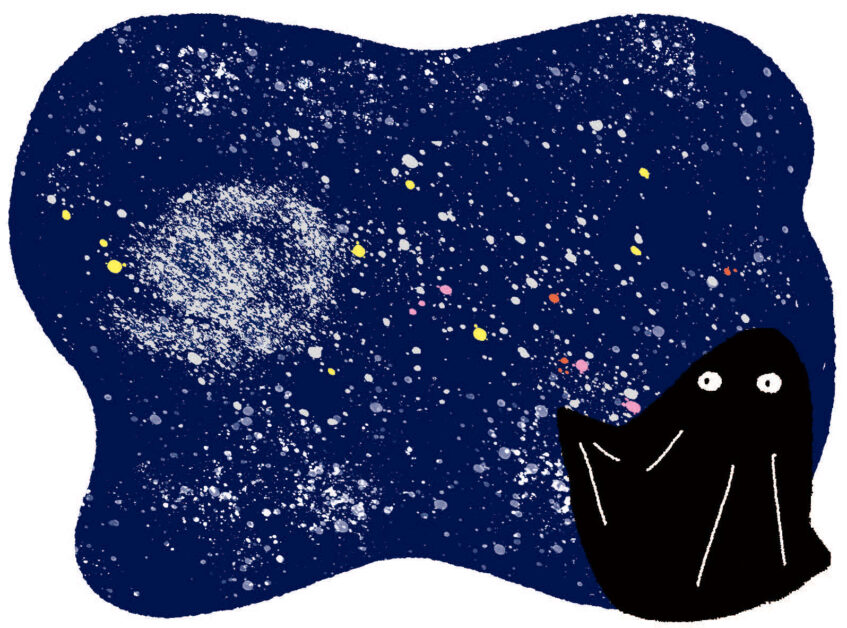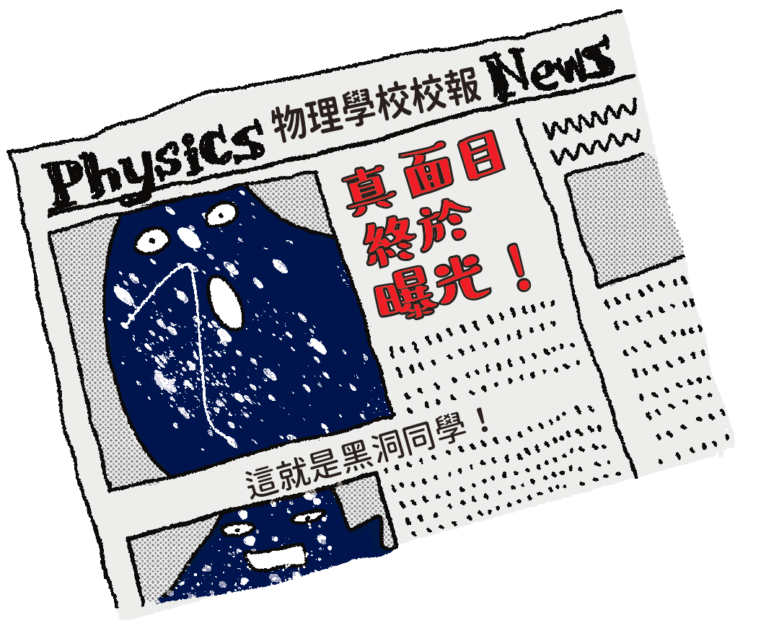本文轉載自顯微觀點
攝影之前的顯微傳播 在顯微鏡已是博物學家必備工具的 19 世紀中葉,銀版攝影技術才剛發明不久,結合兩者的顯微攝影(photomicrograph)隨之邁出第一步。但顯微攝影直到 19 世紀末才真正普及化、以客觀與速度成為自然科學研究的技術。
在此之前,由繪圖師在顯微鏡前臨摹描繪是顯微影像 200 年來的記錄與傳播方法,從休閒式的顯微圖鑑,到科學界的分類學文獻,都有賴精細可信的顯微繪圖。當時的分類學家或解剖學家經常培養出顯微繪圖能力,但與顯微繪圖師分工可以提升效率與美學。儘管有投影描繪器(camera lucida)可作為素描輔助,每個顯微繪圖師的筆觸還是會呈現鮮明的技巧與個人風格差異。
韋斯特(Tuffen West)是維多利亞時代最為人稱道的顯微繪圖師之一,職業生涯長達四十年,以精美版畫將成千上萬種生物型態傳達讀者眼前。他的顯微繪圖可見於醫學、動植物與微生物的科學著作與期刊,並在後世被評論為藝術品,盛年時往往受到最負盛名的博物學家與科普作家雇用。同時,他也是積極的博物學家和顯微技術推廣者。
失去聽力 放大視覺 1823 年,韋斯特出生於英格蘭約克郡。父親是個熱衷化學實驗的藥師,在不列顛科學促進會 (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Advancements of Science ) 位居要職。韋斯特從小就展現對自然與博物學的興趣,他一面按照父親的安排習醫,一面維持蒐集動植物標本的愛好,他 19 歲時發表的鳥類比較解剖學論文贏得了一筆可觀的獎金。
韋斯特 22 歲那年,他的醫學生涯戛然而止。他在父親的化學實驗室遭遇爆炸,幾乎完全失聰,失去行醫的基本能力。但他繼續使用顯微鏡觀察樣本,並開始練習版畫技術;在 25 歲時完成第一幅署名的版畫,並在 27 歲受女王學院雇用,為矽藻進行一系列顯微繪圖。
石版印刷:科普浪潮的技術基礎 韋斯特兄弟為 《顯微鏡前的半小時》 繪製的自然樣本顯微版畫。 Coutresy of NIH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韋斯特的弟弟威廉(William West)是在倫敦執業的版畫家及印刷匠,曾為達爾文繪製《物種起源》第一版的物種樹狀圖(也是該版唯一的圖片)。兄弟兩人經常合作為醫學著作繪畫製版,通常是韋斯特繪畫,威廉製版。儘管最後韋斯特的科學繪圖作品豐碩許多,但他最初的版畫技術很可能是由威廉傳授。
這對兄弟對版畫內容的志趣可能不同,但對美學有著共同的堅持。他們經常在作品下方註明,使用彩色平版印刷(Chromolithography)技術,而非新穎的技術競爭對手—石板淡彩畫(Lithotint)。
1796 年發明的石版印刷,在新世紀成為廣受歐洲各國歡迎的大量圖片複製技術,科學刊物中的印刷版畫,無不經過「繪圖、製版、印刷」三道工序。其中製版的工藝關乎圖畫如何呈現在出版物上,對美感與技術的需求不下於繪製原圖。
19 世紀早期流行的彩色平版印刷中,每一種顏色需要一塊獨立的石板,每一塊石板的圖案必須精準對齊,以繁複的工藝堆疊出豐富亮眼的色澤。而石板淡彩畫每一幅圖畫則只需一塊石板,效率高、成本低,但能表現的顏色有限。韋斯特兄弟堅持較費工夫,色彩美感更為豐厚的彩色平版印刷。
醫學與公衛潮流中嶄露頭角 韋斯特在解剖學繪圖成名的一系列作品也源自其家族成員,他的連襟、口腔醫學之父哈欽森(J. Hutchinson)。哈欽森出版的眾多創新醫學著作包含壁蝨、梅毒、豬囊蟲感染病徵的顯微圖像,都由韋斯特兄弟繪製。他們持續為哈欽森創立的新希德南協會(New Sydenham Society)出版物作畫,合作直到威廉過世。
透過著重翻譯歐陸醫學文獻的新希德南協會,韋斯特兄弟得以觀察、繪製當時嶄新的顯微解剖構造。例如,荷蘭精神疾病與癲癇研究奠基者:施洛德范德柯克(J. Schroeder van der Kolk)涵蓋脊髓到延腦的解剖學報告。韋斯特兄弟的工藝描繪出繁複寫實的神經細胞、腦葉解剖圖,將歐陸最新醫學知識帶到英國讀者眼前。
韋斯特兄弟為新西德南協會繪製、印刷的腦部解剖圖,這是從腦部下方觀察的角度。Courtesy of P. Paisley 韋斯特的生涯起步階段深受 19 世紀英國的重大瘟疫與食安議題影響。他曾參與公衛先驅哈索爾(A. H. Hassall) 的病源調查任務,在 1855 年倫敦霍亂疫情後,出版檢驗市內民生用水的《各處水質顯微檢驗》。
水質檢驗報告中生動的微生物繪圖,皆由繪圖師前輩米勒(H. Miller)作畫,韋斯特製版。透過精細均衡的版畫成品和大眾對水質的關注,韋斯特奠定了技術細膩的名聲。
後來,哈索爾以《刺胳針》期刊曝光當時常見的食品摻假惡行時,持續與小有名氣的韋斯特合作繪圖,以寫實顯微圖像向大眾呈現來自倫敦四處商販的食品樣本。
直到食品摻假報告集結成冊,哈索爾才在序言說明,他多年前的醫學成名作《人體的顯微解剖:疾病與健康》也包含許多韋斯特的畫作,那是韋斯特參與的第一個科學顯微繪圖作品,合作期間哈索爾還讓初出茅廬的韋斯特住在自己家裡,在充沛的支援下工作。可惜的是,哈索爾的主要著作中,多數顯微繪圖都沒有畫家署名,因此無法判斷哪些繪圖是由韋斯特繪圖或製版。
哈索爾、米勒、韋斯特合作的倫敦水質研究版畫:Serpentine Water of Hyde Park. Courtesy of Wellcome Collection. 畫筆風靡大洋兩岸 醫學領域以外,韋斯特也用鮮明精密的畫風描繪博物學圖像。史密斯(W. Smith)所著《不列顛矽藻概要》裡面層次豐富、色彩飽滿的顯微繪圖,使韋斯特作品在博物學家、科普讀者間一時洛陽紙貴。
韋斯特因此受到海洋生物學先驅、水族館創始人葛斯(P. H. Gosse)邀請,合作出版科普讀物。身為博物學家的葛斯具備出眾的顯微繪畫技能,甚至比 19 世紀末聞名歐洲的博物學兼繪畫家海克爾(E. Haeckel)更具聲望。受到葛斯邀請繪圖,表示韋斯特已躋身當時最傑出的顯微繪圖師行列。
葛斯的著作《顯微鏡前的夜晚》 是當年大西洋兩岸最受歡迎的科普著作。書中以創造論解釋生物型態多樣性的宗教觀念、鮮明多樣的生物插圖廣受歐美讀者歡迎。韋斯特與著名的解剖學家兼科學畫家福特(G. H. Ford)合作為本書繪圖,但兩人都沒有署名,難以分辨書中精湛的繪圖分屬哪位作者。
葛斯本人是畫工出色的科普作家,但他仍雇用韋斯特為其著作繪畫。圖為葛斯在《不列顛海葵與珊瑚》中自行繪製的 5 種海葵。Courtesy of Wikimedia 韋斯特也曾為當時最熱門科普作家伍德(J. G. Wood)巨著《博物學》作畫。伍德的作品包含從藻類、草履蟲到寵物犬等生物萬象,他的文字和韋斯特的繪圖深刻影響讀者對生物多樣性與人類起源的想像。當時知名文學家如馬克.吐溫和柯南.道爾都曾在小說中引用伍德的科普內容。
離開顯微鏡,韋斯特的巨觀博物學繪圖依然出色,尤其是針對節肢動物。蛛形動物學開拓者,布萊克沃(J. Blackwall)的《不列顛與愛爾蘭蜘蛛史》、維多利亞時代罕見的女性昆蟲學家史戴維利(E.F. Staveley)的《不列顛蜘蛛》都由韋斯特繪製版畫。栩栩如生的細節、緊密的版面,彰顯了韋斯特博物學繪圖的特色。
韋斯特受雇進行顯微繪圖時,通常由博物學家郵寄為他特製的顯微玻片,讓他自行細細觀察、從容描繪。令人好奇的是,韋斯特的蜘蛛博物學版畫上,總是註明 ”sc. ad nat.” 表示他觀察自然樣本(after nature)進行描繪,而非臨摹他人作品。或許,這些蜘蛛也是由郵差送到韋斯特手上的。
韋斯特兄弟為布萊克沃所著圖鑑繪製的蜘蛛版畫,從針對眼睛、足部的細節可見當時顯微鏡觀察實體樣本的能力。Image source: Bee, L., Oxford et al. 圖文交織,拓展微觀 除了陸地生物,韋斯特為專書、期刊描繪的主題包括有孔蟲、單細胞動物、從海葵到鯨豚等海洋生物,栩栩如生的彩色圖畫拓展了大眾對博物學的興趣。
其中一群可能受彩色圖畫吸引而親近博物學的目標讀者,就是維多利亞時代的中上階層女性。她們雖曾受高等教育、具備社會地位與經濟資本,卻無法加入學會,也罕有機會研究自然、從事博物學相關職位。
例如,倫敦雅典娜俱樂部(The Athenaeum Club),這個以希臘女神為名、服從英國女王的組織,在19世紀初成立時,已經是科學、藝文、法政菁英紳士踴躍參與的知性俱樂部,卻直到2002年才開放女性成為會員。當年俱樂部中的動物學家如瓊斯(T. R. Jones)就強調利用「女性感興趣的」的自然題材、韋斯特栩栩如生的繪圖來吸引維多利亞時代女性讀者。
在林奈學會記錄中,韋斯特謙稱自己是顯微繪圖師,博物學只是業餘愛好。但是他在顯微技術推廣的成果,遠遠超出單純繪圖師的工作範疇。
韋斯特曾推出一系列的顯微知識專欄文章,分享自己的研究心得。1860年代在《休閒科學》(Recreative Science )上著重於他早期對矽藻的蒐集與觀察。1880至1890年代的〈顯微鏡前的一小時〉〈顯微鏡前的30分鐘〉(專欄命名顯然是模仿暢銷書《顯微鏡前的半小時》)則大幅擴展,包含微生物、種子、昆蟲器官的顯微素描以及顯微鏡操作技巧等。
經常以郵件接收顯微樣本的韋斯特在 1875 年成為「郵政顯微協會」(Postal Microscopical Society)主席。該組織建立各地顯微愛好者交流樣本與知識的平台,並在月刊上評析會員們郵寄分享的最新玻片。韋斯特對樣本的縝密觀察與評論,是當時會員們最為珍視的回饋。
韋斯特依據博物學家梅波(W. Maples)原畫繪製而成的蝸牛口器顯微木板畫,後交由埃凡斯印刷。由此可見當時博物學繪圖的多層分工。 全能的科學傳播者 推廣顯微知識的行動中,韋斯特不僅從事評析或繪圖。在他參與的兩本暢銷科普讀物《顯微鏡前的半小時》《顯微鏡下的常見物體》中,他負責篩選樣本、精工製圖,科普作家再以這些顯微繪圖為核心寫作。韋斯特的選樣和繪圖決定了整本書的走向。
《顯微鏡前的半小時》文字作者蘭卡斯特(E. Lankester)在第二版序文中,感謝韋斯特精采的顯微版畫,搭配「作者」的後續著述介紹,在市場上大受歡迎。蘭卡斯特認為韋斯特佔據首要功勞。
與科普作家伍德合著《顯微鏡下的常見物體》時,韋斯特不僅擔任挑選顯微樣本、繪製版畫(此步驟決定了後續文字的走向),也負責印刷的校樣,責任比文字作者更加吃重。此書獲得讀者們熱愛,持續再版直到20世紀。
主導了兩本堪稱史上最受歡迎的顯微科普書,韋斯特卻不曾以作者名義出版專書。他曾在科學期刊發表數篇博物學論文,涵蓋植物、昆蟲、矽藻的顯微構造,採樣與觀察、寫作與繪圖都由他一手包辦。
韋斯特為《顯微鏡前的半小時》所繪的植物博物學版畫。Courtesy of NIH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據佚名資料,蒼蠅足部型態的比較形態學研究是韋斯特最得意之作。韋斯特在 1860 年代發表的矽藻博物學與蒼蠅足部論文,在西元 2020 年後依然有科學家引用。
在《顯微鏡下的常見物體》的出版過程中位居要角的韋斯特,在初版書名頁與印刷者並列,重要性僅次於作者伍德。但隨著版本演進,在 1949 年的再版中,韋斯特的名字已完全消失了。
同樣熱銷的科普圖書《顯微鏡前的半小時》出版歷程中,韋斯特也遭逢一樣的命運。儘管文字作者蘭卡斯特曾表示韋斯特的貢獻最為重要,但是他的名字卻在 1876 年及其後的各版本付之闕如,此時韋斯特的顯微繪圖與科學寫作工作也幾乎停擺。
空白與堅持 韋斯特在 1864 年前後,以及整個 1870 年代都遭遇生產力低落的問題,問世的畫作與文章寥寥無幾。直到 1882 年後,韋斯特才穩定地為期刊作畫並刊載科普專欄,但再也沒有產出研究論文或專書版畫。
創作死寂的階段,正是韋斯特頻繁進出精神療養院的歲月。他的症狀缺少明確醫療記錄,但研究者認為,頻繁的住院符合躁鬱症的週期特徵。
1862 年起,壯年的韋斯特病況不斷起伏,不時住院。即使到他退休後,依然無法逃脫精神症狀的折磨,1879 到 1883 年間,花甲之年的韋斯特在精神療養院裡度過了 31 個月。從首次入院到 1891 年過世,他在療養院居住的時間總和超過 60 個月。
韋斯特在逝世前 6 年寄信給林奈學會,表示自己受困於健康狀況,無法進行科學活動,只能滿懷遺憾地自請退出。
在文明劇烈變遷的 19 世紀後半葉,不少知名藝術家深受精神症狀所苦。梵谷(V. van Gogh)、孟克(E. Munch)和韋斯特的同胞,愛貓畫家韋恩(L. Wain)。這些藝術家的精神症狀影響繪畫風格,但並未阻止他們繼續創作,甚至成就他們名留青史的傑作。
可惜的是,定位自己為「顯微藝術家」(microscopic artist)而非傳統藝術家的韋斯特,沒能找到精神失調與繪畫結合的創作出口。
韋斯特 1886 出版文章搭配的繪圖,品質與早年作品頗有落差。Courtesy of Dolan J. R. 繪圖與研究的生產力遠非韋斯特失去的最重要事物,他在即將成為醫師時失去聽力;他在新婚三年後(1860年)不幸喪妻,並在不久後開始進出精神療養院;在 1875 年,他青春期的兒子離開人世。
造化弄人的是,韋斯特分別在喪妻與喪子的年份,獲選為林奈學會成員與郵政顯微協會主席。遭遇精神疾病之後,他的科學繪圖產量從未恢復,但也不曾放棄推廣顯微科學,直到 1891 年逝世前,他仍在持續整理、刊登過去的顯微素描與筆記。
玻片之後的隱形人 58 歲就自稱退休的韋斯特留下不到 1000 件署名作品,沒有水彩畫展、自畫像的紀錄。以當時顯微版畫行情來看,韋斯特很難平衡他的家庭開支,但他留下 500 英鎊的遺產,表示他的報酬可能高出其他顯微繪圖師甚多,或者他還有許多未署名的畫作在維多利亞時代流傳。
如同韋斯特的貢獻在解剖學教科書出版多年後才被哈索爾公布,或是在科普暢銷書的再版生命中逐漸湮沒,功勞被忽略似乎是維多利亞時代顯微繪圖師的常態。隨著科技演進,顯微繪圖這個職業在 20 世紀初不可避免地被顯微攝影取代。
從 19 世紀的博物學到現代學術工作,在科學上得到信賴、美學上得到讚賞的顯微影像,都由許多人的技術與心力交織而成。當精彩的顯微影像映入眼簾,不妨也看看研究主持者之外,還有哪些猶如現代顯微繪圖師的影像技術人員隱藏在這幅微觀風景之後。
韋斯特最得意的博物學論文中,關於矽藻和蒼蠅足部構造的繪圖。Courtesy of Dolan J. R . 參考資料
Dolan, J. R. (2021). Tuffen West FLS, FRMS (1823-1891): artist of the microscopic, naturalist, and populiser of microscopy. Arts et sciences , 5 (1).
Paisley, P (2015).The Tuffen you probably missed, and some you’ve never seen. microscopy-uk.org
Paisley, P (2016). More Tuffen you possibly didn’t notice. microscopy-uk.org
查看原始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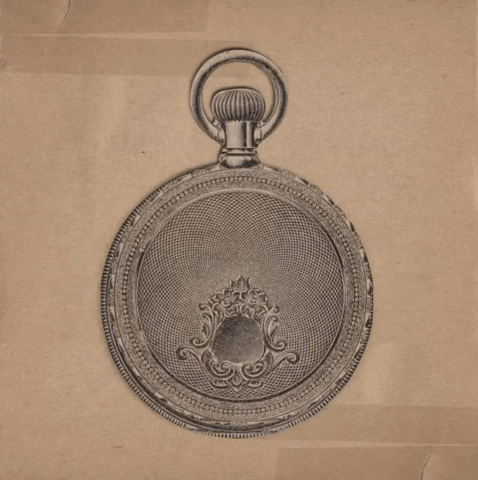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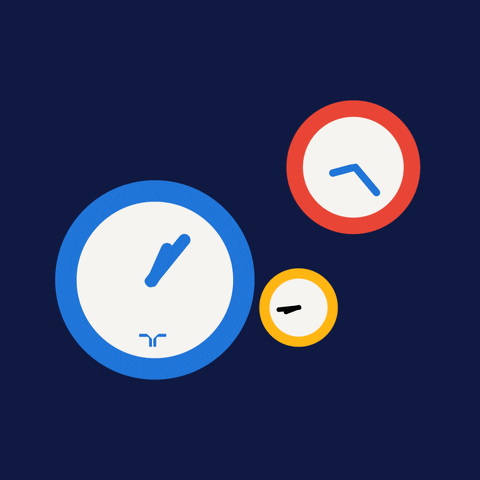

的漫畫「幾點鐘是什麼意思?」.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