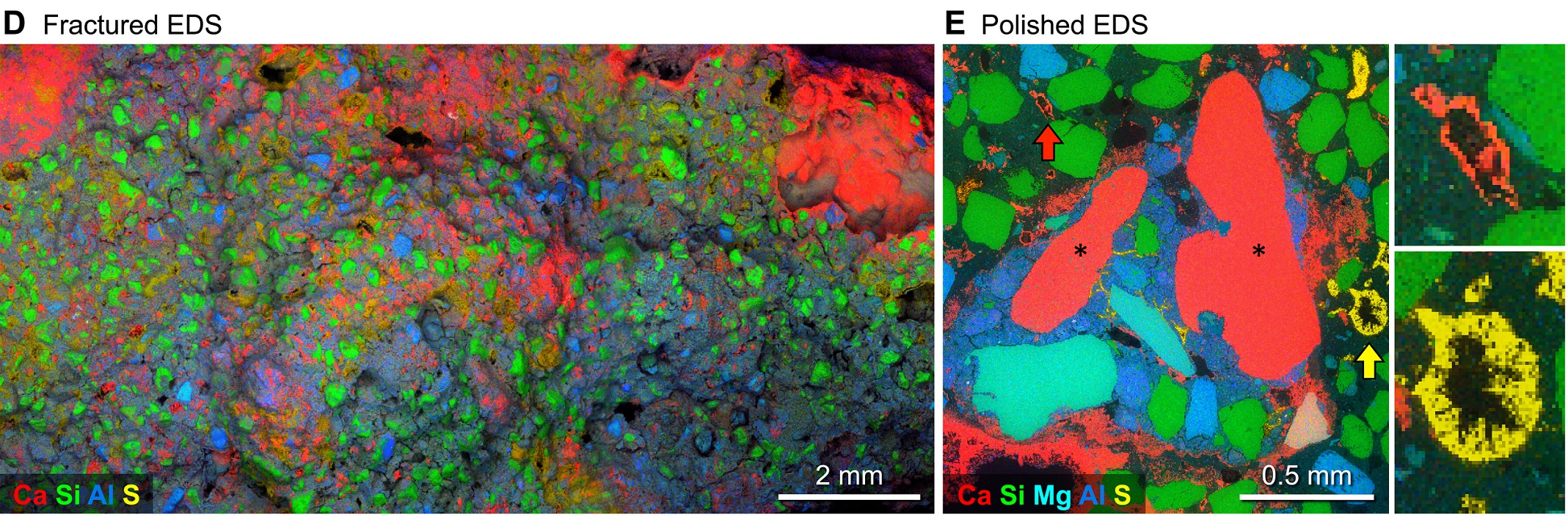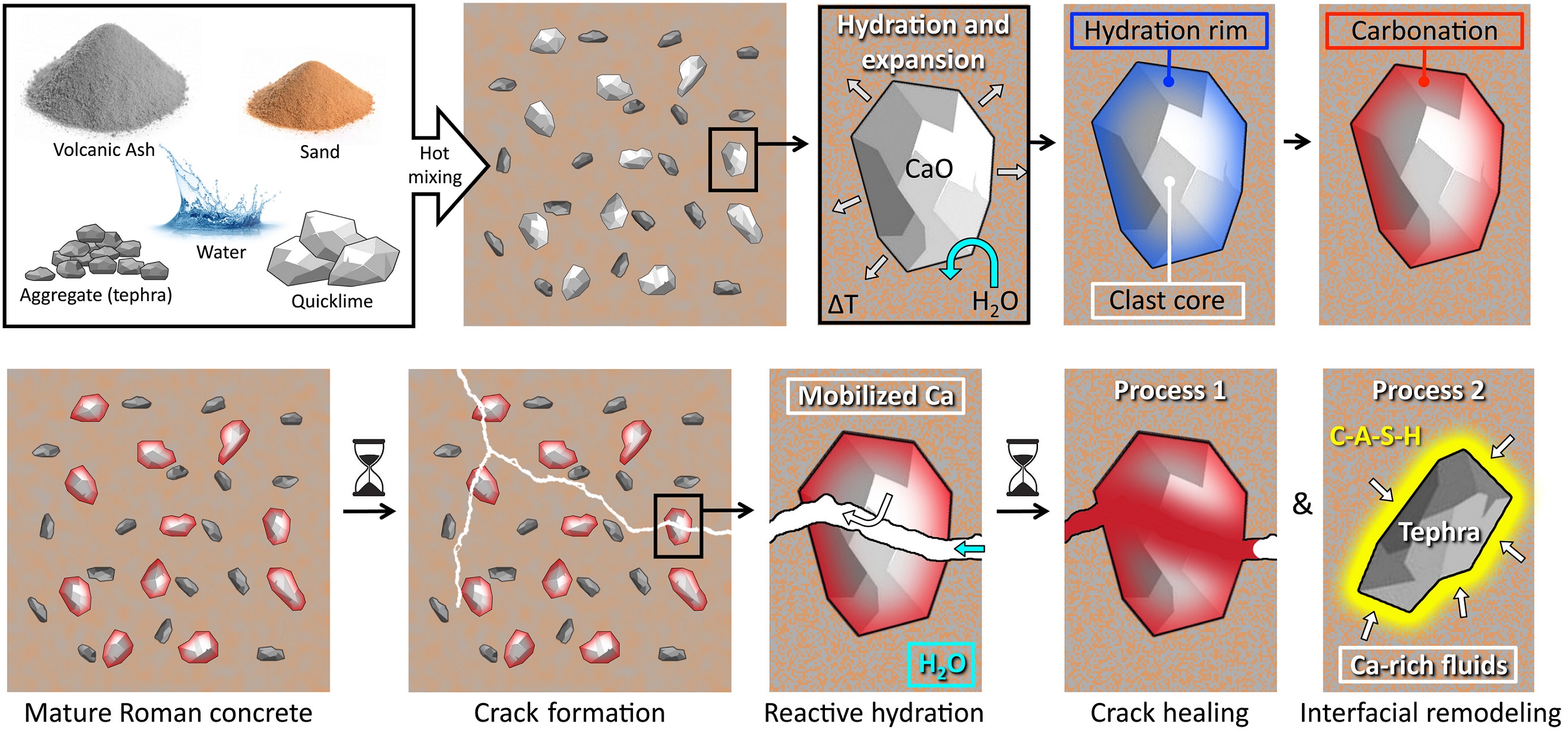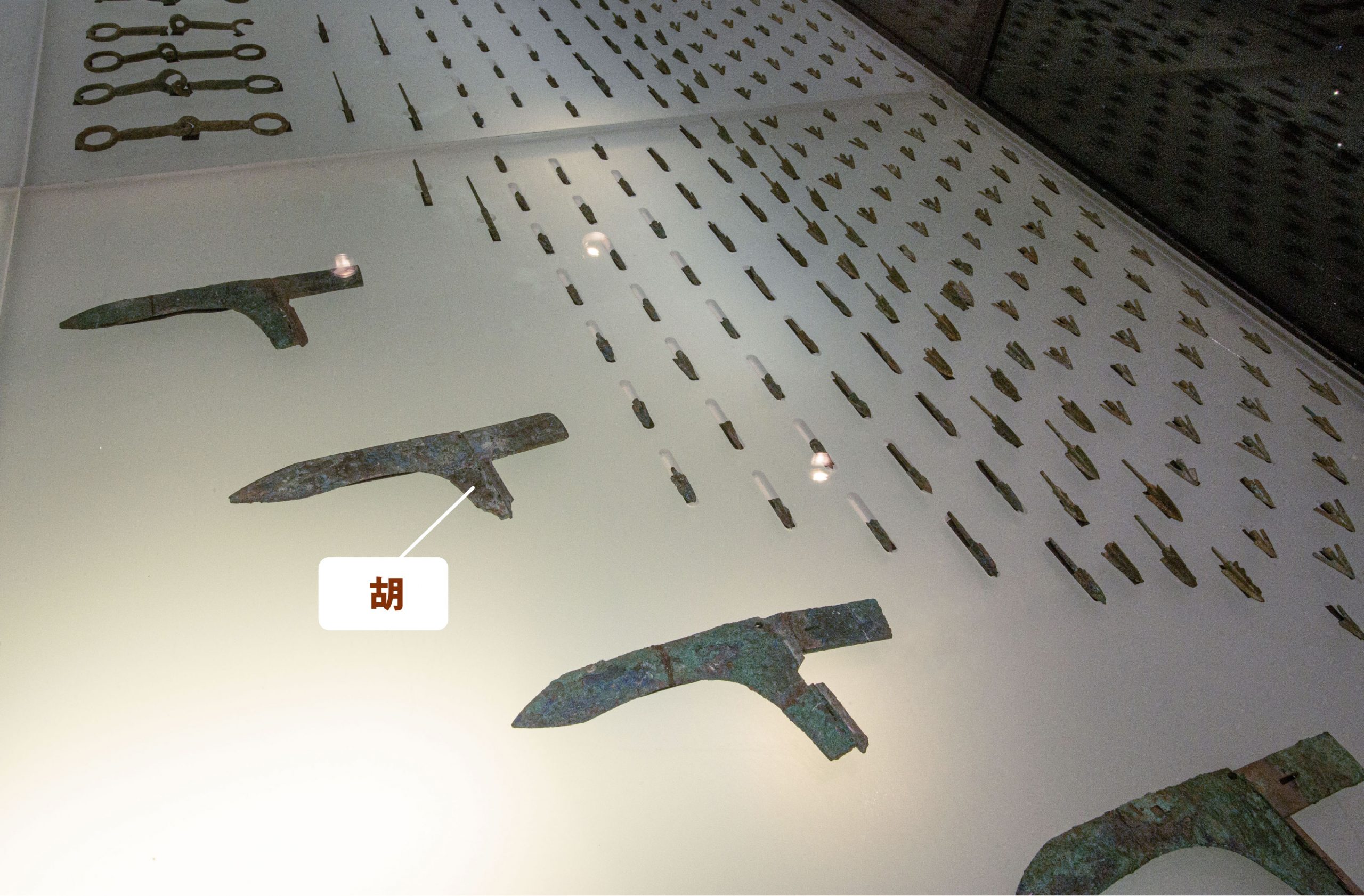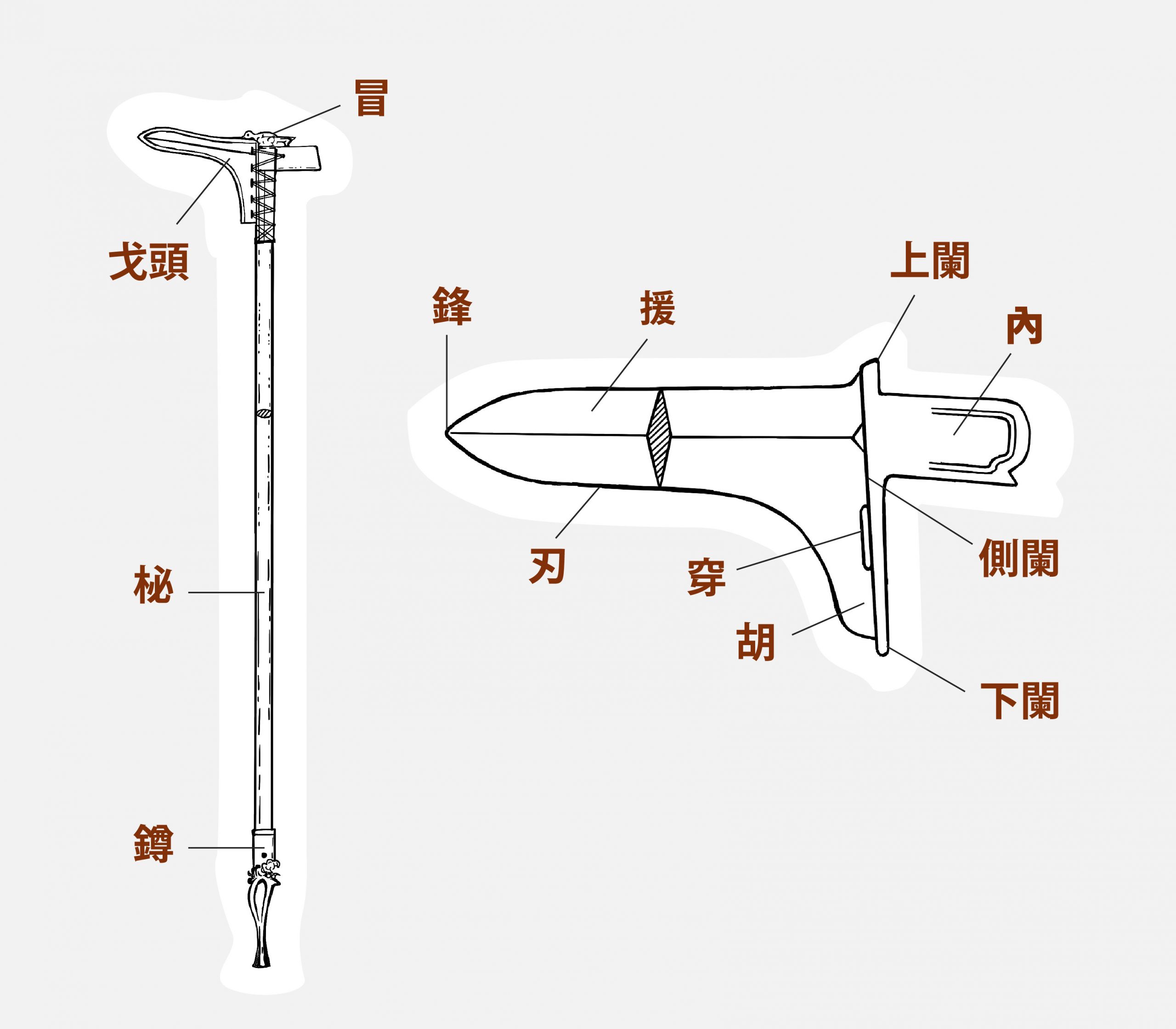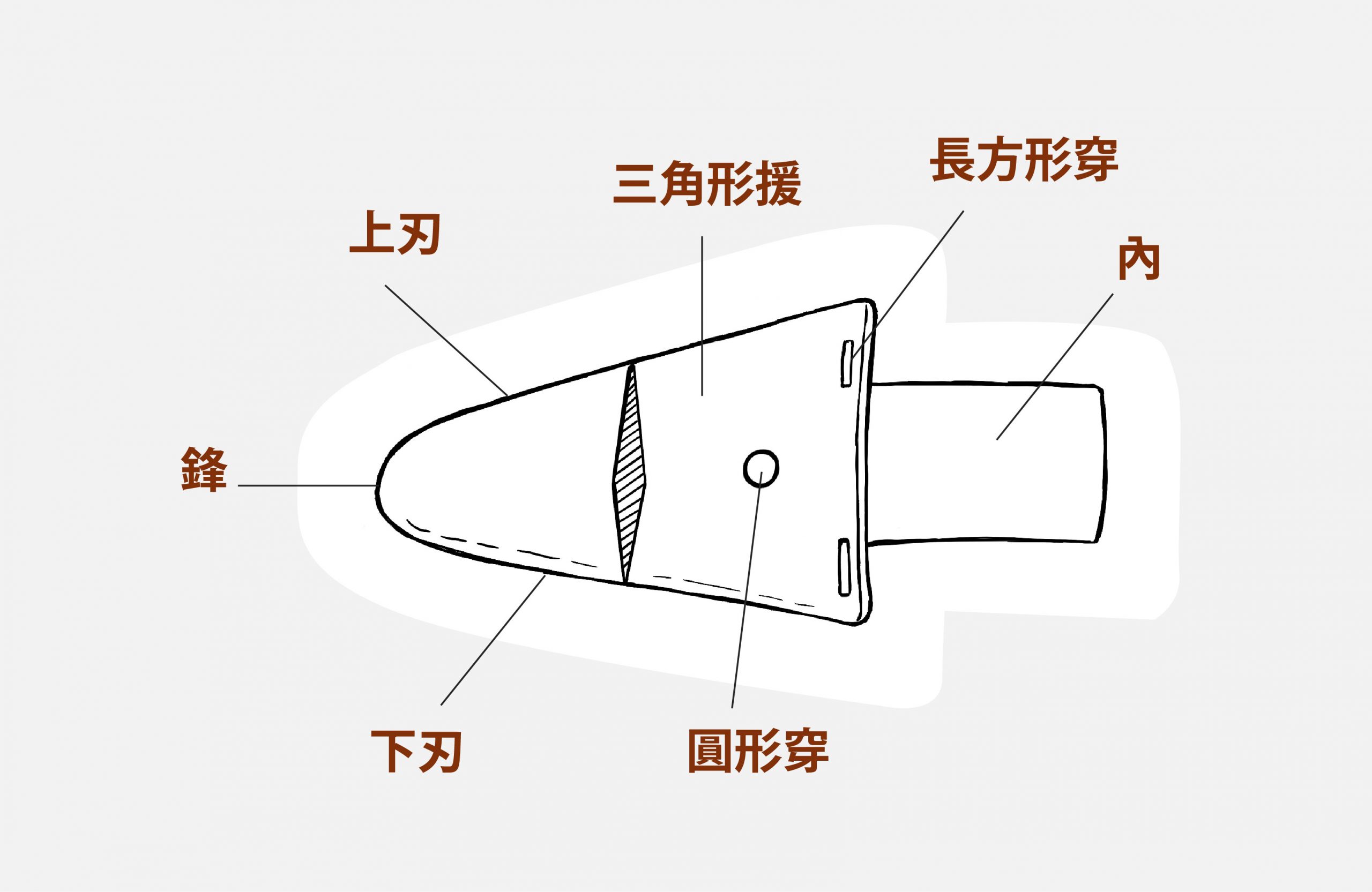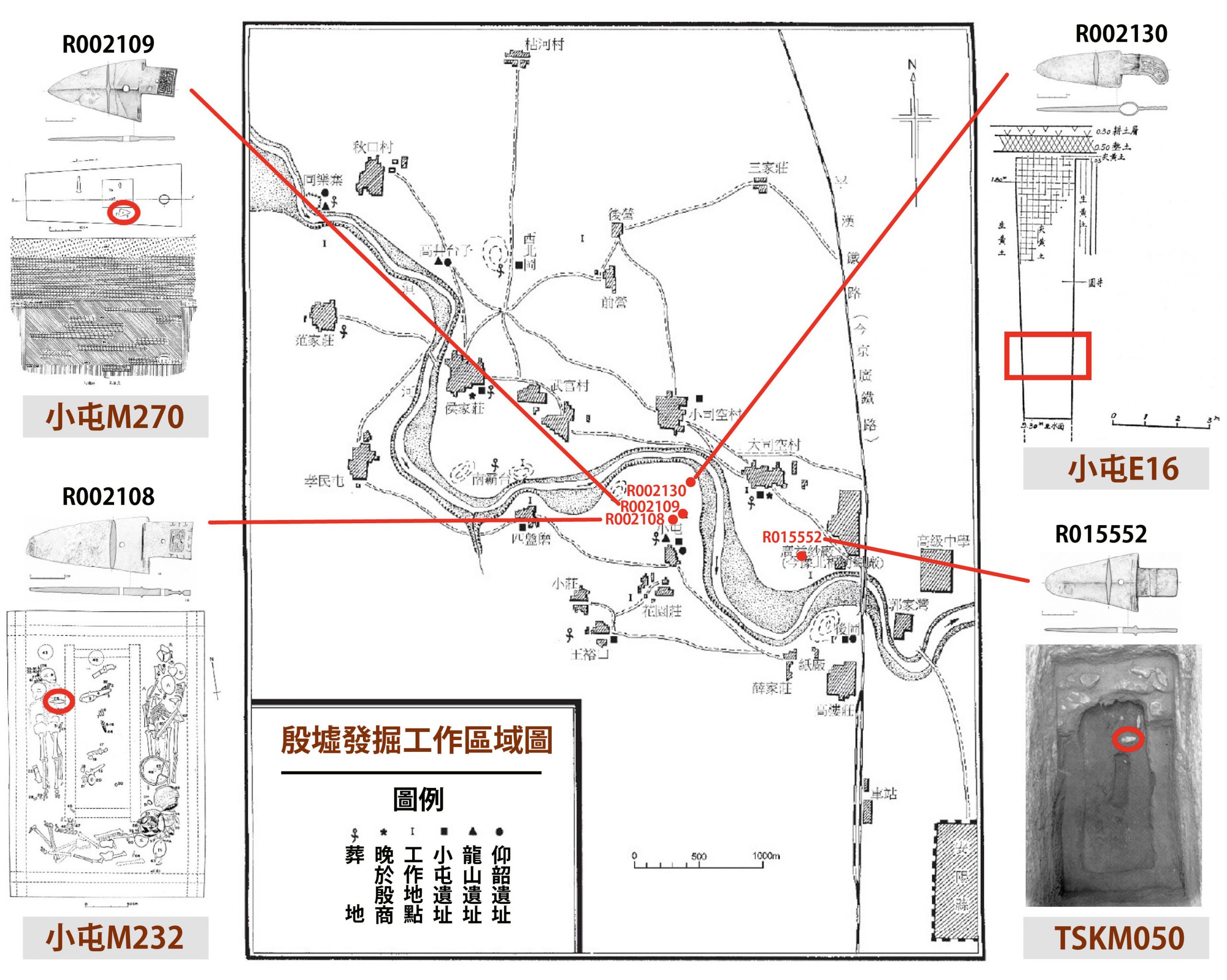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採訪撰文|黃楷元
- 責任編輯|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麻豆港的歷史
臺灣四面環海,整座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都與海洋息息相關,而港口正是海洋與陸地間的樞紐,許多故事都由此而起。臺南麻豆曾緊鄰倒風內海,擁有一座貿易興盛的內海河港「麻豆港」,也是西拉雅族最強部落「麻豆社」的居住地。四百年來滄海變桑田,當地的人文環境又發生哪些變化?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專訪院內臺灣史研究所林玉茹研究員,從港口走入臺灣史,揭開一段原住民與漢人勢力興衰交替的故事。

聽到「麻豆」這個地名,絕大多數的臺灣人腦中浮現的畫面應該是香甜多汁的文旦柚。有「柚鄉」美名的臺南麻豆,目前文旦栽種面積達到 800 公頃,說整個麻豆就是一座大果園也不為過。
不過麻豆蔚為文旦果園只是近三百年的事,在有人類活動的悠久歷史中,讓麻豆躍上世界舞台的其實是其「港口」角色。
奇怪!麻豆明明距離海邊有 30 公里遠,怎麼會有港口?這就不能不佩服造物者的力量,真能讓滄海變桑田。
走訪位在麻豆東北角的「水堀頭」遺址,可以看到一座三合土(由糖水、糯米汁、牡蠣殼灰加沙混合成的建材)遺構,這塊約 10 公尺長、看起來像是坡道的結構,究竟是水利設施、墓道還是碼頭,曾經是學界爭論許久的公案。
直到 2002 年,一次歷史學和考古學的共同研究,終於正式解開謎團。現任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林玉茹研究員,與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劉益昌教授合作,經過層層抽絲剝繭,終於證實三合土是碼頭遺構,水堀頭就是曾經的「麻豆港」。

「距今 4,000 至 3,500 年前,海水曾內侵到麻豆、佳里、善化一帶,在清代,這裡被稱為『倒風內海』,船隻可以通行、貿易。」林玉茹表示,「臺灣西部海岸是離水海岸地形,容易形成海埔新生地。清康熙中葉後,漢人進駐臺南地區,又積極把潟湖圍墾成魚塭或鹽田,是倒風內海逐漸陸化的主因之一。」
林玉茹是研究清代臺灣史、海洋史的專家,麻豆這個地方的「前世今生」引起她的高度興趣。除了自然地貌的海陸更迭外,更讓她一頭栽入研究的,其實是這裡的人文變遷。
在經濟上,港口是帶動城市發展的火車頭;在文化上,港口則是一扇看見外面的窗。
港口所在地因為與外界連結,成為本地和外來文化的交匯點,更是理解多元文化互動變遷的重要依據。而麻豆的水堀頭遺址雖然現在已位居內陸,卻保有臺灣碩果僅存的清代內海河港遺構,讓麻豆港與其周遭歷史得以重見天日。
林玉茹的研究剖析了麻豆港自 17 世紀荷蘭時期到 19 世紀清治時期的歷史(1624-1895 年),揭開一段原住民與漢人勢力興衰交替的故事。
守護部落文化的殖民者
最先居住在麻豆這塊土地的「麻豆社」,是西拉雅族四大社之一,也是臺灣西南平原最強大的部落。推測早從 14 世紀起,麻豆社人便開始與漢人進行零星貿易,以鹿皮、鹿肉、魚及藤等物產與漢人交易布、鹽、瓷器、銅簪、瑪瑙等奢侈品。但到了 17 世紀,西方強權開始把手伸向亞太地區,也改變了麻豆社的命運。
荷蘭人為了與葡萄牙、西班牙競爭海上霸權,1624 年在大員(今臺南安平一帶)建立了政權,同時作為國際貿易的據點。麻豆港位於大員北邊的倒風內海內,是麻豆社的對外出入口,因港口條件佳、又佔據重要航道,面對侵門踏戶的荷蘭人,很難不起衝突。
1635 年起,麻豆社在內的西拉雅族四大社逐一被荷蘭人征服,麻豆港也被納入大員的貿易體系,從事與大員、打狗、堯港等地的區間貿易。

林玉茹從文獻中觀察到,荷蘭人雖然為了擴大殖民利益,積極招攬漢人來臺開墾,但土地所有權仍然歸原住民所有。1644 年後,更在秩序及貿易利益最大化的考量下,選擇以「隔離政策」來治理這塊區域,一方面減少爭端、一方面也讓交易及稅賦更加透明。漢人除了做生意之外,勢力無法直接伸入麻豆社領域。
接續荷蘭人治理南臺灣的鄭氏政權,也在這個基調下維持「荷規鄭隨」,例如鄭成功的軍屯政策主要開墾無主地,遇到明確歸屬原住民的土地則避開。林玉茹認為,「雖然荷蘭和鄭氏的統治讓麻豆社失去部分主導權,但他們的管理卻也相當程度地保護了部落的土地與文化,不被漢人勢力快速入侵。」
這段期間,在麻豆港居主導地位的仍然是麻豆社人,不過在貿易和互動中,漢人仍然對原住民帶來了影響,例如引進甘蔗、藍靛等新經濟作物。
麻豆社原住民的兩難——要漢化,還是要遷徙?
然而,到了清康熙 23 年(1684 年),原住民與漢人隔離的景況隨著鄭氏政權一起告終。清朝把臺灣納入版圖後,對於漢人的開墾採取相對放任的態度,漢人移民開始大舉登臺,海上貿易也更加興盛。
漢人不只可以用租佃的方式耕作原住民的土地,更開始透過買賣取得土地所有權。林玉茹爬梳清代留下來的「地契」,觀察到漢人逐漸蠶食原住民勢力範圍的跡證。到了清乾隆、嘉慶年間,漢人土地鄰接原住民田園的情況已相當普遍,甚至出現原住民反過來向漢人購買土地的逆向操作。
在國家政策和漢人勢力的進逼下,原本壯盛的麻豆社,面臨兩種命運:漢化或遷徙。
林玉茹進一步指出麻豆社式微的原因,起因於麻豆社從清康熙中葉以來,先後被徵召參與平亂戰役,或是被課徵勞役、番餉,勢力明顯衰微,此消彼長之下,漢人逐漸取得麻豆這塊地區的主導權。
清乾隆中葉(約 1755 年後),漢人的街庄「麻豆保」以麻豆街為中心成立,稱得上是兩方勢力交替的重要指標事件。現存的三合土遺構可能就是在此時期由漢人所興建。麻豆港在此時仍然繁榮,只是主角換成了漢人,值得注意的是,當中包括「隱身為漢人」的原住民,許多改姓氏為「陳」,也接受漢人的宗教信仰。
從麻豆文衡殿(武廟)保存的紀念碑文可知,原住民改信奉漢人的關聖帝君,更參與捐款修廟事宜。特別的是,漢人如使用原住民土地,需繳香油錢給文衡殿,曾有漢人因侵占原住民土地又不繳錢而鬧出糾紛,在官府的仲裁調停下,最終在文衡殿立下「貼納武廟香燈漢番和睦示告碑」以示和解。
這種族群勢力的消長變遷,是林玉茹從文獻多方考察、彙整大量線索建構出的軌跡。除了從地契看出土地所有權轉移的歷程外,地圖的標註也是證據之一。
清乾隆末期,「麻豆社」已從臺灣輿圖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漢人建立的「麻豆保二十庄」。其他像是地方志中,對於生活型態、商業活動、公共事務等的描述,也都可以看到蛛絲馬跡。

成為全臺少見的「街村與農村」合成聚落
時間來到 19 世紀,「滄海變桑田」的結局終於登場。水文環境的自然變化,加上居民的屯墾,麻豆地區的港道日益淤塞,至清道光末年,文獻上已無麻豆港的紀錄。
但麻豆市街卻沒有因為港口的消失而沒落,由於地處樞紐、物產豐饒,仍是非常繁榮的交易集散地。一些麻豆地方仕紳靠著「蔗糖」生意,躍升富豪階級。
林玉茹發現,從文獻對於市街的描述看來,這時的麻豆已成為漢人地盤。例如清代文人丁紹儀在《東瀛識略》中這麼描述眼中的麻豆:
均雜處民間,存番無幾;往昔番廬胥成村市,舊社無從跡矣。
儘管原住民的身影已從麻豆的畫面中淡出,但他們留下的生活印記,仍然決定著這座城鎮的風景。
過去麻豆社的聚落是以「檳榔宅」為主體的農村格局,擅長園藝的麻豆社人,會在屋舍四周種植檳榔樹或文旦、龍眼等果樹,形成單一住宅面積廣大、卻又宅宅相連的結構,是兼具「集居」與「散居」特色的超大規模農業聚落。

後來漢人在開發過程中,順應原本的檳榔宅聚落格局,又在商業活動的發展下,另外形成了漢人風格的市街。兩者疊加之後,麻豆就形成了全臺少有、別具特色的「街村與農村合成聚落」。
這樣的城鎮風貌可以說是原住民與漢人勢力興衰、相互涵化的最佳例證。
說出臺灣的故事,是林玉茹的終身志業!

雖然林玉茹是海洋史學家,但她自揭,海洋並不存在她的兒時記憶中。林玉茹在臺南歸仁長大,從小沒看過海,直到去臺東讀師專後,才有機會近距離接觸大海。
海對我而言,是神秘的!港口可以通往哪裡?彼岸有什麼在等著我?這種充滿冒險的氣味,令人非常著迷!
林玉茹自幼課業成績優良,因家境因素考量,最後選擇就讀師專。到臺東讀書後,彷彿掙脫了一身束縛,終於不再被升學壓力綑綁,而是出於對知識的熱愛而學習。
「那時候想繼續唸書,但因為一邊在國小教書,必須選擇夜間部。在師大沒有夜間部的情況下,我只能選擇臺大。在臺大歷史系讀了兩年後,我做了一個當時看起來很不自量力的決定──挑戰研究所!」
林玉茹笑說,感謝師長和同儕的鼓勵,讓她有勇氣成為第一個「越級打怪」考上臺大歷史研究所的夜間部學生。這位熱愛知識的國小老師,就從臺大歷史所開啟了學術研究之路。
1990 年,臺灣本土化運動方興未艾,攻讀碩士第一年的林玉茹就決定選擇臺灣史作為研究志業。「所謂的終生志業是,你即使到老了、到要走入棺材的時候,都還對那個工作有興趣。學術研究對我來講就有這樣的意義,它沒有退休的一天。」
身為臺灣史研究者,林玉茹認為說出屬於這塊土地的「故事」至關重要。學術殿堂縱然迷人,但歷史作為這塊島嶼的血脈,還是必須轉化為大眾可以理解並共感的知識。
「我是臺南人,麻豆也算半個故鄉。四百年來,這塊土地上的人群怎麼在大海的懷抱中,彼此競逐、興衰更迭,與世界連結,透過我的研究能說出這些故事,讓人們的存在更加有血有肉、鮮明真實,就是作為學者最大的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