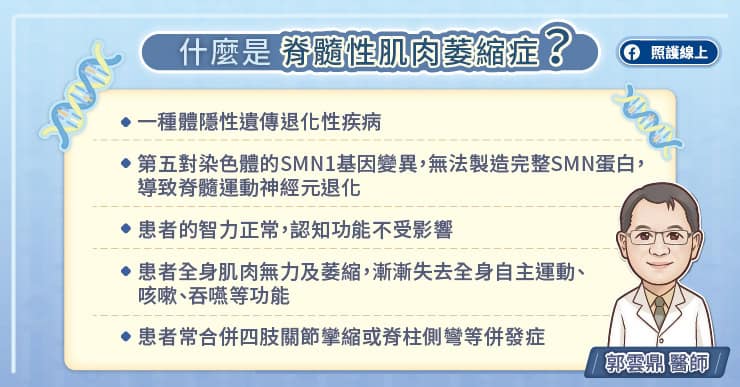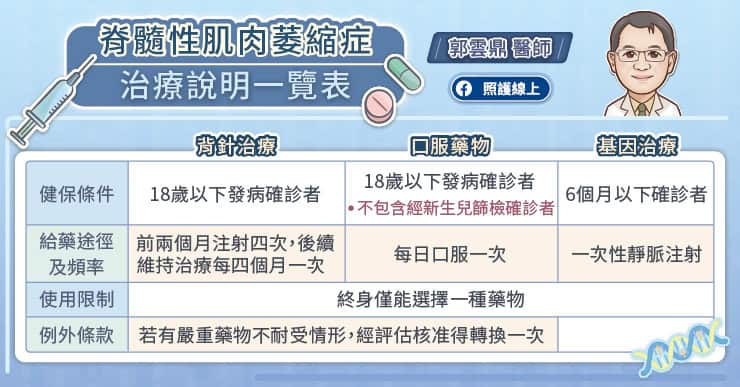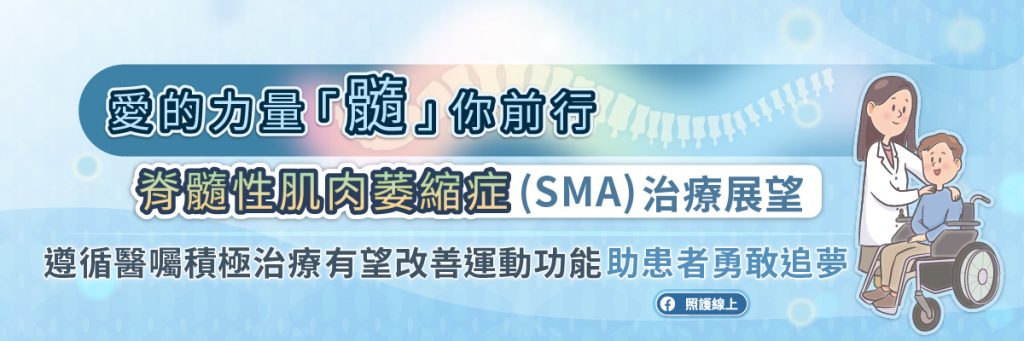臺灣的成癮治療仍在陣痛期
每座藥癮冰山下的議題盤根錯結,沒有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解方。研究成癮醫學的國家衛生研究院神經及精神醫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王聲昌就認為,各國用藥文化、歷史不同,很難把國外做法原封不動移植臺灣。要探究的,是怎麼在臺灣自己的脈絡下檢視成癮問題。
臺灣在一九九八年修正公布《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其實已符合國際將吸毒者由罪犯轉為病犯的趨勢。現在施用一、二級毒品被查獲,會送到勒戒所觀察勒戒,若評估有繼續施用的傾向,則送戒治;戒治後三年內再犯,下一步才可能通向監獄。二○○八年建立的「緩護療」,則是本於「病犯」觀點所出現的政策,在監禁隔絕前,有一道醫療的緩衝機會。
自一九九八年修法以來,王聲昌認為國內對藥癮者的處遇投入依舊不足。他表示,長期以來,成癮者的醫療處遇偏向症狀治療,比如急性戒斷期出現躁動,就求診請醫師開藥鎮靜,這是頭痛醫頭,不是戒癮。臺灣的成癮治療,仍在典範轉移階段。

接受我們採訪的醫師與檢察官也提到,成癮治療沒有健保補助,難以挹注醫院收入,導致治療品質參差不齊,對病人也沒吸引力。臺灣的門診一診看四、五十人是常態,成癮者很難在短時間內獲得幫助。
而且成癮醫學不像電腦斷層,一掃就知道問題在哪裡,病人會談、做量表時難免避重就輕。「每個人來都發誓要戒,評估工具受限下,很難衡量問題有多嚴重,」王聲昌分析,「過去的藥癮者是法律上的犯人,查到毒品就關起來,很少醫療專業者主動去監所(協助藥癮者),無論醫療知識或經驗累積都不足。所以臺灣的醫療在世界排名前段,成癮醫學卻落後。」
更難撼動的是觀念,社會普遍對藥癮者抱持負面印象,讓有心求助的人因擔憂外界眼光而退縮。衛福部心理健康司專門委員洪嘉璣,主要負責的業務是成癮處遇,她這樣比喻:「藥癮比隱疾還隱疾,病人自己不講,家屬也不敢求助。」

成癮是段病程,治療需要一組配方,每種配方在不同階段帶來不同效果。這些配方分散在各部會與醫療院所,大家的目標都是降低藥癮危害,立場卻常背道而馳。洪嘉璣舉例,「例如警察看到這個人怎麼又吸毒,要抓起來;我們看到的是他從每天打六針,到現在二週用一次,已經有進步。」跨部會的合作,總得花很多時間溝通。
走得磕絆,但在典範轉移的陣痛期總是如此。王聲昌認為,與其把焦點放在成癮是否復發,不如將重點放在服務提供上,研究提供什麼樣的處遇,才能給戒癮者最大幫助。「會遇到的狀況是,很多事情能在既有框架中運作得很好,大家就會質疑為什麼要為了一小撮成癮者改變現狀?」
要有改變,就要有突破框架的嘗試,二○一八年底上路的美沙冬跨院區給藥就是一個例子。
回歸正常生活有可能嗎?
國衛院二○一七年先找二十五間有意願的醫院試辦,訂定適用申請跨區給藥的個案條件、評估機制,並設置協作中心,由專人總機負責媒合轉介個案。過程中狀況難免,總機作為緩衝角色,除了能即時偵錯,讓問題得到回饋,也能累積醫院間的信任,而非增加衝突。一年後累積足夠的基礎與經驗,才讓總機退場,讓院方用電腦系統作業。截至二○二二年十二月,已有二十個縣市、六十四間醫院加入跨區給藥。
接受美沙冬治療的海洛因成癮者,一天不喝美沙冬就可能出現戒斷症狀,但在過去得每天到固定醫療院所報到領藥,造成生活與工作不便、無法出遠門,也影響接受治療意願。

規劃推動此計畫的王聲昌說,跨區給藥概念簡單、實務困難,轉出醫院希望給患者方便,轉入方怕患者有問題,兩邊沒交集。當然一紙行政命令就能立刻上路,但第一線的信任問題沒解決,刁難與挫折恐怕落到個案身上。
儘管如此,從第一線服務端考慮需求的方式,已經逆轉行政體系的思維。而原本須每天到固定醫療院所、在醫護人員監督下喝美沙冬的個案,現在能出遠門工作、探親、旅遊,更接近一般人的正常生活。
「用美沙冬的人很小眾,但就是要從這微不足道的事情開始,慢慢帶動改變。」王聲昌嚴肅的語氣,到這裡終於開朗起來。
司法、醫療與社會能做的,是幫藥癮者清出路徑、磨銳武器,伴著他們上戰場。唐心北認為,成癮是一種腦部的疾病,也是一種關係的疾病,每個生命都不同,沒有一組能套用在特定成癮樣態上的公式。

治療過程,得瞭解每位成癮者用藥的經驗、背景、生活樣態,協助患者消除弱點、強化優勢;不只醫療與司法,還需連結校園、心諮輔導、勞動就業等多元處遇。
每次緩護療的初診,唐心北會問患者同一個問題:你為什麼想戒?他認為這是整個成癮治療的核心,「患者得認真思考他到這裡的原因,不能只說是檢察官要他來。(戒癮)這件事,要從外在壓力轉換為內在的意念。」
畢竟,這是一場和自己的戰爭。
WTV01045-島國毒癮紀事-立體書封-1.jpg)
——本文摘自《島國毒癮紀事:那些在製販、司法、醫療、社區裡的用藥悲劇與重生》,2023 年 5 月,春山出版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