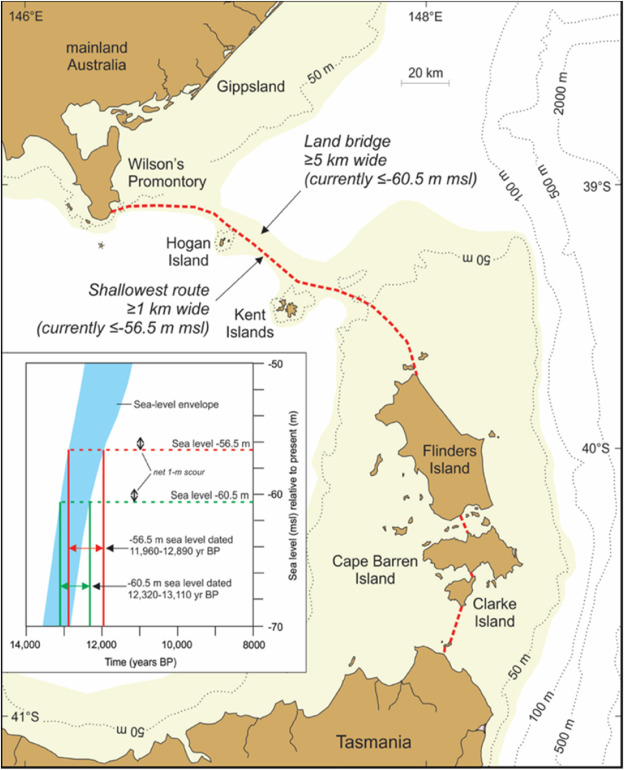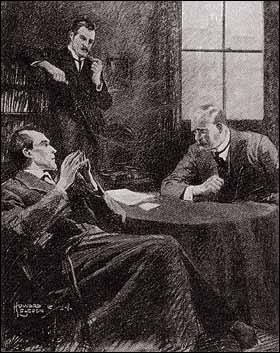預測失準的狂牛症,下次要怪罪給誰?
BSE(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牛海綿狀腦病),是所謂的狂牛症。一九八六年首度確認有牛隻感染,兩年後英國政府委託牛津大學動物學家沙斯伍德(Richard Southwood)擔任調查委員會的委員長。但即使用上了當年最先進的知識,調查委員會也幾乎無法斷言狂牛病的任何事情。

即便如此,英國政府還是委託沙斯伍德進行決策(包括保護畜牧業)判斷。沙斯伍德在一九八九年完成的報告書裡預測,會感染狂牛病的牛隻最多就是兩萬頭,而且應該不會傳染給人類。這個說法成了後來的政策依據,英國政府也立刻公布了安全宣言。
但是預測失準了。感染的牛隻持續增加,在最高峰的一九九二年,光一年就有三萬七千頭。此外,在一九九六年,因吃了受感染牛隻而罹患變異型庫賈氏症(Creutzfeldt-Jakob Disease, CJD,人類的 BSE)的人,共有十例。英國政府因此被迫撤回安全宣言。
對科學家說「全交給你了」會讓科學家深感為難,而全權委託給科學家的我們也會很苦惱。這就是家長制的危險。平時全都丟給科學家,出事了就說他們是御用學者,逼他們道歉。我們打算重複這種模式到什麼時候?
遇到超科學問題怎麼辦?公民應該親身參與?
該怎麼解決超科學的問題呢?
溫伯格認為,要區分專家的任務和公民的任務。
專家應該要研究超科學的問題,能否在可能的範圍內當成科學的問題來解決。至於無法解決的部分,就應該明確指出哪些是科技可以弄清楚的,而哪些是科技無能為力的。專家的任務就到此為止。如果還有無法解決的問題,就應該由利害關係人和公民來共同參與,透過公共討論來解決。後半部分強調了公民應該負擔的任務。
我來說說自己的觀點。對於前半部分專家的任務,我有些質疑。我並不贊同「應該要研究超科學的問題,能否在可能的範圍內當成科學的問題來解決」。但我同意後半部分。它的意思是說,公民必須參與和科技有關的社會決策。

發生超科學的問題時,我們要從和科學家不同的角度,提出恰當的問題,尋求可以接受的說明。然後根據這些說明,在理解後考慮自己應該怎麼做,而社會又應該做什麼樣的選擇。這些必須由公民親身來實踐。
實踐「公民控制科學」,人人都該培養科學素養
科學哲學家小林傳司用「公民控制科技」(civilian contro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來說明公民的任務。近代發明的各種解決問題的手段裡,科學是最有力量的其中一種。軍隊則是另外一種。軍隊若脫離公民的控制就會失控,那非常危險。我們因此創造了一種制度,用非軍人來控制軍人。這就是公民控制。

科學和軍隊一樣強而有力,失控的話也很危險,因此,我們也必須用公民社會來控制科學。那要由誰來控制呢?終究還是要由公民來控制。公民必須具備足以實踐公民控制科學的科學素養。
我認為,這就是全體公民都要培養科學素養的理由。或許有人聽到「公民控制科學」會覺得有點討厭,好像科學家要聽公民的命令行事。最近還有另一種說法叫「科技治理」(governa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但因為我想明確指出是誰在治理,故而採用公民控制這種說法。
此外,我們一直用「公民」這個概念來與科學家作對比。可能有人會問:「到底誰才算公民呢?」現在,姑且讓我們把公民想成「與科學有關係的一般人」就行了。
科學素養就是學會大量科學知識嗎?
那麼科學素養的內容是什麼呢?一般公民不是科學家,不需要具備運用科學來解決問題的素養。公民的任務並非和科學家有一樣的想法,而且公民所擁有的科學知識量也不會超過科學家。這些都不是科學素養的本質。
公民必須具備的知識,是關於「科學怎麼向前邁進」、「科學怎麼被納入政策」、「當社會處在什麼情況下,科學會出狀況」這些問題的知識。就像核能發電的例子:在什麼樣的社會狀況下、當產業部門之間的關係是如何時,它會變成像偽科學那樣的危險技術?這些針對科學的知識,就是公民科學素養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們一直忽略這些問題。典型的例子是美國自一九八五年開始實施的理工科教育改革計畫,稱為「給所有美國人的科學」(Science for All Americans)。這個計畫為了提高國民的科學素養,列出所有美國公民都應該具備的基本科學素養。
為了列出清單,各個領域的分科會議都列舉出公民應該知道的最基本的科學知識。結果,不管是哪個領域,都挑選了大量的內容。如果把各個領域最基本的科學知識集合起來,那根本就沒有人可以完全通曉這些知識!計畫因而失敗。

在二戰之後,美國嘗試了包括「給所有美國人的科學」的各種教育計畫,但美國公民的「科學素養」並沒有因此提高。這讓我們瞭解,用知識的量來衡量公民必須具備的科學素養,是徒勞無功的。而且,某個時刻的「必備知識」,十年之後便舊了。技術的發展,原本就會讓一般人完全不瞭解內部構造的黑盒子越來越多。
曾經擔任美國全國科學教師協會(National Science Teachers Association)會長,也是核子物理學家的夏摩斯(Morris Shamos)因為對此有痛切的體悟,才會在一九九五年出版《科學素養的神話》(The Myth of Scientific Literacy),把提升國民科學素養的計畫說成是畫餅充飢。
夏摩斯認為,應該讓兩成的國民習得所謂的「科學素養」,而剩下八成的國民則學習「科學意識」(scientific awareness)。
科學素養的真意:「針對科學」的知識
科學史學家杉山滋郎曾介紹過夏摩斯的觀點(杉山滋郎,〈科學教育——什麼才是真正的問題?〉〔科学教育——ほんとうは何が問題か〕,金森修、中島秀人(編著),《科學論的目前狀況》〔科学論の現在〕,勁草書房,第四章)。如同杉山滋郎指出的,夏摩斯所說的科學意識(對於科學的關心和認識的程度),內容其實有點模糊。但我認為,夏摩斯談論的意識裡有很大一部分,和參與公民控制科學所需要的能力是相同的。
也就是說,公民科學素養的真正意義,並不是關於科學發現的知識。真正重要的,應該是「針對科學的知識」,比方說瞭解科學與技術這個行當的特性、能適當地評價和批評科學家的活動,以及能檢驗專家的可信度等。

簡單地說,對於公民而言,能適切地批評社會中科學和技術的現況,是很重要的。舉例來說,要有能力參與檢視科學相關事業的預算編列是否浮濫、建立發展科學的適當制度、恰當地進行公共評論,這些才是公民科學素養的內容。
本文摘自《「科學的思考」九堂課》,游擊文化, 2017 年 10 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