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Kum Long Yin
即使不同意,仍要捍衛發言的權利?
試想像以下情況:在一個不成熟民主的社會中,人民在選舉當中選出一些反對民主制度的人作當權者。他們支持極權主義,無視少數族群的訴求,甚至對反對他們的人發表族群仇恨言論 (hate speech)。這個時候我們該怎麼辦?要管制這些仇恨言論,還是容許?
其實這個問題並不容易回答。若果我們要管制或禁止這些仇恨言論的話,會不會違反民主社會的言論自由原則呢?相反,我們不禁止這些支持極權主義的言論,不懲罰攻擊少數族群的言行,這些思想可能會蔓延,有可能摧毀多元民主制度的基礎,最後真的變成了極權政府,一發不可收拾。

民主社會中,寬容的確是基礎。此話何解呢?民主社會其一重要功能,在於能維持多元開放社會,讓擁有各種不同思想背景,屬於不同族群的人能夠生活其中。在這種社會中,理性思辨與公眾討論,讓想法不同的人相互交流,最後「真理愈辯愈明」,不合理的政論便可被排除在外。所有人都有權利參政,亦有義務作公共討論。但是,這種社會不能只有一兩種人,我們卻要對不同的意見寬容,民主社會才能運作;同樣地,民主社會的正常運作,也能反過來保障社會的多元發展,不能以一把聲音蓋過所有人,要防止「一言堂」出現。
但是,這種社會的運作建基於理性及寬容。若果在多元寬容的社會當中,出現了不寬容的人,我們還應否對不寬容的人寬容呢?把不寬容的人排除在寬容社會之外,繼而成為自己也成為不寬容之人?還是,不理會民主社會自我推翻的風險把他們納入其中?顯然兩種態度都有原則上的問題。
民主過了頭?德國威瑪共和時期瓦解
以上的難題, Karl Popper 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曾經提及:
較少人知道的,是寬容的悖論:無限制的寬容最終會導致寬容消失。若果我們把無限制的寬容應用在對待不寬容之人,或者我們對不寬容之人的打擊不作準備,這樣的寬容最終會被破壞。我並不是說,我們經常要管制不寬容的思想,只要我們有理性的公共論點來反抗他們的話,管制這些言論都是不智的。但我們應該有權宣稱,有必要的時,我們可以用武力管制這些思想及言論。很多時候,這些極端思想未必有理論討論的層次,他們可能禁止追隨者聆聽理性的論點,以這些欺騙的手法,教導追隨者以槍或拳頭回應討論。所以我們有權宣稱:以寬容之名,我們有權力不去容忍不寬容之人。1
他的回答可能會令上世紀經歷過納粹統治的人比較安心,至少這種說法堵塞了諸如法西斯主義重燃的風險。其實,兩次大戰其間的歐洲便正經歷着這種個難題。當時德國的威瑪共和時期,的確是歷史上具完備民主制度的政體,可是經濟大蕭條,戰敗賠款、戰爭罪責及民族屈辱等等讓不少的民眾漸漸支持納粹黨,當時德國社會民主素養薄弱,對衝鋒隊及國會縱火案等事件不聞不問,亦縱容了納粹黨的坐大。這便是對不寬容的寬容,漸漸令寬容消亡的其中一個例子。
管理「極端想法」?土耳其政變頻出
而 John Rawls 曾經在《正義論》中討論過寬容的問題,他認為只有在我們要為了自我存續或者自保的情況下,才可以主動干涉這些不寬容者的思想、行為或言論,否則自已亦會變成不寬容者。因為,根據正義原則,人毋須呆等着別人消滅自己,卻有權自我保護 (self-preserve)。
然而,唯一的難題在於,如果那些不寬容的思想、行為或言論沒有直接威脅,我們該怎麼處理?2
要回應此問題,我們需要先評估具體情況,John Rawls 認為哲學並不足以解決這方面的困難。並且,他認為政治哲學僅適用於處理憲法及政治行動是否正義等原則問題。
再舉個例子,近代的土耳其便經常觸及以上的問題,而軍事政變頻生。一戰之後,鄂圖曼帝國土耳其帝國瓦解,當時的戰勝國把土耳其帝國的大部分土地都劃為英法的勢力範圍及殖民地,情況有如清朝晚年。土耳其國父凱末爾 (Mustafa Kemal Atatürk) 將軍是土耳其少數能打勝杖的將軍,他認為土耳其的落後在於不夠西化。故此,他把土耳其建立為一個政教分離的共和國,並宣布一連串西化政策,例如:解放婦女,拉丁化土耳其字母,而更重要的是使憲法給予軍隊保護世俗化政權的權力,所以土耳其軍隊的精英亦以共和國保護者自居。

每當軍隊認為國家走回頭路之際,有重返回教政教合一的傾向,軍隊便會發動政變,以圖保護世俗化政教分離的民主政權。的確,歷史上土耳其軍隊多次政變後,亦還政於民,不久又重新大選。2016 年的政變,就是土耳其軍隊認為艾爾多安破壞已有的民主與世俗原則,開始管制言論,例如禁止使用 Twitter 等等,因而以對「不寬容者的管制」,希望回到國家的正軌。
軍隊每一次介入政治的時間,就是認為政府所行的道理對民主社會有直接的威脅的,類近 Rawls 所說的情況。翻查當時政變的新聞,軍隊的領袖的確說「土耳其的民主與世俗原則已被現在的政府所破壞」。但是,我們又如何說明這是一種破壞?到了什麼程度,才可判斷為不出手不可,必須干涉?
但上述的政變,不正是反抗者對不寬容者的不寬容,自身亦變成了不寬容者嗎?我們又該如何判斷這些不寬容者對國家的存續,有沒有直接威脅呢?這種難以定義的灰色地帶,會否在被極端組織濫用,並作為行動的藉口呢?
坦白說,我亦沒有想到一個清楚的答案,也許如 John Rawls 所言,哲學並不足以解決這類困難。
- 本文轉載自《好青年荼毒室》,原文標題為〈民主政體的內部困難:由寬容悖論說起〉。
備註
- [1]:Karl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Vol. 1, in note 4 to Chapter 7
- [2]: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Belknap Press, page. 192-1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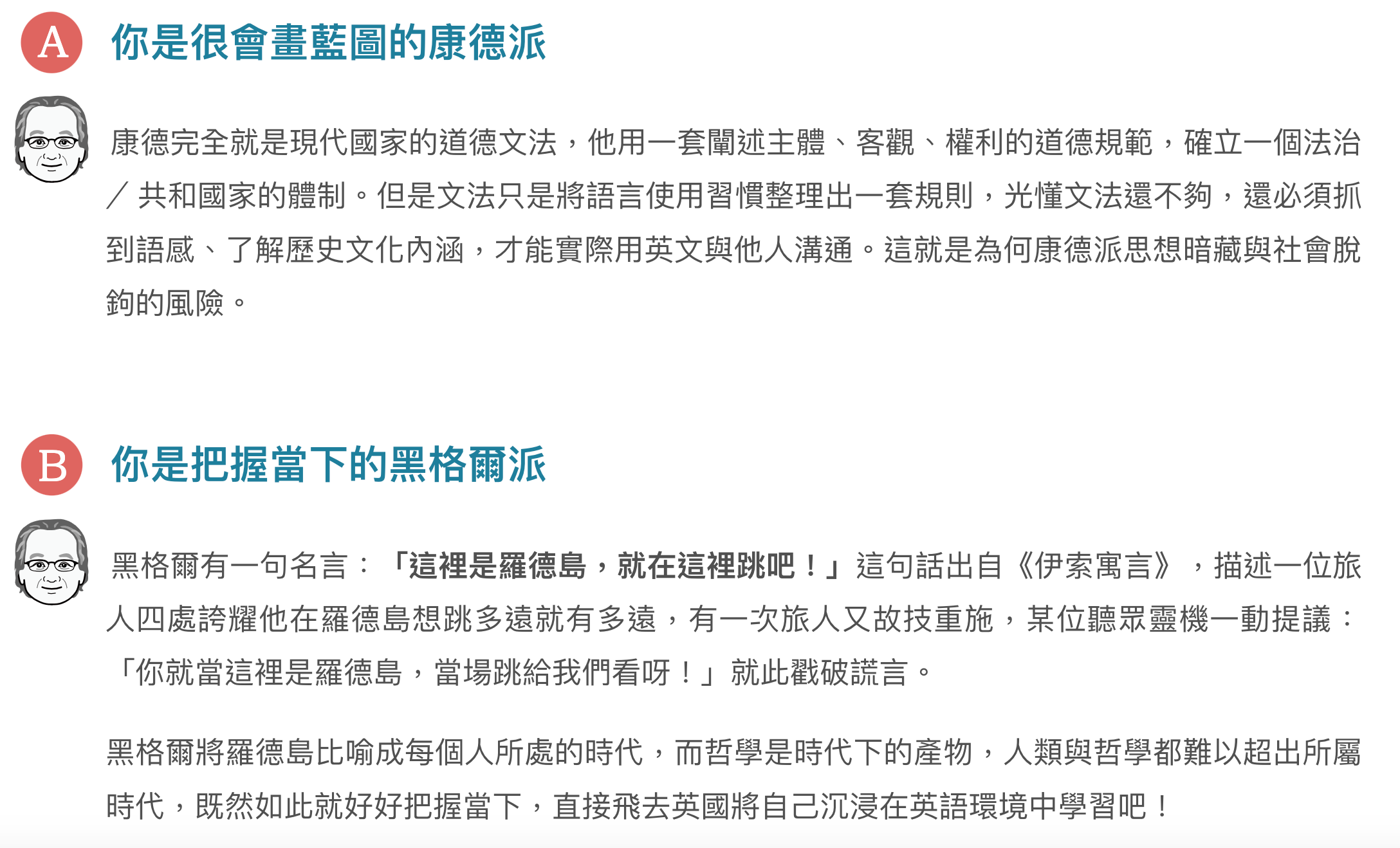
















2-85x85.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