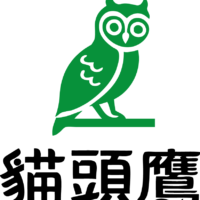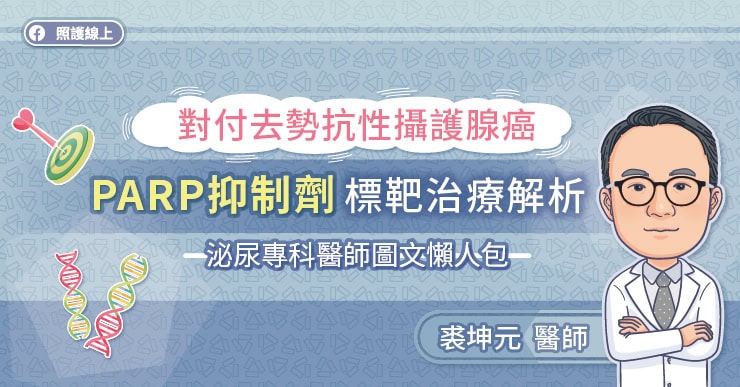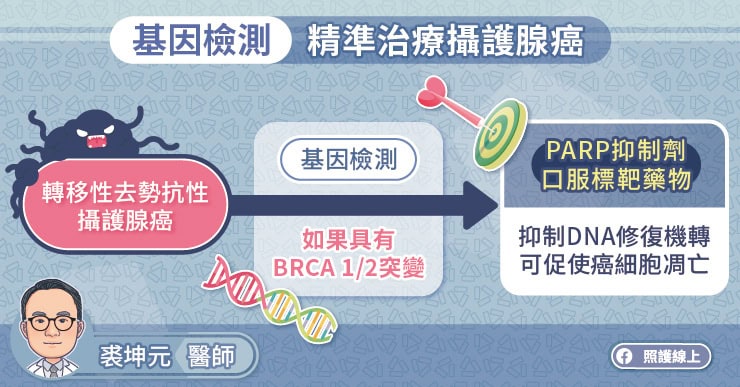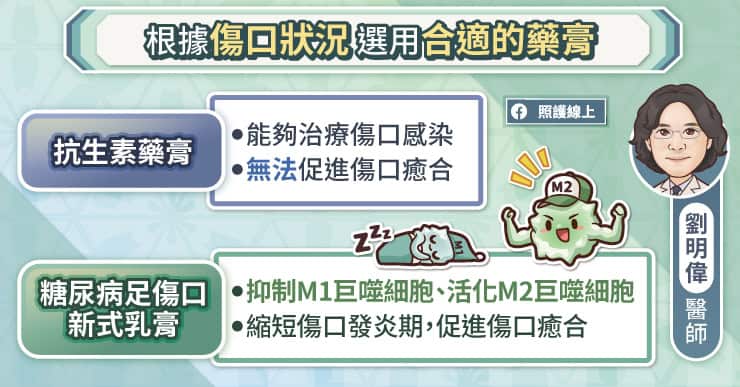民國一○○年四月,是我從外科總醫師轉任急診主治醫師的第一個月,那個早晨,如同過去在醫院值班的其餘五百多個日子一樣,我睡在醫院,鬧鐘設在六點二十分,當耳邊響起Linkin Park的嘶吼後,無論腦中有多麼混沌,我都會直起身甩甩頭,走向值班室的洗手間。
是的,值班時候絕不敢賴床,能睡到被鬧鐘叫醒,而不是在凌晨接到任何急救或照會的電話聲,早已是萬幸。於是,我總把這個能按部就班刷牙洗臉上廁所的機器人行程,當成是重要的儀式,好像走錯任何一步,都會遭天譴似的。
梳洗完畢進到急診診間,看見學弟的手正放在電話上,急迫地看著我說:「學姊,我們剛好要呼叫你。」
「怎麼了?」我順手移動滑鼠,瀏覽著電腦上的病人名單。
「不是!」另一個學弟接著說:「醫護大樓那邊有緊急狀況,急救小組已經趕過去了,等一下應該就會送過來,小凱醫師先跑過去幫忙了。」
「知道是誰嗎?」無論是誰,只要住在醫護大樓,就可能是任何一位我們所親近、熟識的人。儘管外科醫師的訓練生涯裡見過太多大風大浪,但接獲這次通報時,只感覺血液裡大量的腎上腺素湧出,腦子瞬間清醒。
「目前還不知道……」學弟們的臉上也都掛著些許緊張與憂慮。我點點頭,告訴自己定下心神,跟學弟們說:「走,我們都過去內科幫忙。」
我們三人一起跑到內科急救區,氣氛凝重,沒有人說話。急救車上早已準備齊全,急救推床也已備妥,我們三人就在這個狹小的空間裡踱步著。
「病人到!」檢傷護理師的女高音吼叫著,小凱醫師隨著擔架快跑進入急救區,「是學弟!實習醫師!」
「來,挪床,一、二、三!」
「心電圖!氧氣!打靜脈導管!」
「心臟按摩!」
「打強心劑!靜脈輸液!」
「第一劑保斯民打了!」
「繼續心臟按摩!」
在震驚中,沒有人停下腳步,反而都像脫韁野馬般衝了出去,急著能多幫上一點,能多作些什麼。
急救繼續進行著,而學弟的身體卻毫無反應。心電圖一直沒有起色,但沒有人願意承認,願意放手。大家都繼續作著任何能作的事情,不願意結束。
我們一邊施行心肺復甦術,一邊把學弟移到加護病房,心臟外科及心臟內科的大批人馬已經等在那裡,準備放置葉克膜。見到熟悉的學弟沒有一絲氣息,總醫師大吼著:「快!這個學弟很認真,大家一定要救他!」緊挨著牆壁,讓器械推進房間的我,頓時眼眶蓄滿了淚水。
我看了一眼正在鋪單消毒的心臟外科同事,心裡默默想著,有這群人真好,永遠都願意挺身當閻王的絆腳石。心臟外科的學妹抬起頭,給了我意味深長的一瞥,她的眼裡正訴說著驚訝、難過、害怕、心涼。我懂,我都懂,但是我低下頭,寧願看著器械也不敢再看她的眼神。
心臟外科的主治醫師找到血管後插進導管,發出一句振奮人心的話:「血是紅的,還有機會!」沒有人答腔,但每個專業人員都用盡全力搶救學弟。一回頭,加護病房外已經擠得水洩不通,聞風而至的醫師、主管、同學、同事,大家都想來看看有沒有能幫忙的地方。這時我瞥見學弟的室友小文縮在角落,在呼吸器聲響此起彼落又人聲鼎沸的加護病房裡,顯得無聲無息,但他臉上的眼淚正瘋狂地滑落。
唉,早上是小文發現學弟在廁所失去意識的吧,一定是嚇壞了。我頓了一下,想要走過去拍他的肩膀,可是,我停住了;我怕,我走過去,也會蹲下來和他一塊痛哭,畢竟,我也嚇壞了。
走出加護病房,我打了通電話給同為外科醫師的先生,就劈頭講了這段經過,最末,我加了句:「老公,我愛你,你一定要好好的。」
「你也要好好的,去休息一下。」然後我們靜默了一陣才掛斷電話。
早上八點多,我的腦海還在不斷重複播放每個急救的細節,偶然插播著過去和學弟對話的點滴與畫面,想著曾教他如何判讀電腦斷層,而他認真地聆聽;想著想著好多事情。這時候的情緒,已經分不清楚是在高點還是在低點,我只覺得沒辦法休息,但需要同伴,於是我走進最熟識的開刀房。也因此聽說了學弟被送到急診室前的那個片段:室友小文聽到學弟的鬧鐘響個不停,於是起床察看,這才發覺浴室的門反鎖著,呼叫卻沒有回應。小文馬上向管理室及隔壁的外科阿柏學長求援,撞開反鎖的門,看到學弟已然沒了氣息。阿柏立刻開始施行心肺復甦,壓胸、口對口人工呼吸,直到救護人員趕到。
我腦海的片段更多了,我佩服著阿柏的果斷,在沒有任何器械幫忙下,作到了最極致的救助;心疼著小文的慌亂,在半夢半醒間愕然發現室友沒了反應;開刀房裡的同伴,都講著那個浴室的門,大家想著,還有沒有多一點的可能,好像,只要那個門能早一點點開,我們就有多一點點的機會,只要多給我們一點點時間,我們可能可以……
早上十點多,雖然盡了一切的努力,學弟還是走了。
看到加護病房外排排站著許多同為實習醫師的學弟學妹,我鼻頭好酸,還是不知道要上前和他們說點什麼,他們也都各自一個個沉默著,流著淚。
後來的後來,事情的發展已經超乎我的想像。也許因為那天的我屬於深陷其中的人,反而不願意再去多看任何一點媒體的報導或評論的浪潮。直到有一天主任打電話給我,說:「你知道學弟在外科實習的時候,選你為「最佳住院醫師」喔!」
那一刻,曾經試圖壓抑的一切又湧上心頭,我完全講不出話來。
我只能默默的祝禱:「學弟,謝謝你。在我心中,你也一直是好棒、好優秀的實習醫師。」
再後來的後來的某天,心臟外科的主治醫師跑來告訴我:「我剛剛去寫了健保申覆。」
我盯著電腦螢幕,頭也不抬地答了一句:「我也常在寫啊,刪一堆,什麼都亂刪。」
「我今天寫的是學弟的申覆……」他說。
「幫學弟裝了葉克膜,結果被核刪了?」我問,雖然沒有太多的訝異。
「嗯。」他沒有憤恨,只淡淡地說:「想起來好悶啊……我們到底做了什麼?我們所有能做的都做了,但好像總還有許多人覺得我們做得不夠,而健保卻總是覺得我們做了太多。」因為一向如此,我們只能無奈地在這個體制所定下莫名的規則裡轉呀,繞呀。
當然,直到現在,我的心中還依舊在想著,是不是還能再多做點什麼?能再改變點什麼?
或許這難題的解答,該是要從制度面著手。
摘自《醫療崩壞!沒有醫生救命的時代》第一章〈台灣醫療崩壞正在進行中,而你該怎麼辦?〉。本書由貓頭鷹出版社出版,獲2012年10月PanSci選書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