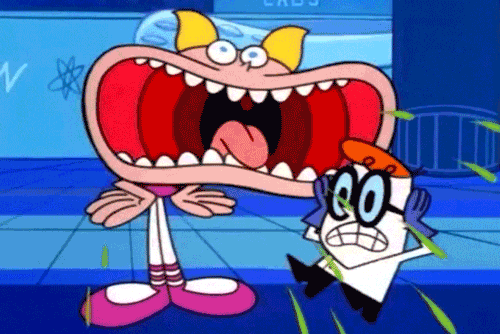本文由民視《科學再發現》贊助,泛科學獨立製作

前言:2014年3月24日凌晨時分,警察驅離於23日傍晚起進攻行政院與在行政院外靜坐之學生與民眾,驅離過程中引起極大的爭議,一部分的人認為警察執法過當、暴力對待民眾(以盾牌剁人、警棍用力打人),另一部分的人則認為警察作法並無不妥(學生不應該攻佔行政院)。本文將不評論對錯,希望以心理學之客觀角度分析警察攻擊行為背後原因。
首先,要問警察為什麼要打人?或說為什麼會打人? 如果我們從生理、情緒的觀點出發,推想由於部分警察是南部調往北部,一路舟車勞頓;又部分警察被迫結束休假,前來支援;再加上現場民眾與警方雙方互相挑釁的行為,使警察內心累積不少負面情緒,再碰上不肯配合驅離之群眾,在執行命令時遇上許多困難,挫折之際,於是將憤怒宣洩在對群眾的暴力行為之上。在心理學當中這被稱為「挫折侵略假說」(Frustration–Aggression Hypothesis):人若遭受挫折時,將會攻擊無辜的人,即俗話說的「遷怒」 [1] 。在這個抗爭場面,警察把內心的挫折與壓力遷怒在抗議的群眾之上,攻擊此時就是最好的宣洩方式。
另外,根據行為學派的觀點,攻擊行為和其他行為一樣,發生頻率與結果是獲得獎賞或懲罰有很大的關聯(效果率, Law of Effect) [2]。如果警察的攻擊行為沒有遭到懲罰阻止,且警察從這個行為當中獲得攻擊性欲求的滿足(即佛洛伊德所提到的「死的本能」 [3] ),警察的攻擊行為將自然大幅度的增加,這也滿足心理學中「工具制約」(Operant Conditioning)的原理 [4]。不只如此,僅僅只是看著其他警察展現出攻擊行為,自己也可能會因此展現更多暴力行為,這就是「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或「觀察學習」:僅僅是觀察就會學習,某種程度上來看其他個體是可以感同執行動作者(打人的警察)的攻擊性慾求是被滿足的 [5]。
進一步來看,警察的攻擊行為多少也與其穿制服有關。首先,充滿凝聚力的警察團體就會產生強烈的群內偏好(In-Group Favoritism),並容易認為群外(Out-Group)的人是不好的,於是警察傾向於認為抗議民眾不好,且在這個抗議的群體中不論是誰都一樣是可鄙的無賴 [6]。由於警察都穿著類似的制服,並且依規定撕去了自己肩膀上的編號(辨別個人功用),使得執行暴力行為後,其所需付的責任被分散至整個警察群體共同承擔(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7] ,導致警察個體在團體當中得以去個人化(Deindividualization) [8],並且不會認為「自己」會需要付起責任;相對的,會將責任歸責於「團體」共同承擔。
心理學家Zimbardo研究結果指出:在身分被隱匿的情況下,攻擊行為會有增加的現象 [9]。此外,如果不僅匿名,同時也穿著象徵壞人的服飾,匿名攻擊行為又會增加更多。隨後他更進行了著名的史丹佛監獄實驗(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讓一群學生隨機指派,去扮演囚犯或獄卒的角色,實驗到了最後,扮演獄卒的學生會對扮演囚犯的學生進行脅迫與虐待的行為 [10] 。

綜上先前實驗可見,當一群警察聚集又同時進一步削去個人色彩之時,其行為之執行是可以毫無後顧之憂的,更可能抱持著「反正之後算帳可能也算不太到我」、「反正做這件事情的人又不只我一個,要辦一群人的罪是有難度的」……等心態,其隨應做出來的行為是可以預見的,再加上各個穿著制服,被賦予的身分(警察、鎮暴)角色相當明確,更會使勁做出被權威上級要求做出的任何任務,當然包括:驅離民眾,然卻不會計較任何手段,因為是在群體保護之下,大家可以相擁取暖,我並不孤單。也如Gustave Le Bon在1895發表的《群眾心理學》(Psychology of Crowds)所述:因衝動、責任喪失、無理性、愚蠢之群體特質,個體於其中又因匿名、默化、暗示等因素,得表現出衝動、兇殘的反社會行為。
另一權威服從研究:Milgram experiment也指出在權威的驅使下,六成半的人會服從權威,且不會顧及無辜者(受試者)生命之安危 [11] 。實驗過中,受試者會以實驗者要求之最大電壓電擊無辜的受試者,雖然其明顯知道受試者可能會受不了而受傷、痛苦。將此情況套用至鎮壓現場,鎮暴接到上命令,他們理所當然服從權威鎮壓在場的民眾,並不會顧慮到其他,畢竟他認為他終究只是服從而已,責任並不在他身上!

命令的內容也提供了警察合理化(Rationalization) [12] 暴力行為的依據,命令內容驅離學生,其行為是依「法」行政,因此警察會認為暴力是合理的,而刻意忽略了相反的聲音:這樣的粗暴,引發流血行為是不符合比例原則的,畢竟學生們終究只是躺在那邊絲毫不會造成警方人生的危險!他們會這麼做不是沒原因的,如果聽進去了相反的聲音,就會產生行為與自我之間矛盾的不舒服感受,這種感受被稱為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 [13] 。
為了避免認知失調,警察會緊抓著「依法行政」這個論點不放。進而產生更多的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 [14] ,他眼中看到的就只有自己是在「依法行政」而已。在此同時亦有另一個認知失調的例子於:當警察以暴力對待學生之後,並不會因為罪惡感而停止攻擊,反而攻擊會加劇,根據在場旁觀者之轉述,鎮暴在對那群真的不堪負荷而不支倒地之民眾進行驅離時,嘴裡都會碎念道;「再假裝阿」、「再裝死阿」,這是因為如果其不這麼想,並停手去關心傷患,他將會被自己的罪惡感所吞噬,更會因罪惡感而認為自己是壞人,進而產生更嚴重的認知失調,然而,又為了避免認知失調,其又會傾向於認為對方是壞的、受處罰應得的,又進而將對方去人性化(Dehumanizing) [15] 。這被Davis & Jones的實驗證明:讓實驗參與者說出某人的缺點之後,參與者之後就會認為該某人是負面可鄙的。
總結來說,整個行為可以回到Bandura在2004所提:「個體在社會化過程中,將逐漸掌握該團體或社會之道德準則。為了維持團體的人際,個體用約束力來控制自身的行為,以避免違背道德標準,違犯之際,雖然不會受到強制力懲處,但隨之而來的卻是強烈的罪惡感。因此,個體會限制自身的行為已符合內在道德標準;此自我約束力更在殘暴行為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然他亦指出,此約束力能選擇性地被執行,使得一些違反道德標準(殘暴鎮壓)等行為有機會被展現。這種打破原本被限制行為之障礙的歷程稱之為「道德分離(moral disengagement)」,主要透過三步驟完成:
一、道德辯護(Moral Justification):改變自身對事件的解釋或評價,以便之後再為自己的行為辯護。執法過當的鎮暴或警察替自己的行為進行辯護,可以直接自身進行辯護,亦可從「團體」觀點進行。
二、責備受害者(Blaming Victims):藉著責備、汙名受攻擊者,得以認為那些人本應該受到懲罰,讓自己更能接受去攻擊這樣一個行為事實。認為學生或群眾是因為自己的所作所為違法(攻佔行政院)而被攻擊是罪有應得。
三、汙名化受害者(Dehumanizing Victims):一般情況下,人們是很難對被自身所認同的人痛下毒手的!但是對一個被去人性化或汙名化的人則可以攻擊得泰然自若,當鎮暴彼此在溝通時都稱呼靜坐的群眾為「暴民」之時,這些群眾不再受「學生」、「社會大眾」如此人性的觀點所看待,使得暴力尾隨至。Wasmund早在1986就說過:「藉著宣稱敵人的非人性,否認其為人之本質,伴隨之道德顧慮及自然消除」 。因此,對非人性的「暴民」實施殘暴、流血的鎮壓驅離也就是順理成章、無罪惡感之事了 [16] 。
最後,我們應該要以何種角度來觀看警察打人這件事情?我們不能草率的給予褒貶,而要深入的明白事件背後的因果關係才能夠據此下一個結論,這篇文章以心理學的觀點來說明暴力行為背後的真正原因,在透澈原因之後才有評價的可能,也就是說:心理學負責還原真相,其餘的留給歷史評價。
參考資料:
- Frustration–aggression hypothesis — Wikipedia
- Law of effect — Wikipedia
- Death drive — Wikipedia
- Operant conditioning — Wikipedia
- Observational learning — Wikipedia
- In-group favoritism — Wikipedia
-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 Wikipedia
- Deindividuation — Wikipedia
- Philip Zimbardo — Wikipedia
-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 Wikipedia
- Milgram experiment — Wikipedia
- Rationalization (making excuses) — Wikipedia
- Cognitive dissonance — Wikipedia
- Confirmation bias — Wikipedia
- Dehumanization — Wikipedia
- Moral disengagement — Wikipedia
—————————–
更多內容也可以上科技大觀園搜尋「情緒」,或每週六上午8點收看民視53台科學再發現。















-200x2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