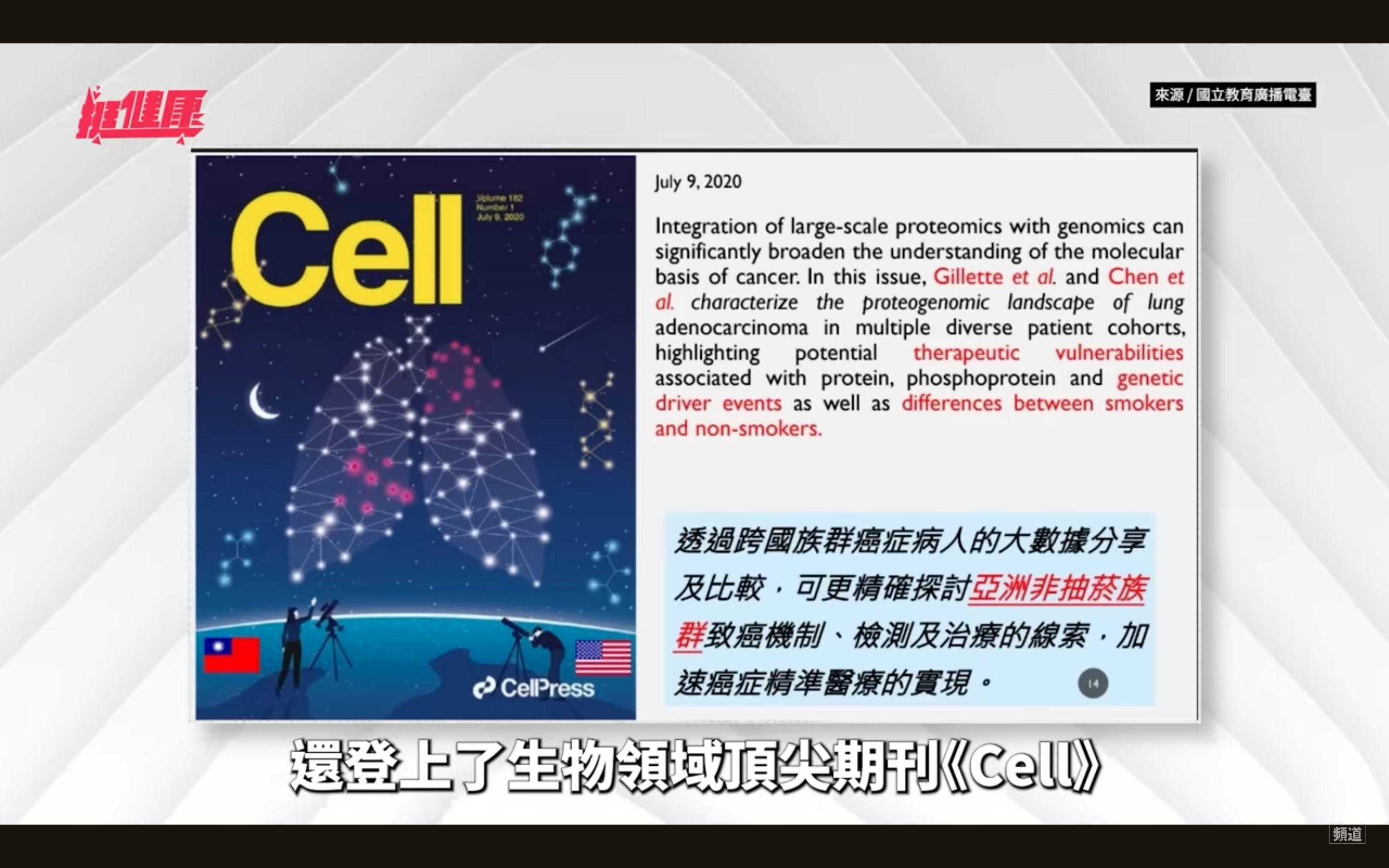- 作者/莎拉.吉爾伯特、凱薩琳.格林
- 譯者/廖建容、郭貞伶
籌錢也是一種科學工作
其實最近這些年來,籌錢已經成為我的主要工作。我猜大家想到科學家時,會想像我們待在實驗室裡,與複雜的器具設備為伍,或是眼睛緊盯著試管裡的東西看。那是我以前的模樣,我也經常希望,現在的我依然如此。
我喜歡待在實驗室裡,每週都得到許多小小的勝利,好比為我剛剛造出並截取的 DNA 製作一幅完美的圖像,或是在病毒滴定時發現和我的預期完全相同的病毒數量。經過多年的訓練,我已經非常善於「從事科學工作」,我也善於訓練別人成為優秀的科學工作者。但直至 2020 年初,我已經超過十年沒有在實驗室工作了。

我這段時間真正在做的事情,主要是找錢。牛津大學雇用我不是為了教學,而是要我進行研究。那意味我必須為自己的研究弄到資金。我必須設法找錢購買實驗室使用的設備和材料,像是組織培養容器或是培養細胞的培養基。我也必須負擔管理費,來支付我們在大學裡所用建物的經常費用,諸如此類。我還必須負責支付我自己和團隊成員(主要是臨床醫生和實驗室研究員)的薪水;為了幫助我們取得資金、記錄花費,並向資助者提交報告,我更另外請了三位全職專案經理和一位約聘專員。
在本質上,每個研究團隊都像個小型企業或是慈善機構。它由一群人組成,執行一連串相關聯的專案,研究團隊的頭兒(也叫作計畫主持人)必須負責找錢,讓團隊裡的人保有這份工作。這項責任會為研究者帶來極大的壓力和挫折,也可能與科學研究的宗旨背道而馳。
舉例來說,有些補助金贊助的是特定領域的研究,所以對於資金的用途給予一定的彈性。不過,有愈來愈多的補助金是為了特定目的而設立。另外還有些時候,我們申請並取得的不是補助金,而是合約。合約的規定比最嚴格的補助金還要多:我們要用這筆特定的錢進行特定的計畫,並且要在特定的時間範圍內完成。假如我們能預先徹底的規劃我們需要做的每件事,就可以順利完成這種合約,例如,製造第一期臨床試驗的疫苗,然後執行臨床試驗。
然而,若合約缺乏彈性,就可能造成問題。有些原因是基於政府的補助時程週期,所以我們必須同意在某個日期前展開計畫,每三個月提交報告,然後在某個日期之前完成計畫。這代表研究者往往要試著在規定的時間和預算範圍內,硬塞入所有想做的事,專案經理要花很多時間追蹤研究者的活動內容,填寫更多表格來爭取更多時間、更多錢,或是變更合約的其他要求。團隊裡若有人請產假或是調到另一個職務,就可能讓整個專案偏離正軌。

更重要的是,缺乏彈性的合約會扼殺創造力或新發現的空間。我們透過合約的嚴謹結構可以瞭解該做什麼事,以及有多少時間可以完成。對於能事先定義的研究來說,這是行得通的,但是對於探索、創新性質的研究就行不通了。
即使在平時,取得資金也是場漫長且充滿不確定因素的鍛鍊。申請書填寫起來非常複雜,流程從開始到結束通常要花一年時間,而且成功率總是遠低於三分之一,這可以從第 2 章我們向流行病預防創新聯盟申請失敗的例子得到印證。研究委員會和其他贊助者(在我的領域,主要包括流行病預防創新聯盟、威康基金會、英國研究與創新機構,最近還多了歐盟)會發布「計畫徵求」公告,徵求某個特定領域的研究申請,申請書要在某個截止日之前提交。
當然,每個贊助單位有自己的申請流程和癖好,會用不同的方法陳述應該要完成的事、所需花費和時間。每個贊助單位對於支付項目也有不同的規定。例如,威康基金會不支付個人防護裝備的費用。在研究實驗室裡,研究者需要使用拋棄式手套,一方面保護研究者的安全,另一方面保護研究工作不被人汙染,因為我們皮膚上的細菌和酶可能會汙染我們接觸的東西。護目鏡和實驗衣也是大多數實驗室的標準配備。又例如,流行病預防創新聯盟會支付個人防護裝備的錢,但不支付文具費用。
大家可能以為科學研究工作很穩定。但事實上,學術研究是一種充滿不確定因素的職業。補助金支持的計畫期間從一年到五年不等,但大學只允許我們在取得補助金之後才能刊登求才廣告,所以又拉長等待的時間。這也代表計畫展開幾個月之後,才會有人真正開始工作,而這些人的聘雇合約不能超出補助金涵蓋的時間範圍。換句話說,若某個人受雇參與一個為期三年的計畫,但他在計畫開始六個月之後才報到上班,那麼他的合約長度就是兩年六個月。
當這些研究者的合約快到期時,他們通常不知道計畫主持人能否取得更多資金,好讓他們的研究工作和聘雇狀態能夠延續下去。此時他們會承受很大的壓力,並面臨抉擇,看是要投入所有的精力完成研究並發表論文,藉此提高獲得更多補助金的機率,還是開始找其他的工作。許多傑出的科學家基於缺乏穩定性和持續存在的壓力,而離開學術研究的領域,塞巴斯蒂安就是一個例子。

找錢、寫論文、到世界各地參加會議以便跟上最新科學進展(並提高個人知名度)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所以像我這樣的計畫主持人通常很難繼續進行實驗室的研究工作。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前的那十年,我曾數度後悔選擇了這條路。但在 2020 年初,後悔的情緒完全消失,我反而把那些年無止境申請計畫補助金的工作視為重要的訓練,因為從摸索的過程中,我學會面對複雜性和挫折感。若沒有累積那些經驗,我一定無法走出 2020 年上半年尋找資金的迷宮,讓我們的疫苗計畫能夠跑得這麼遠、這麼快。
檢驗需要時間,也需要錢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初,全世界還沒有意識到情況有多麼急迫,但當時我們覺得有必要開始啟動疫苗計畫,幸好那時我能夠運用疫苗中樞的資金來啟動計畫。我當時得到的其他資金都屬於目標明確的計畫,但疫苗中樞的資金支持的是一般疫苗開發工作,因此我們得以展開疫苗開發計畫。
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疫苗中樞是一個為期三年的計畫,其宗旨是改善疫苗製造的方法,並邀請英國和海外(尤其是中低收入國家)的製藥公司參與。這件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新疫苗從研發到讓民眾接種的過程中,製造環節有可能成為關鍵的瓶頸;在實驗室裡做出看起來很厲害的疫苗,卻無法大量生產以展開臨床試驗,就等於派不上用場。如果為了大量生產而必須回頭重新設計疫苗,那可能要多花好幾年的時間。
疫苗中樞的資金來自英國政府的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預算,代表這筆錢可以用於其他國家的開發計畫。2015 年,英國政府承諾把 0.7% 的國民所得毛額編列為政府開發援助預算。2014 年伊波拉疫情爆發之後,英國政府決定善用這筆預算,把一部分的錢拿來開發疫苗,對抗導致全球型災難的疾病。
疫苗中樞的資金讓我們撐過了 1 月。我們用這筆錢買了所需的合成 DNA,在實驗室做出第一批疫苗,注射入老鼠體內並分析結果。雖然蘭貝和我從 1 月 11 日就開始設計疫苗,但我知道,假如我們想繼續進行下去,就需要更多資金。
疫苗開發的資金需求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一、設計和臨床前試驗;二、製作並測試起始原料;三、製造臨床試驗用的疫苗並進行臨床試驗;四、大規模製造和大規模施打疫苗。愈後面的階段愈花錢,每個階段的費用比前一個階段至少再多加一個零。我們主要寄望於流行病預防創新聯盟和英國研究與創新機構,於是我開始在他們的網站上搜尋機會,並寫電子郵件給我在這兩個機構的聯絡人。
1 月 13 日,我主動去找流行病預防創新聯盟討論。他們說,他們目前打算「聚焦於速度最快的平台──也就是 DNA 和 mRNA」。我聽了非常驚訝。DNA 和 mRNA 疫苗能夠很快就展開臨床試驗,但不一定比腺病毒載體疫苗快很多。(我們的第三期試驗展開時間遠比他們早很多。)此時絕對是初次大規模使用 mRNA 疫苗的時機,但在我看來,只考慮 DNA 和 mRNA 疫苗的決定一點也不合理。這樣的開始令人感到沮喪。
世界衛生組織在 1 月 30 日宣布新冠肺炎疫情為公共衛生緊急事件。這是世界衛生組織最高等級的警戒聲明,因此,即使他們沒有使用「大流行」這個詞,全世界也應該要注意到事情有多麼嚴重。就在隔天,英國出現第一個確診病例。
儘管流行病預防創新聯盟在 1 月表示要聚焦於 mRNA 和 DNA 疫苗,他們還是廣泛徵求「證明可行的疫苗技術,適用於大規模量產,以便快速對新型冠狀病毒做出回應」。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