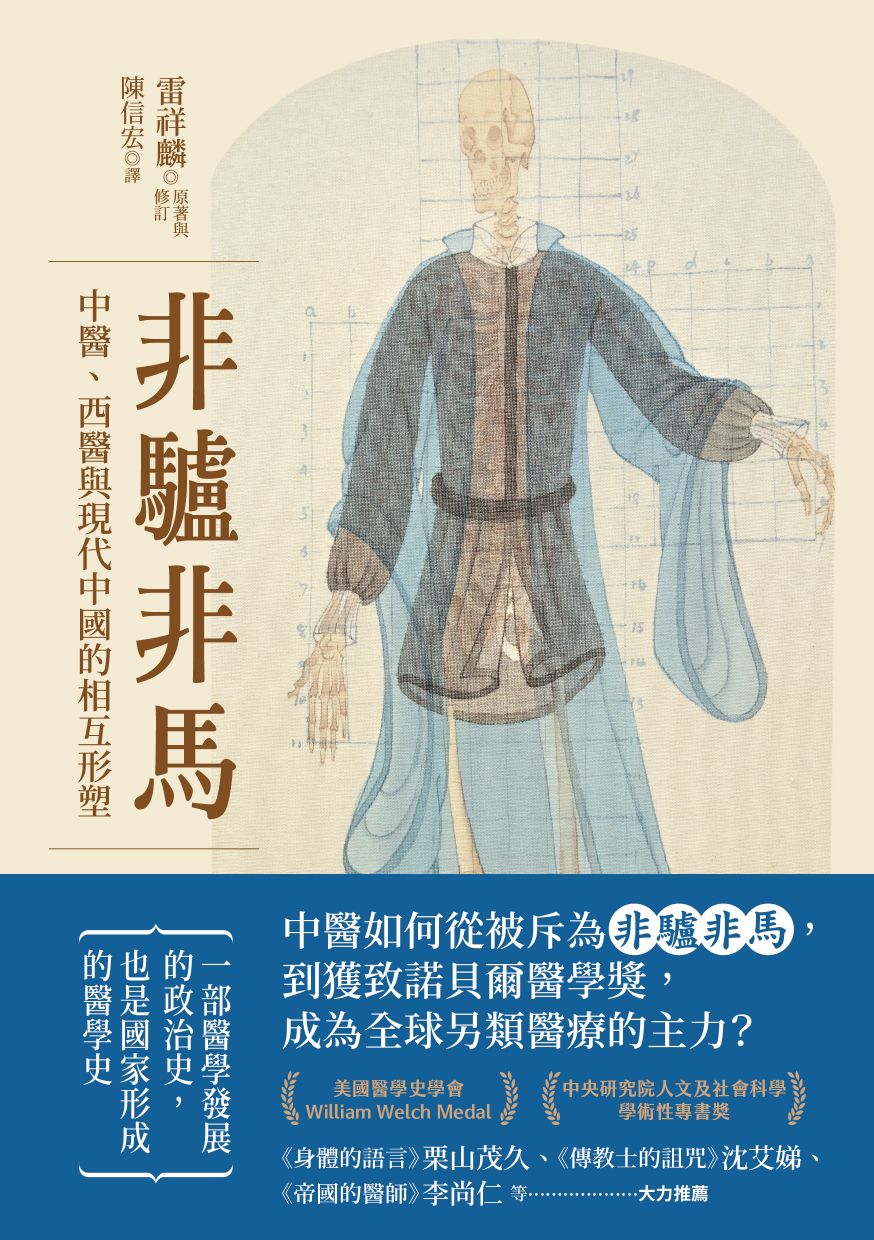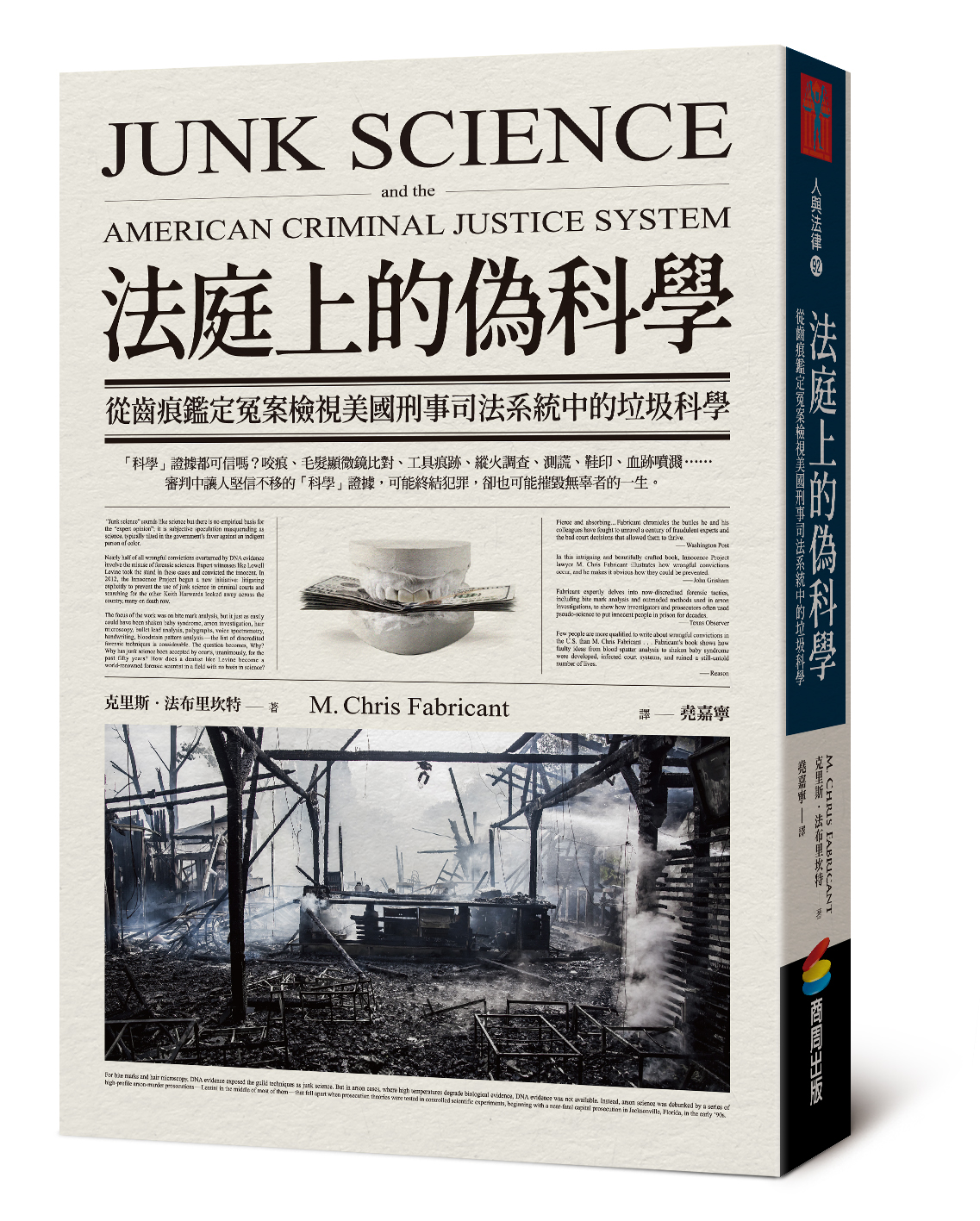- 作者 / 哈利・柯林斯, 崔佛・平區(Harry Collins, Trevor Pinch)
- 譯者 / 李尚仁
至少從一九五○年代起,現代醫學就認為安慰劑效應在科學上已經成立。研究顯示如果施予安慰劑的話,大約有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七十不等的病人似乎可以由此受益。
其中或許最讓人驚訝的是安慰劑外科手術:適當地麻醉病人、切開皮膚,但實際上卻沒有接受有意義的手術;根據報導這樣的手術高度有效。
有時候假的手術甚至似乎比真的手術還更有效。例如,它似乎對某些種類的胸痛和背痛有效。一九九○年代中期的研究顯示,這對膝關節炎有效;只把病人的膝蓋切開,其治療效果和那些對膝關節進行刮搔沖洗的效果一樣好;而一般認為後者是膝關節炎高度有效的標準療法。
不幸的是,這些看來很簡潔明瞭的發現還是引起爭論。現在我們必須穿越另一個更為扭曲的哈哈鏡廳堂:身體不適的人即便沒有接受任何治療也有可能痊癒,而接受安慰劑治療的病人和接受大量醫學介入的病人,同樣可能都是以大略相同的速率自行痊癒。
換句話說,接受安慰劑治療的病人,可能不是由於安慰劑效應而有所改善,而是自行痊癒的;而醫學治療也同樣無效,接受外科治療的病人其實也是自行痊癒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並不是安慰劑效應和真正的外科手術一樣好,而是安慰劑效應並不比真正的外科手術好,兩者同樣都是無效的。
用實驗證實「安慰劑效應」
要了解是否真的有安慰劑效應,必須做另外一種實驗:把接受安慰劑的一組,和完全沒有接受安慰劑的另一組拿來做比較。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有安慰劑效應的話,接受安慰劑的病人的治療狀況,必須要比沒有接受治療的病人好。
兩位丹麥醫師(Hrobjartsson and Gotzsche)蒐集對接受安慰劑治療與沒有接受治療之病人進行比較的研究論文,並在二○○一年進行分析。在這一百一十四個試驗當中,只有少數實驗是直接設計來測試安慰劑;其餘大多數狀況是醫生檢查了三組病人:接受醫學治療的病人、接受安慰劑治療的病人,以及完全沒有接受治療的病人。他們發現就治療狀況的改善而言,接受安慰劑的病人和沒有接受治療的病人,兩組並沒有顯著的差別。
這聽起來像是個決定性的研究,丹麥醫師的報告乍看之下很有說服力。他們分析的研究數量以及病人數目都很大。此一研究似乎推翻了一個重大的成見。但如果仔細檢視論文最後謹慎的但書的話,就會發現其結論並不是那麼地牢不可破。
首先,資料顯示安慰劑對於疼痛的經驗有小的效應,此外安慰劑有可能對一小部分病人或某些疾病有相當大的效應,雖然並非對所有病人或所有疾病都有效應。丹麥研究者所使用的統計分析方法,很容易掩蓋掉這些輕微的效應和少數的疾病與病人。更讓人憂心的是下面所要討論的複雜邏輯,要說明此一邏輯,在句子結尾必須使用越來越多的驚嘆號。
不管是安慰劑或其他的療法,是無法以盲目的方式和沒有治療的狀況做比較!病人和治療者都會知道誰沒有接受治療;事實上,沒有接受治療這件事情是無法隱瞞的,否則這就不是「沒有接受治療」,而是接受安慰劑。
現在,事情變得更複雜
如果醫師和病人知道誰沒有接受治療,我們會預期這將帶來期待效應以及報告效應;如果安慰劑有作用,我們會預期安慰劑組病人和未受治療組病人的差異會更加顯著!換句話說,沒有接受治療的病人應該會對自己的前景感到悲觀,而執行治療的人應該會預期該組病人不會有什麼改善;因此我們會認為,不論施行治療者或接受治療者,都會有很強的報告效應,而且期待效應還會強化這兩者。
總而言之,即便沒有安慰劑效應,在這些非盲目的實驗中,由於沒有治療那一組的負面報告偏差和期待效應,實驗結果應該會看到有安慰劑效應。在這個愛麗絲夢遊的仙境中,這應該是種永遠不會失敗的實驗!不管有沒有安慰劑效應,結果應該總是看起來會有安慰劑效應的!!
現在這些實驗的結果卻是沒有顯著的安慰劑效應,那麼意味著沒有任何的期待效應與報告效應出現在這些實驗中,這顯示這些實驗一定有什麼問題!!!就像孟德爾關於遺傳性徵的著名實驗一樣,實驗結果太漂亮了,使它看來好像一定是造假!
丹麥研究者在回應這些質疑時論稱,由於大多數的實驗有三組病人,而非兩組,因此病人和分析師所在意的都不是安慰劑組和未受治療組的差異,而這點或許減低了報告效應與期待效應。然而這樣的論點看起來仍是很薄弱的。
無論如何,缺乏期待效應和報告效應即便不是決定性因素,也有其他理由讓我們不信任這個研究的結論。正如前面所說,沒有接受治療的那一組病人,無可避免地會知道他們並沒有接受治療。如果他們的疾病很嚴重的話,那麼他們可能會覺得既然在這個研究當中沒有接受任何治療,便會自行決定以和此一研究無關的方式尋求其他的治療(參見第四章有關維他命 C 試驗的類似主張)。這點並不適用於安慰劑組,因為這一組的病人以為他們正在接受治療。結果就是,有無自行治療所帶來的差異,可能導致不同組別的成功率沒有太大的差別。
無法執行的雙盲實驗
考量上述兩種反對丹麥研究人員結論的論點,讓我們不知道該採取什麼樣的立場,這種情況經常出現在困難的統計科學中,我們只知道不能像過去那樣把安慰劑效應視為理所當然,但我們仍舊很難確定它並不存在。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在安慰劑組和沒有接受治療組之間進行一場雙盲實驗,然而這在定義上就是不可能的(在這個句子最後不得不加上一個驚嘆號)!
儘管有這些學術爭論,製藥公司與藥物試驗的執行者乃至製藥公司的批評者,都認為安慰劑效應是真實的。批評者指出,所謂的雙盲通常無法執行,因為如果藥物有昏眩或口乾等副作用的話,病人經常能因此猜出他們吃的是真藥或是安慰劑。這意味著即便藥物在隨機對照試驗中勝過了安慰劑效應,但也可能只是因為由於藥物有副作用,而有了更強的安慰劑效應!
製藥公司和為其執行試驗的單位非常重視安慰劑效應的真實性,它們實際上甚至還評估接受試驗的病人對於安慰劑效應的敏感程度,試圖排除掉那些容易受到暗示的病人(隱藏式的心理治療)等等。我們可以這樣說:就安慰劑效應如何影響我們對醫學的思考而言,它是真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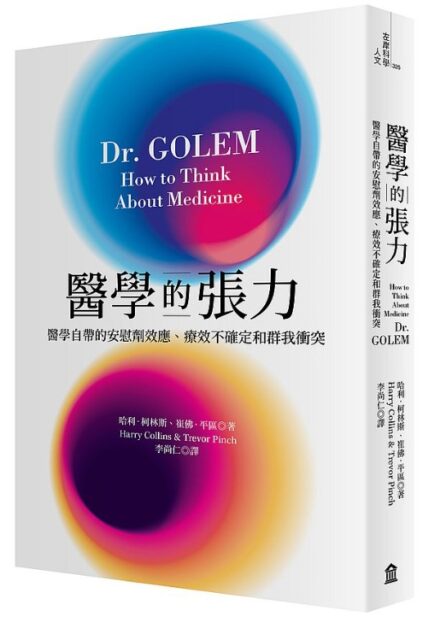
——本文摘自《醫學的張力》,2021 年 9 月,左岸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