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傑克.路易斯(Jack Lewis)
- 譯者: 鄧子衿
沙發馬鈴薯
現代的社會中,有一類人的懶惰行為就在我們眼皮底下發生,但往往受到忽視。這種最糟糕的懶惰者往往很少出現在公共場合,他們一想到要做好自己應盡責任時便厭惡不已;除了一起生活的人之外,其他人都見不到他們。如果你剛好走進房中遇到這種人,可能會發現他們坐著不動或呆若木雞。他們極致的惰性狡詐地隱藏在看似專注的表象之下,但是可別被騙了。
審判日來臨時,這些人會受到惡魔貝爾芬格的誘惑,開始無止盡奔跑,就像被某個毫無人性的體育教師折磨一般。那些人在地球上過了有如過客一般短暫的人生,並且浪擲太多時間在追求徹底虛幻的目標,這些目標哪怕達成了,對其所處的社會也不會帶來半點價值。這些人就算保住了飯碗,也會在公車、飛機或火車的交通行進期間,也就是眾目睽睽下,眼睛死盯著螢幕。

他們是科技的奴隸;是「糖果傳奇」(Candy Crush)、臉書、IG、Snapchat 和推特的狂熱粉絲與忠實奴僕,並且將空閒時每分每秒都花在螢幕上。此外還有那些把所有餘暇時光都用在大型多人線上遊戲(MMOG)上和食人鬼、矮人、機器人與太空海盜進行虛擬戰鬥的成年人。這些人當中有些還在養孩子,在小孩終於上床睡覺之後,熬夜不睡,把自己寶貴的睡眠時間花在線上賓果遊戲、在客廳中舒服坐著玩線上輪盤與樸克錦標賽。大家在這些數位娛樂上浪費了許多光陰,而這些時間本來可以用在其他有用的事情上。
Steam 這家大型線上遊戲公司會記錄玩家在各種遊戲上所花的時間,對我們這一章的討論很有幫助。在這份「可恥名單」(Wall of Shame)上的前十名,玩遊戲的時間超過五萬個小時,每年平均玩超過五千小時的遊戲。要知道,就算你每天玩八個小時遊戲,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下來,也還湊不滿三千個小時。顯然有些人生活中就只有遊戲,其他什麼事情都不管了。那些看太多網路色情影片的人腦中紋狀體的結構改變,導致人的動機也跟著改變:一心只想看色情內容,不顧其他事。同樣的,每年花許多時間投入電玩的人,腦中也會有這樣的改變。如果針對那些每年看幾千個小時網路色情片的人、猛看YouTube 上貓咪影片的人,或是拼命玩自己最愛的社群媒體的人,也都統計了類似Steam 這份可恥紀錄,那我們會發現,懶惰不只是相當嚴重的一個大罪,也是現代社會中最為普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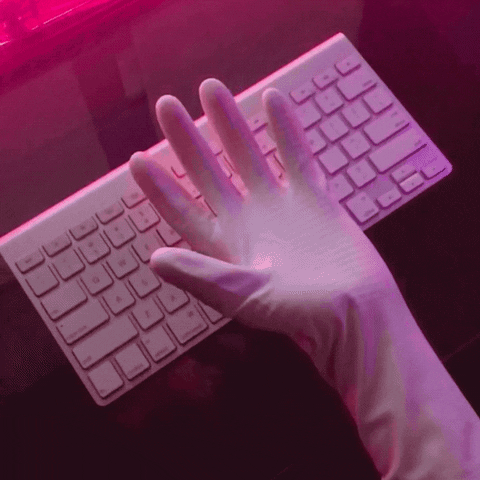
消遣放鬆或懶惰沉溺
並不是每個使用這些應用程式、玩線上賭博或是有玩電玩的人,都會犯懶惰之罪。這取決於生活中其他時間裡,一個人是否有生產力,如果有,那麼他想要有限度地在空閒時間黏著手機、平板電腦或是電腦螢幕,那都是自己的選擇。甚至有愈來愈多證據指出,玩第一人稱視角的射擊遊戲的確有助於增進各種認知能力,但是有很多人最後都沉溺在這些遊戲中。由於這些數位產品和遊戲都是設計來鼓勵使用者宛如成癮般地投入其中,只有最自制的人才能控制自己的使用時間。很不幸,有許多人最後把過多時間都耗在從客觀角度看來毫無意義的數位娛樂上,也因而對整體生活品質都帶來了不良影響。
在現在這個時代,數位產業的龐大規模營造出了假象,而犯下最嚴重懶惰之罪的人就是那些每天不分晝夜,把所有可用時間都用來盯著螢幕的人。這些崇拜數位科技的重度螢幕使用者腦中的紋狀體迴路最開始往往都沒有毛病,在養成這種習慣之前多巴胺的濃度也沒有失調。其中絕大多數人都是自主選擇要揮霍自己寶貴的空閒時間,而對於世界的運作來說,他們幾乎沒有產出什麼有價值的東西。這些人正是惡魔貝爾芬格的子民。

我們還在尋找平衡點
在現代,使用數位產品來娛樂並沒有錯,但是絕大部分人都沒有好好思考過,花那麼多時間坐在那裡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這可能是因為那些科技問世的時間都很短,出現的速度也很快,大家還沒有時間好好思考現況,或是調整行為、避免不良後果。下一代的人很可能在這方面得以找到平衡,不過現在科學和社會依然在探究數位產品對人而言的利害得失,我們這一代人就這麼不知不覺,成了範圍遍及全世界、規模巨大無比的實驗中的白老鼠。
電腦遊戲設計者得要負一些責任,可以這麼說,他們對人類報償路徑的運作,要比任何研究紋狀體的科學家還要清楚(只不過已內化而不外顯)。他們擁有的資料比任何國際合作的科學團隊還要多。他們有充分的資金來源,要盡可能讓最多的人黏著他們的產品不放。在這個地球上,沒有哪種機構比電玩產業更了解要如何打造出非藥物產生的快感體驗,讓人使用了之後想每天不斷再用,通常還讓它成為生活中優先排序最前面的活動。你可能覺得這種貶斥未免太小題大作,玩遊戲才沒有害。但事實上,遊戲已經奪去了一些人的性命。如果自戀與肥胖的死亡警訊最早是在美國出現,對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有預先示警的作用,那麼過度使用數位科技的「預言水晶球」就非東亞莫屬了,我們可以從中窺見未來的模樣。
二○○五年,一對南韓夫妻意外讓自己三個月大的孩子餓死,然而諷刺的是,他們怠忽親職竟是因為全心投入在一個照顧虛擬嬰兒的遊戲中。大型多人線上遊戲《魔獸世界》散布於世界各地的玩家會在遊戲中組隊戰鬥;二○○七年,中國的張先生在連續玩《魔獸世界》五十個小時之後死亡。二○一二年二月四日,《台北時報》(Taipei Times)報導,一位二十三歲男性在長時間值班之後,還到網咖報到,並於桌前玩了十小時遊戲後身亡。這篇報導的驚人之處,並不只是因為有人玩遊戲玩到死——在二○一二年,玩遊戲玩到這種程度在東亞來說並非不尋常——讓人意外的是,死者旁的其他顧客一直要到死者身體僵硬轉青的時候,才發現他已死去多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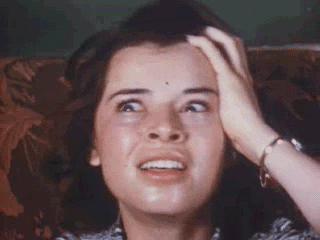
成癮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疾病
許多人身上原本應該用來從事其他有意義和有助益之事的時間和精力,都浪費在毫無建設性的活動上。有些人現在已經對遊戲成癮了,但沒有人一開始就成癮。在腦部變得上癮之前、在一個人因為玩遊戲能帶來愉悅而自願耽溺的時候,他的確犯下了懶惰之罪。一旦某人對於自己的愛好投入了夠多的時間——大食客變得病態肥胖,或是色情影片迷過度縱欲而對網路色情片上癮——這時就有比較多判斷上的灰色地帶。紋狀體的結構產生了變化,玩遊戲從自發轉為強迫,於是就比較難說誰是犯下了懶惰大罪者,而誰又只是個無助的成癮者。
社會上有些人對無家可歸者、長期失業者與身心症患者的態度非常嚴苛,但這些人並無法自由選擇自己的命運。懶惰罪名應該要冠在自己選擇把所有可用時間與精力浪費在瑣碎娛樂中的人頭上。
誰還去管宗教呢?應用程式商店裡盡是給大眾服用的鴉片。而在未來,虛擬實境這種數位海洛因很快就會出現在我們家中了。希望大家能在第一波矽谷的電腦革命中得到教訓,否則我們都會被吸入數位世界的懶惰黑洞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