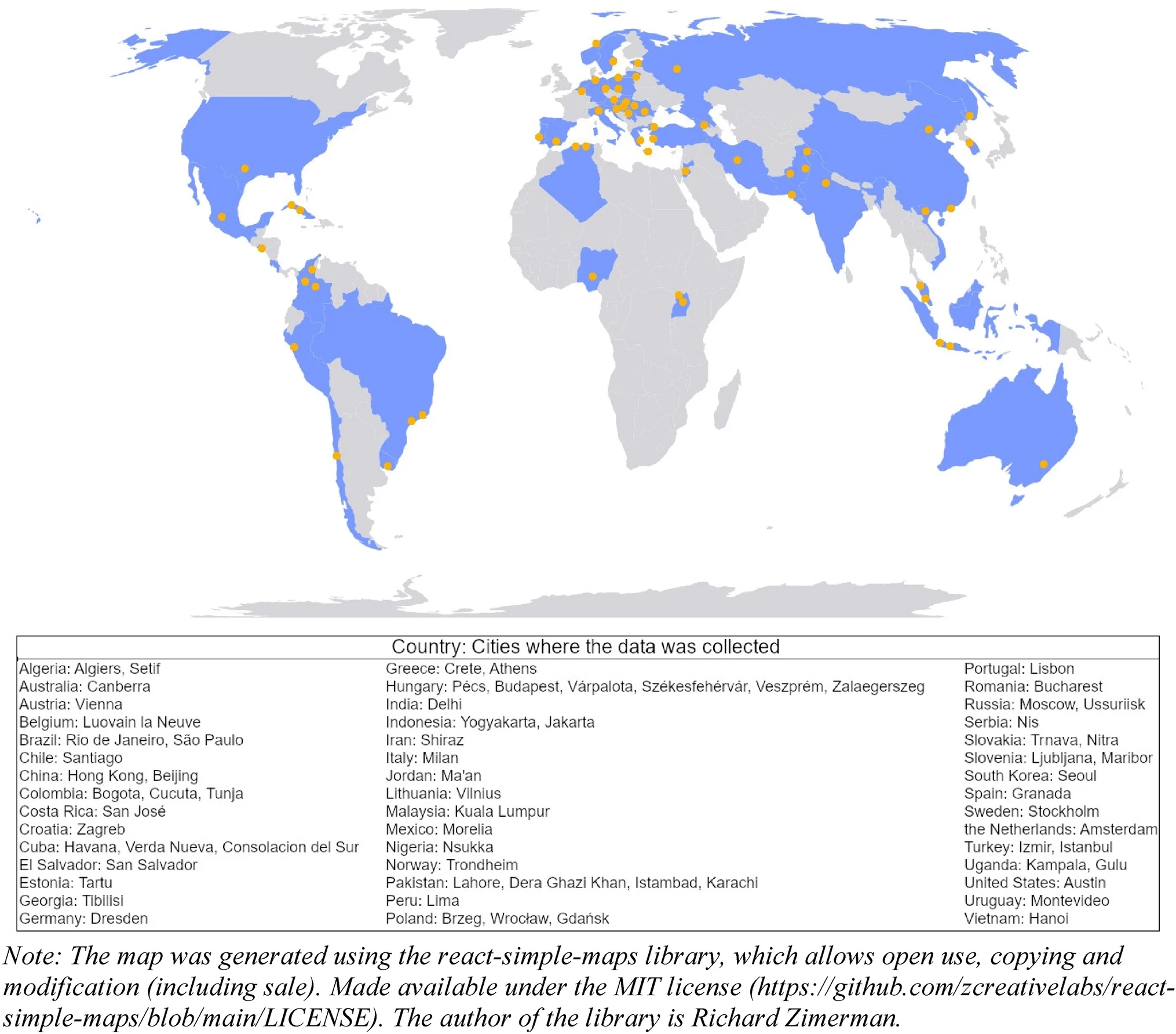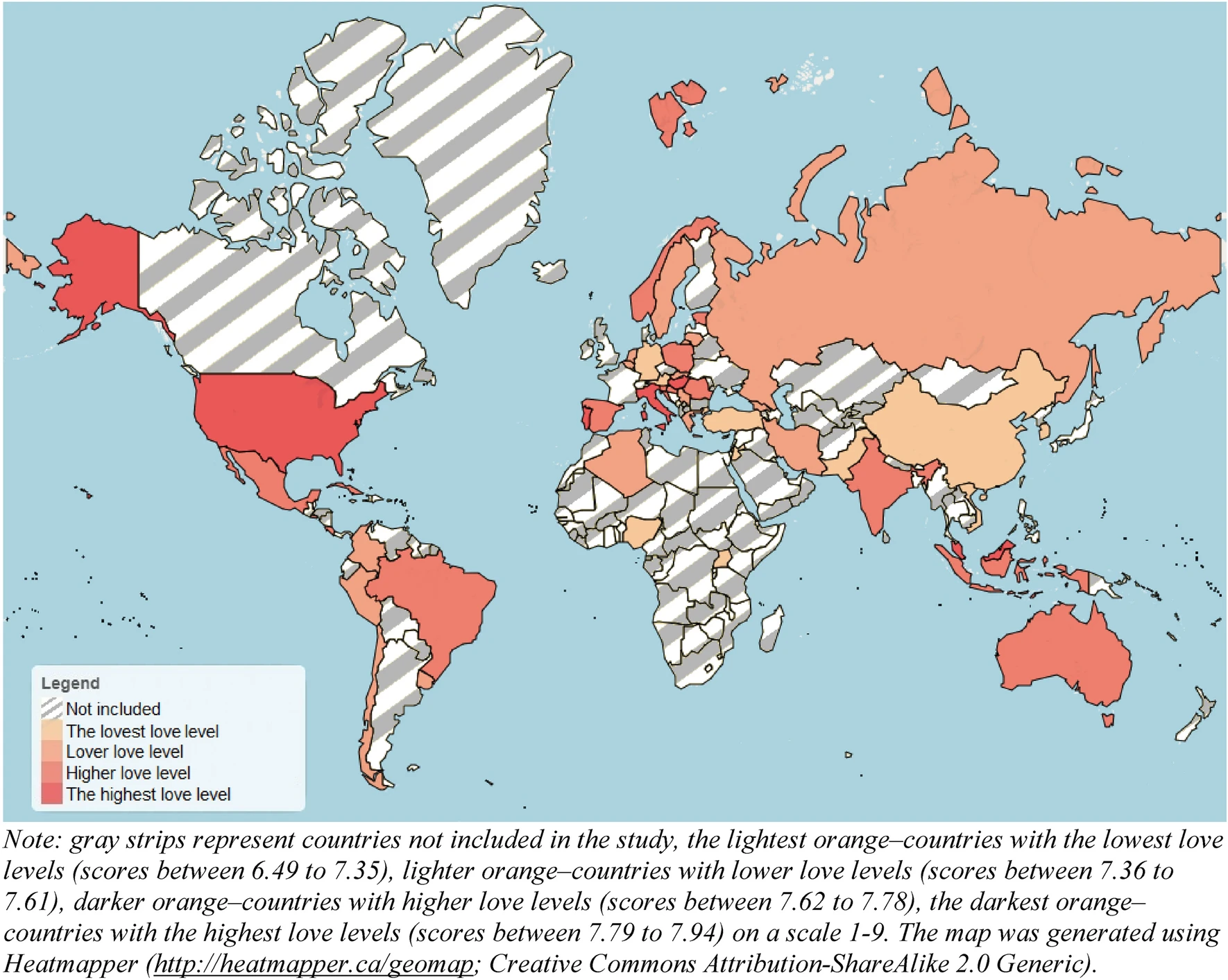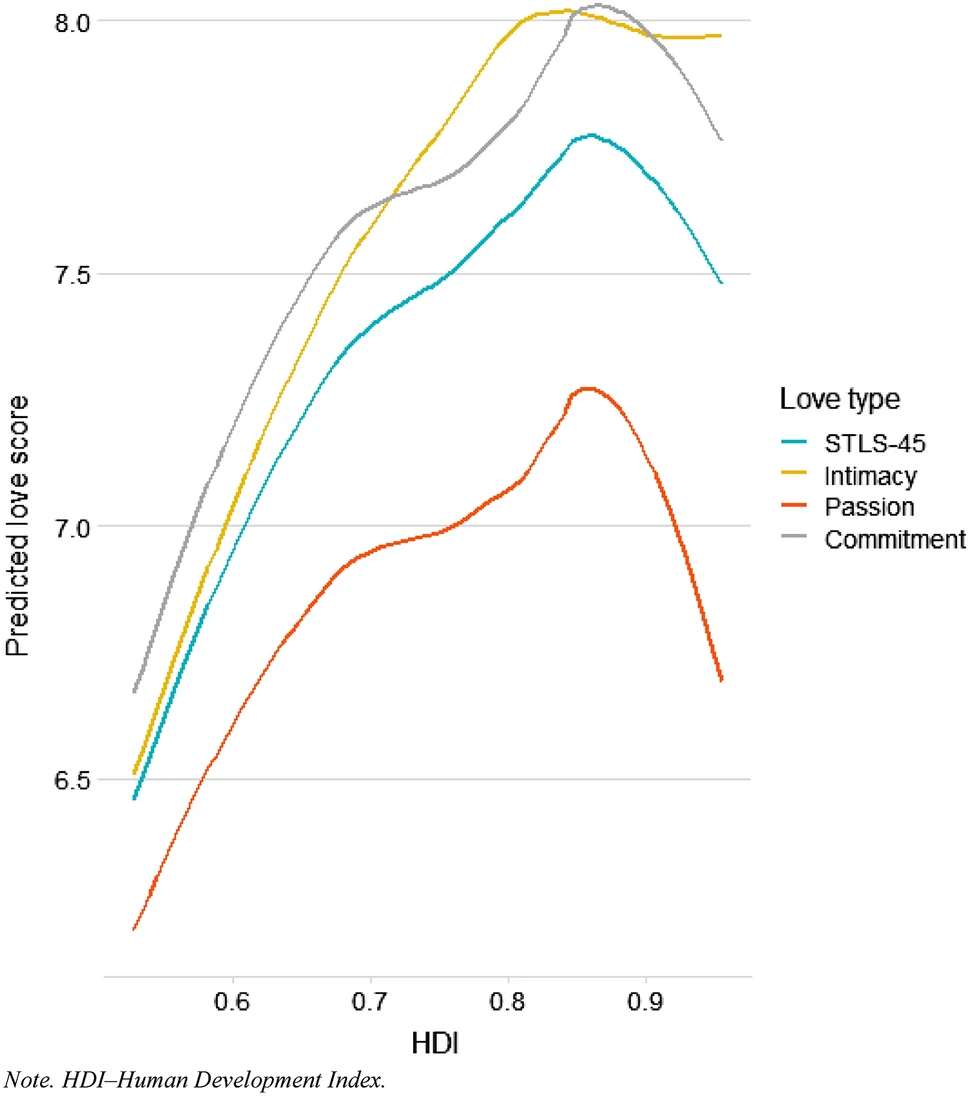- 作者|Vivek H. Murthy
- 譯者|廖建容
集體更甚於個人——集體主義
全世界有許多傳統社會建立在共享的歷史、錯綜複雜的家系、當地的價值觀、交織的故事,以及宗教信仰的基礎上。就和哈特派信徒一樣,歸屬感是這些文化的核心。南非的祖魯族甚至有個說法:「我在是因為你在,你在是因為我們同在」,這個說法還可以濃縮成一個字「ubuntu」,意思是「透過其他人而活著」。「ubuntu」與個人主義相反,它把個人與群體的連結放在第一位,視和諧為最重要。
研究者用「集體主義」來描述一種結構上強調集體更甚於個人的團體,相反的概念是個人主義團體。另外還有第三種文化:正在從集體主義進入到個人主義的「過渡」文化。羅卡奇發現,過渡文化裡的年長者特別容易感到孤獨,因為他們已經習慣擁有強大的社會支持,當社群裡的成員開始各自打拚後,年長者很可能不知道如何適應新的處境。羅卡奇說,在個人主義傳統盛行的國家(例如挪威),年長者很習慣自己一個人生活,但在日本或以色列,年長者往往將獨居視為不正常,並因此感到沮喪,也難以承認這個事實。他們比較容易將社交孤立視為自己的問題,彷彿獨居代表「我不值得別人花時間來看我」。

極端集體主義文化的服從與脫離
我們或許很容易將傳統文化與其他集體主義文化浪漫化,但也不該將它們視為孤獨的解方。這類文化幾乎容不下個人發展與表達的空間,一旦你脫離或拒絕服從規範,將會面臨另一種類似疏離感的孤獨。當歸屬感是在嚴格的條件下才能獲得,即使是輕微的違背規範也可能引發痛苦的後果。當你反抗與違背準則,可能導致其他人開始躲避你、將你放逐,甚至更糟的情況。
對於讓家族蒙羞的成員施予榮譽處決(honor killing),是極端的例子,但遺憾的是,在南亞、北非與中東,每年仍有數千件這樣的案例。鄰居之間經年累月的長期不睦,也可能導致集體暴力衝突、文化分裂,乃至戰爭。我們在土耳其、印度、盧安達和前南斯拉夫都見過這樣的悲劇。中東情況更嚴重。
傳統社會的根是部落。部落將維持緊密連結的所有好處,都賜給遵從社群制定的信條和行為準則的成員,對於不遵守部落意識型態和規矩的人,就加以抵制反對,而且往往將他們妖魔化。如同古老的部落,傳統社會傾向於對外來影響與變革心存懷疑,因為那些東西不是完全在個人的掌控之中。擁有認識了一輩子的好朋友和鄰居的支持,固然令人安心,但它也可能使人感到極度孤獨,甚至致命——當你的膚色、性傾向或種族和其他人不同,或是你嚮往族人禁止的職業、宗教或生活方式。在今日的美國,成長於關係緊密的極端主義社群、長大後開始質疑家族價值觀的孩子,就會體驗到這種孤獨。
德瑞克.布萊克(Derek Black)正是其中之一。德瑞克的父親曾經是白人民族主義運動的領袖、三K 黨(Ku Klux Klan)的「大巫師」(Grand Wizard),以及美國第一個、也是最大的白人至上網站「風暴前線」(Stormfront)的創立者。德瑞克的教父是大衛.杜克(David Duke),他也曾是三 K 黨的「大巫師」。德瑞克在家人深厚的愛與保護中長大,從小在家自學,由家族成員教導。由於周遭只有家族成員圍繞,所以他從來不曾質疑家人相信白人至上的假定,直到他離開家庭,到「外面」上大學。
我和德瑞克在 2019 年有個機會聊天,他回憶道,「我們感受到某種意義和目標,覺得自己做的是對的事。」
為了說明這種親密的關係,他告訴我一段青少年時期的經驗:他與家人進行一趟長途公路旅行,「我有機會和社群裡形形色色的人相處,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這種把人連結在一起的人際網絡,感覺非常踏實。」
德瑞克告訴我,問題是,這種緊密關係有一部分是建立在對外人的憤怒和仇恨之上,尤其是對猶太人和少數民族。德瑞克很難對外人產生同理心,因為他所處的文化強調外人和他之間的差異,而不是他們共有的價值觀或經驗,並且習於用負面的方式描繪外人。
走入不同人群認識社群的意義
當德瑞克在 2010 年到佛羅里達新學院(New College of Florida)讀大學時,他的為難處境開始被突顯出來。「上大學讓我第一次看見成長環境以外的社群,而且是一個我能夠認同的社群。我後來也開始關心這個社群。」德瑞克曾經和父親一同主持廣播節目,有位打電話進電台的聽眾稱這所大學為「多元文化主義的溫床」。德瑞克的父親認為,德瑞克上大學相當於是到敵對的人文陣營臥底,進行祕密蒐集情報的任務。但德瑞克天生充滿好奇心,突然間,他的周遭全是個人信念、政治理念和性別認同與他不同的人,「我想要更深入了解他們的不滿和問題。」
他原本打算悄悄執行這個想法,但這個計劃有一天突然被中斷了,因為有個學生發現了他的身分,並在學校的留言板「爆料」他是白人民族主義者。結果,德瑞克遭到許多人的撻伐,但有少數人例外。有幾個同學向他伸出援手,和他進行深入對話。這些人帶著尊重與同情之心,主動與德瑞克分享交流。這個舉動逐漸改變了德瑞克的信念,並幫助他意識到自己原本的價值觀極具毀滅性。德瑞克後來揚棄了家族的信條。雖然他試圖與家人維持關係,但是家人認為德瑞克背叛了他們的核心價值觀,關係變得很緊張。白人民族主義社群裡的人,大多唾棄他的做法。

與家人的關係斷裂雖然已經好幾年,但德瑞克至今依然非常痛苦。他告訴我,這件事促使他認真思考,社群造成的正面與潛在負面影響。
「社群真正的意義與目的,」德瑞克反思的結論是,「來自擁有共同的理念,根植於共同的信念。不論這信念的基礎是宗教、政治、藝術或是體育運動,都反映出某個理想世界的獨特願景。一旦信念(連結的基礎)是建立在仇恨與恐懼之上,便會滲出毒性,慢慢侵蝕社群的正當性,最後破壞所有成員的幸福。這個情況不只發生在白人民族主義這類極端主義者身上,其他維繫關係的基礎是排斥與仇恨他們視為「不同」的其他人,最後也將面臨這樣的結果。」
雖然這類社群的成員可能感受到與彼此的連結,然而他們對於非我族類的懷疑,會使他們以嚴格的條件篩選往來的對象,進而限制了他們與廣闊世界的連結。他們對別人的信任、覺察與了解,也會隨之消逝。對於像是德瑞克這種決定冒險離開社群的人,這種情況將會使他們感受到的威脅與孤獨感更加強烈。然而即使刻意為之,能夠完全與世隔離的人少之又少。在現今這個極其多元的社會,我們注定會與不同背景的人交會。要在這個社會建立歸屬感,必須看見並欣賞存在於種種差異之上的共通人性。
這意味我們需要運用同理心,使自己不陷入從狹隘觀點指責他人的束縛,想像另一個人正在體驗的感受。即使那個人來自不同的種族、人種、宗教或國家背景。我們要有意願一起發現與培養共同的興趣和目標。
這不代表我們應該完全忽視彼此的差異與歧見,這代表的是,我們的共同點可以讓我們團結在一起,在我們因為衝突感到孤獨與焦慮時,幫助我們克服這些問題。如同德瑞克發現的,若社群只將同理心留給志同道合的人,這個社群注定會被整個社會疏遠。於是,隨著世界不斷改變與成長,社群成員開始覺得憤怒、害怕,愈來愈容易感到孤獨。
把人們凝聚在一起,使我們覺得所有人真正彼此相屬的,是連結,而不是仇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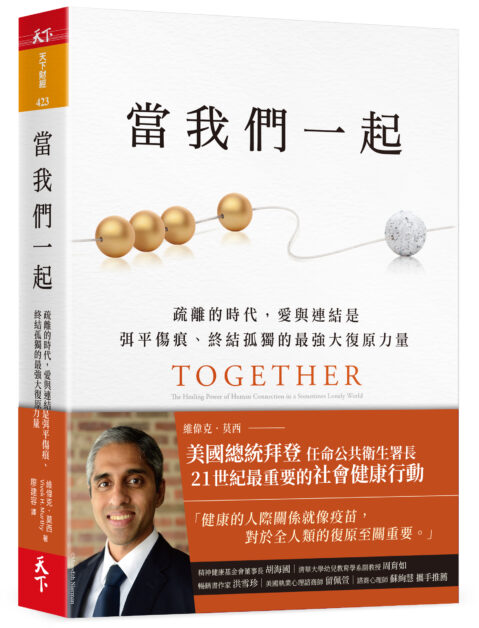












-200x2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