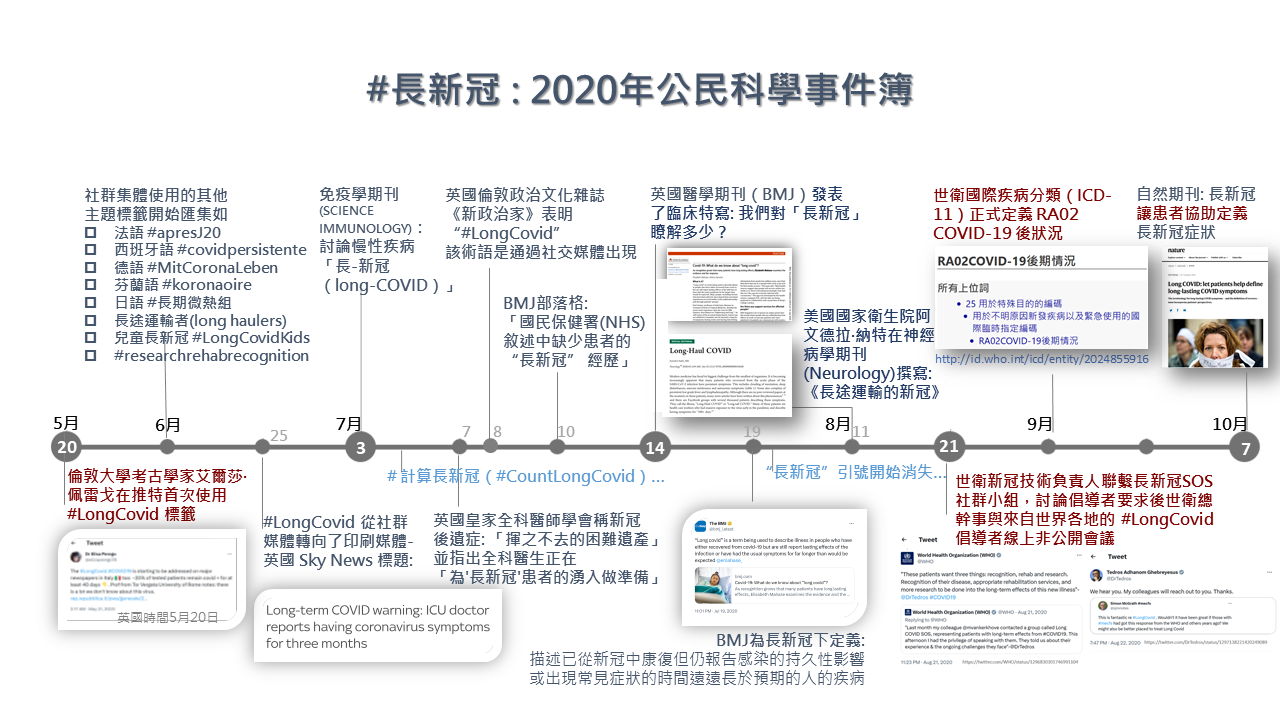「不,你沒明白,它的本質就是不斷地重來。」 ──卡繆《鼠疫》
法國存在主義作家卡繆於 1947 年發表小說《鼠疫》,描述 1940 年代的法國殖民地阿爾及利亞,境內一座城市奧蘭(Oran)爆發鼠疫而封城的故事。雖然情節均為小說家杜撰而成,但故事背景則確有所本──奧蘭曾於 1849 年爆發霍亂,造成大量居民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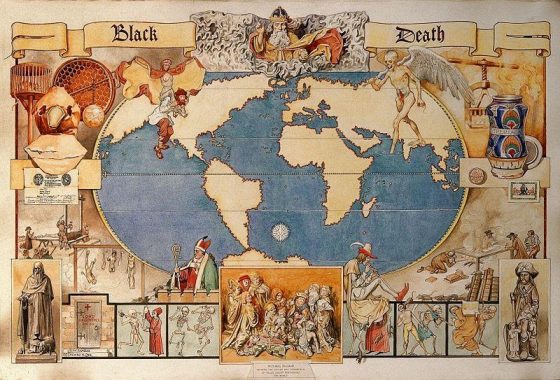
卡繆將這場歷史上的霍亂改為鼠疫──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具毀滅性的傳染病,它每次出現都猶如死神降臨,奪走無數人命。尤其十四世紀的鼠疫大流行,至少造成全世界七千五百萬人死亡,其中歐洲更有三分之一人口因此喪命。
疾病造成的群體恐懼的確是小說常見的題材,但卡繆的《鼠疫》其實是藉由疾病,隱喻二戰納粹蹂躪下的歐洲;但誰能料到,此番虛構情節到今日竟成了現實。

如今在全球肆虐的 COVID-19(亦作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疫情雖然沒有鼠疫那麼可怕,卻也已經奪走超過二十一萬條人命;世界各地的城市亦難逃奧蘭的命運,因為封城而成為與外隔絕的孤島。
此時再讀《鼠疫》,既視感如影隨形,甚至連心理階段也相差無幾。我們正面對的處境與《鼠疫》有多相似?書中不同角色的反應與作為,可以帶給我們怎樣的省思?在這人心惶惶的當下重讀《鼠疫》,或許有助於我們找到因應之道──不只是此次疫情,也包括未來的危機。
第一階段:當疾病的哨音響起,否認疫情
在小說中,第一個發現異常的,是一名醫師。
醫師李厄在住家的樓梯平台發現一隻死老鼠,但是當他據實以告,門房卻不相信,堅稱這棟樓不可能有老鼠,一定是有人惡作劇。其實門房並不是故意置之不理,相反地,正因為他向來很盡職,所以才無法接受這個事實──怎麼可能有老鼠出沒,他卻從未察覺?
就連醫師李厄也陷入自我懷疑,明明已經發現病患出現類似鼠疫的病灶,卻仍說服自己「區區幾個病例不會形成流行病」。這樣的心態也出現在醫生公會會長李察身上。當會議上有醫師吐出鼠疫這個病名時,他連忙阻止說:「不應該過度驚慌,目前只能說這是一種會引發鼠蹊部併發症的熱病,假設的說法無論在科學上或生活上都很危險。」
從門房、醫師到公會會長,他們都不是欺上瞞下的人, 只是「因為瘟疫是不可想像的」,擺在眼前的雖是事實,卻難以接受。

如書中所說:「疫災其實是常見的事,只是一旦落到自己頭上往往令人難以置信。」這群人並不是特例,一般人在沒有深入了解時,也不會輕易相信噩耗。 Kubler-Ross 的悲傷的五階段(The Five Stages of Grief),人面臨哀傷或災難時的第一反應,就是否定──人們拒絕承認已經發生的事實;他們試圖告訴自己,生活和以前一樣,沒有改變。
COVID-19 的疫情蔓延與人的這種心理有很大的關係,當二月中國與亞洲各國已經出現多起病例時,歐美國家卻仍隔岸觀火,並未立即採取嚴格的防疫措施,輕忽疫情的嚴重程度,將其比擬為一般流感,主觀上先排斥大型瘟疫的可能性,直到無可迴避才願接受噩耗,背後多少就是這種拒絕承認事實的心態。
第二階段:封城後,每個人都成為一座孤島
「瘟疫為奧蘭市民第一個帶來的就是放逐。」卡繆如此形容封城後奧蘭市民的感覺。這似乎與我們所認知的放逐定義不同,一般所謂放逐指的是流放到異地,不得再返回家鄉,而奧蘭市民被迫困在土生土長的故鄉,為什麼算是放逐?
放逐帶來最大的痛苦,就在於硬生生切斷情感上的連結。無論是與家人、愛人,或朋友的情感,甚至是對家鄉的孺慕之情,因為被迫分離而只剩回憶與想念,更因看不見終點而倍感痛苦──這正是奧蘭市民的感受。

愛人朋友因封城令困於城外,不得相見;家人感染疾病被送往醫院隔離,生死未卜;縱使有幸所愛的人都在身旁安然無恙,原來的生活也已經完全走樣,周遭環境雖然沒變,卻已不再是熟悉的家園。雖然仍身處熟悉的家鄉,卻像是被鼠疫放逐到陌生的異鄉,沒人知道疫情何時結束,沒人知道何時可以重拾往日生活……。
書中的封城寓言,在 COVID-19 肆虐的現在全球許多城市封城,奧蘭市民的情境在許多地方真實上演。人們面臨生離死別的痛苦,甚至無法待在所愛之人身旁,執子之手,陪他(她)走完最後一程,也無法見最後一面,只能排隊領回一罈骨灰。
第三階段:看不見盡頭的疫情,帶來冷漠與仇恨
面對瘟疫這種無形的敵人,無法正面攻擊,也難以劃出一條的有效防線,只能祈禱每天公佈的統計數字帶來好消息。
然而,漫長的等待逐漸消磨人們的意志,奧蘭市民原本「憤世嫉俗的激烈情緒被一種消沉所取代」。因為「它(瘟疫)的曠日持久,天大的苦難也變單調了。」市民們因此變得冷漠,原本還會互相關切,「但經過這長久下來的警戒之後,好像每個人的心腸都變硬了,無論是走路時或生活中聽到痛苦呻吟聲都能置若罔聞,彷彿那是人類的自然語言。」
主動挺身而出加入防疫陣線的衛生小組成員,也逐漸疲乏,「慢慢萌生一種奇怪的冷淡」。因為不斷面對被鼠疫折磨的病患與家屬,「唯一自衛的方式就是躲進這種冷酷中,……而內心還保留的那些也都被疲憊給剝奪了。」

冷漠背後代表的就是失去同理心,而喪失同理心往往便導致仇恨,因此後來開始出現暴力、劫掠等犯罪事件,整座城市宛若陷入地獄。不幸地,這次 COVID-19 疫情爆發後,歐美部分國家也發生了攻擊亞裔的事件;而臺灣雖然疫情並不嚴重,卻也出現反對讓滯留在外的同胞返臺的輿論。無論如何,這都值得我們警惕在熬過漫漫長夜時,永遠都要記得黎明總會到來,不要反被黑暗吞噬。
對抗鼠疫的唯一方法:正直
如何確信黑夜終將過去,隧道盡頭有光?西方往往訴諸宗教。但卡繆並不相信外在救贖。當一個小男孩在李厄醫師眼前斷氣後,他痛心的對身旁的神父吐出:「我到死都不會去愛一個讓孩子受折磨的宇宙現象。」是的,李厄早就表白不信上帝,因為「如果他相信有個全能的上帝,就不會再為人治療,而會把這項工作留給上帝去做。」
對李厄醫師而言,即使上帝存在,祂也始終沉默不語,所以人類只能盡己之力對抗死亡。事實上,因為人終究一死,所以李厄的醫療工作其實是「一場永無止境的失敗」。這看似荒謬的本質,就如同卡繆在《薛西弗斯的神話》中所傳達的,盡自己的本分,「想盡辦法抗爭下去,絕不能認命投降。」

對抗這場瘟疫已經不僅是個人之事,而是群體共同的責任。封城將奧蘭市民綁在一起,「再也沒有個人的命運,而只有集體的經歷,也就是大家共同遭遇的瘟疫與共有的情感。」因此雖然李厄並不認同神父的信仰,但仍邀請神父加入衛生小組,因為他相信「我們能攜手合作,是因為有個超越褻瀆與祈禱的東西將我們結合在一起。」
群體的歸屬感不僅限於世居奧蘭的市民,藍柏這位外地來到奧蘭採訪而受困於此的記者,幾經波折才終於找到門路,可以偷溜出城外與女友團聚,但他卻在臨行前決定留下來,加入衛生小組投入救護工作。
藍柏的抉擇一方面是受到李厄醫師等人的感召,另一方面則是由於這幾個月下來,他已經與這個城市休戚與共,所以最後才會堅定地說出:「我知道我是屬於這裡的。」也因為對抗瘟疫是眾人之事,所以李厄醫師始終不認為自己或衛生小組是英雄。就像他與小組成員的這段對話:
「這一切無關乎英雄主義,而是一種正直。說出來可能讓人發笑,但我覺得對抗瘟疫的唯一方法就是正直。」
「什麼叫正直?」
「我不知道一般人怎麼看,但對我來說,就是盡我的本分。」
是的,每個人懷著小小的善心盡其本分,就是英雄。
如今,COVID-19 讓世界各國成了一座座孤島,但與奧蘭不同的是,每座孤島並不是孤立無援,全球已是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當每個人盡其本分阻止瘟疫蔓延,不只是在保衛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園,同時也可以幫助其它地區的人民度過疫情。

當最後鼠疫終於消失,群眾歡慶封城解除時,李厄醫師心中仍升起警惕:「或許有那麼一天,為了帶給人類苦難與教訓,瘟疫會再次喚起老鼠,把牠們送到一座幸福快樂的城市去赴死。」我們幾乎可以確定這是必然發生的預言──這波疫情過後,未來仍會有新的病毒侵襲人類。
但願人類能記取教訓,如《鼠疫》書末所說的,明白「應該做些什麼,或許以後還得再做些什麼,以便對抗始終全副武裝的恐懼。」
- 註:本文所引用《鼠疫》中的字句,均出自麥田出版社出版,顏湘如翻譯的《鼠疫》。
本文由故事與泛科學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