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艾德華.布爾摩 (Edward Bullmore);譯者/高子梅
- 編按:本書不同於傳統生理、心理二元論觀點,而從免疫學的角度切入、結合神經科學,重新思考憂鬱症與身體發炎的關聯。文中的 P 太太為類風濕性關節炎患者,也被作者診斷有憂鬱症的症狀。
我曾經簡單地以為,心智在發炎可能類似身體的發炎。從羅馬時期以來,我們就知道身體發炎時會紅腫。所以,我以前把發炎的心智想像成腫脹、憤怒、滿溢、激切、不受控制、潛藏著危險。用精神醫學的用語來說,大概就是躁症。
不過我現在的想像完全相反:那不會是一個易怒和極具威脅的傢伙,而是一個陰鬱和沉悶的人。像 P 太太,她雙手因發炎的關節而腫脹變形,心裡暗自納悶自己的情緒怎麼這麼低落,精神不濟。現在,她在我眼中就是典型的心智在發炎,不是比喻,而是運作上就是如此。

發炎常出現在憂鬱之前?
把「心智在發炎」從隱喻轉化為實際狀況,首先我們要有十足的證據顯示發炎和憂鬱症的強烈關聯。承認兩者之間有關就是好的開始(這種關聯有時候就在眼前,卻被視而不見)。不過關鍵問題是因果。
一個後二元論的全新思維要能穩固扎根,就需要從科學上證明發炎不只跟憂鬱症有關,而是會直接造成憂鬱症。看看各事件發生時間的先後,可以幫助我們理出因果關係,前因一定先於後果。如果發炎是憂鬱症狀的前因,那麼我們希望有證據顯示發炎出現在憂鬱症之前。最近有研究提出了這方面的證據。
舉個例子,2014 年,一項研究發現,布里斯托(Bristol)和英格蘭西南部 15000 名孩童中,九歲時沒有憂鬱症但有輕微發炎的孩童,在十年後滿 18 歲時極有可能罹患憂鬱症。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目前已有數十項人類研究和數百項動物研究顯示,發炎出現在憂鬱症或憂鬱行為之前。
想確認發炎與憂鬱的關係,有先後順序還不夠。
但光是順序的先後,並不足以讓大家正視發炎是憂鬱症的前因。科學家和醫師會質疑發炎是如何引發憂鬱症的:究竟是什麼樣的生物機轉,一步一步從血液的細胞激素,到大腦出現變化,進而引發憂鬱的心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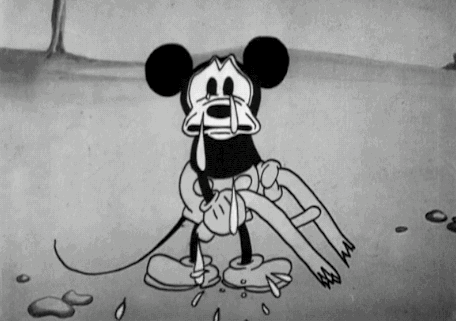
關於這些問題,最近的動物和人體實驗也提出了有力的證據。實驗結果顯示,如果一隻老鼠被注射致病菌,行為上就會變得有點像是我在看過牙醫後的樣子。牠會退縮,不願與其它動物互動,活動力降低,睡眠和進食周期受到干擾。簡而言之,在動物身上,感染確實會引發一種被稱為疾病行為(sickness behaviour)的症候群,有點類似人類的憂鬱症。
事實上,要觀察到這種疾病行為,你甚至不必先讓老鼠遭受感染,只要在牠身上注射細胞激素就可以,這也證明了並非是細菌本身造成疾病行為,而是對感染的免疫反應造成的。發炎會在動物身上直接引發類似憂鬱症的行為,這一點無庸置疑。
此外,我們現在也很清楚發炎會如何影響老鼠的大腦。我們知道神經細胞若是暴露在細胞激素下,死亡機率會升高,而且不太會再生。我們也知道神經細胞若是發炎,它們之間的連結(稱為突觸[synapses])在資訊學習上就會比較無力。而且發炎會降低血清素的供給,而血清素是神經細胞之間的傳導物質。
所以至少從動物實驗中,我們可以直接連結發炎與大腦神經細胞運作方式的改變,來解釋看似憂鬱症的疾病行為。
發炎的生理機制真的會讓人產生憂鬱嗎?

但要在人體內複製類似的連結,就不太容易了。畢竟我們不能以實驗之名把危險的細菌注射進人體內,也不能把細胞激素(或任何其它物質)直接注射進健康人士的大腦裡,所以不可能觀察發炎會對活生生的人類神經細胞造成什麼影響。
另外,要一次觀察一個細胞很難。絕大部分的人類神經細胞(大概有一千億個)都緊密地集中在大腦裡,受到頭骨的嚴密保護,與外在世界完全隔離。要想「看到」一個活人頭殼裡的運作,唯一方法只能靠磁振造影這樣的大腦掃描技術。
最近的 fMRI 研究已經開始證明,人體發炎對大腦和心情有直接的因果關係。
舉例來說,健康的年輕人在接受傷寒疫苗的注射後,就會跟實驗室的老鼠被注射細菌後一樣,免疫系統出現反應,血液裡的細胞激素會倏地升高。這些受試者出現輕微憂鬱,他們大腦內某些區域活躍了起來,而這些區域就我們所知跟情感表現有關。
所以精神免疫學已經成熟到能以新的角度和合理的說法,來幫忙解答我為什麼看完牙醫後會變得憂鬱。我不需要搬出機器裡的鬼魂。我可以理所當然地主張,是我接受的根管手術造成細胞激素上升,穿透血腦屏障,傳遞發炎訊號,讓大腦神經細胞的情緒處理網絡起了變化,進而導致憂鬱症發作,害我老是揮之不去死亡的陰影。
發炎這種免疫反應,為何會引發憂鬱呢?
這套反二元論的說法,在每一個步驟上都有可靠的實驗證據,不過還是不夠完整。畢竟在現有的證據基礎上,仍有一些缺口和異常,雖然這種情況對任何一門發展迅速的科學領域來說都在所難免。然而,就算我們已經可以回答「如何引發」,我們還是很想問「為何引發」。

在科學上,唯一可以接受的答案就是演化。為什麼發炎會引發憂鬱症?只能說這是物競天擇的結果。一定是因為唯有對感染或任何發炎出現憂鬱反應,才有利於我們的生存(或者至少在以前是有利於我們的生存)。我們一定是繼承了這種自好幾代以前就物競天擇下來的基因,能讓我們在發炎的當下因憂鬱反應而受惠。
以我來說,我可以合理推測,我遺傳了曾經幫助先人熬過感染的基因,所以在看過牙醫後,短暫地感到憂鬱。這樣的基因遺傳很可能有助我從根管治療的輕微創傷復原,一方面積極地殺死任何致病菌,另一方面指揮我待在床上,保留體力。
當然,不管是神經免疫學還是精神免疫學這類 A 加 B 式的新領域,重點並不是要找到我不喜歡看牙醫的理由,而是說,一旦我們可以繪出一條從身體經由免疫系統通到大腦和心理的路徑,一旦我們以後二元論的概念來闡明發炎的心智,就能找到全新的方法來對付精神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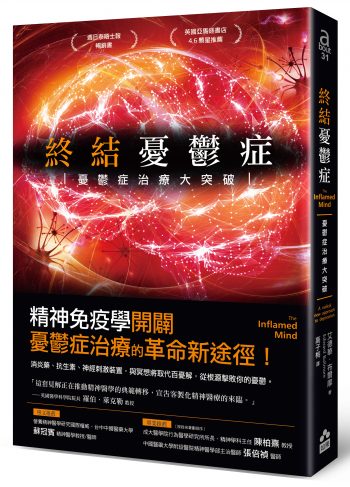
——本書摘自《終結憂鬱症:憂鬱症治療大突破》,2020 年 2 月,如果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