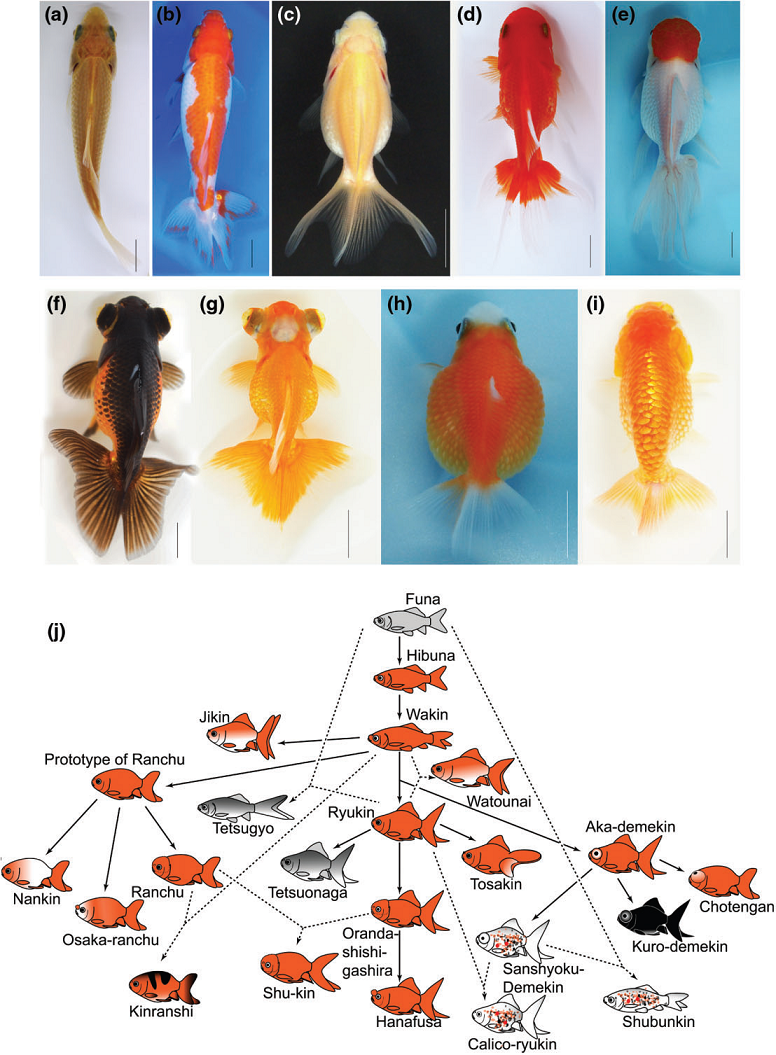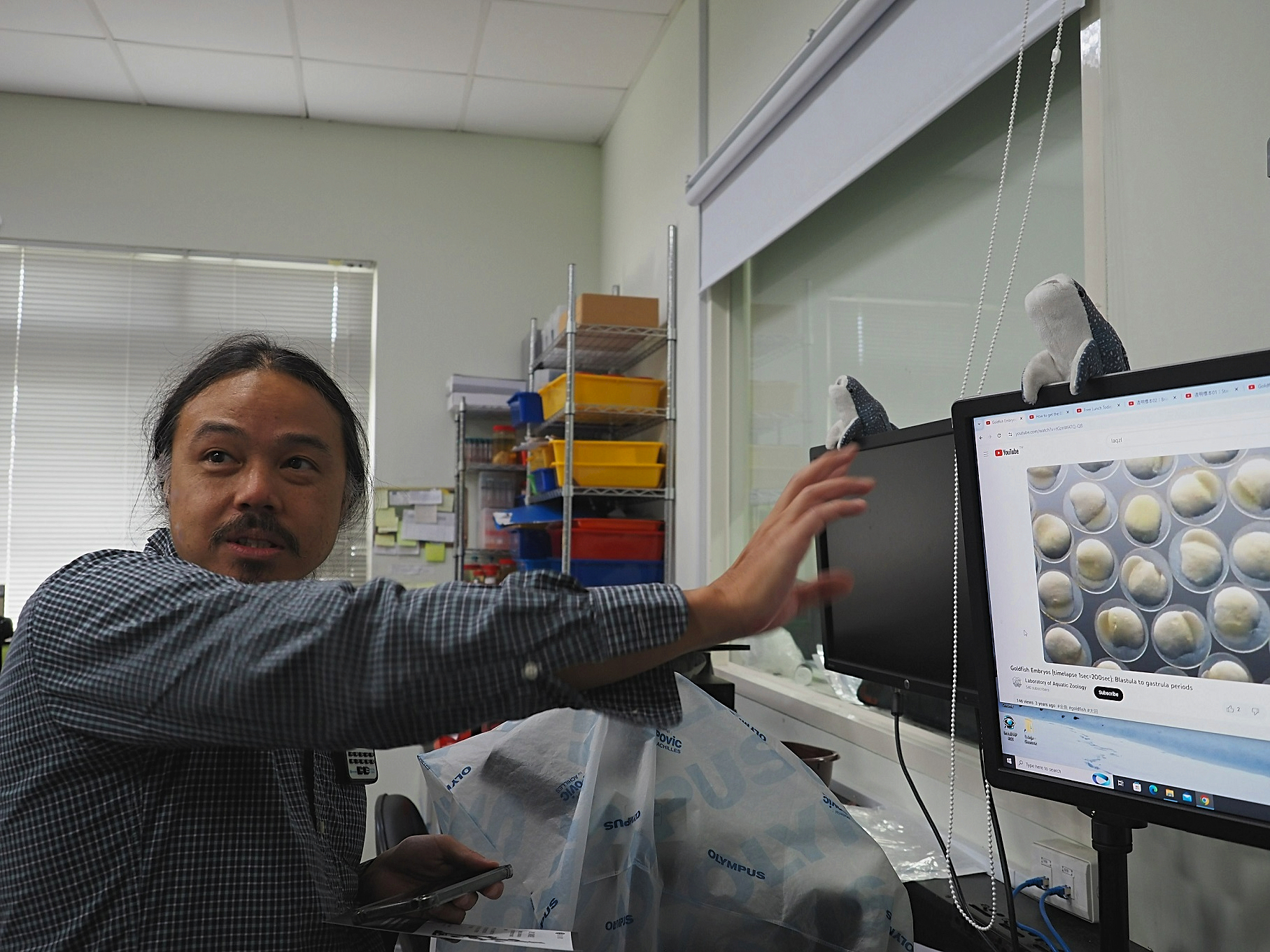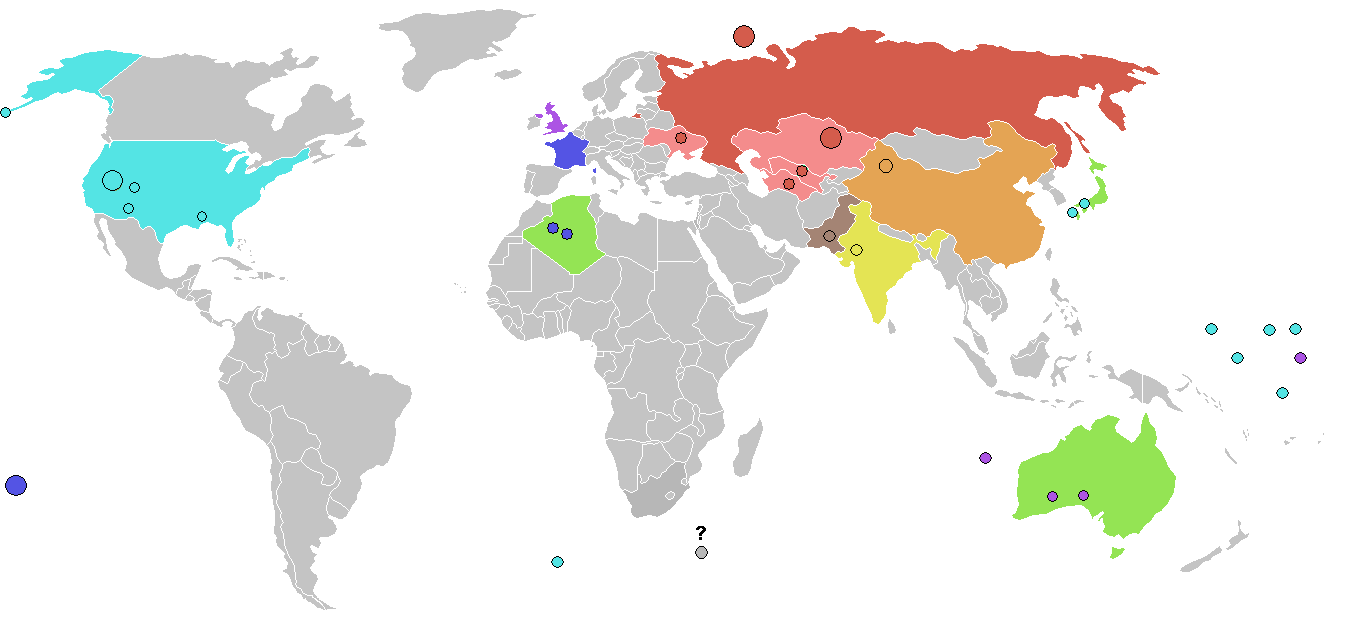文/洪廣冀 (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助理教授)
編按:科技與社會研究學者、任職於巴黎政治學院(Sciences Po Paris)的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教授,於2017/5/17在中央研究院以「新氣候體制:科學、政治與否認」(The New Climatic Regime: Science, Politics and Denial)為題發表演說。本篇為台大地理環境資源系洪廣冀老師於演講過後所寫之心得與見解。

現在是二點四十二分。約莫十二小時前,我被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在中研院的演講深深地震攝了。回想起來,那種「震攝性」並非來自某種被「法喜」穿越全身的滿足感——而是,即便我真的不是很能習慣拉圖的口音,我還是可以感覺到拉圖演說中的幾處大洞:到底拉圖在演講中提及的幾個概念(如人類世、地緣政治、氣候變遷、生態系統中的物質循環)有那些是新的呢?到底這些概念跟川普的崛起與英國的脫歐有什麼關聯呢?到底什麼是拉圖在演講中一再提及的「否定」?
當我盯著拉圖緩慢地總結自然科學家就全球環境變遷的研究發現時,我很難不聯想起之前與環境社會學者 Steven Yearley 的聊天。那時,我問及 Yearley 在 1992 年與哈利.柯林斯(Harry Collins)出版《認識論的膽小鬼》(Epistemological Chicken;發表在安德魯.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主編的 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後,這幾年來他對拉圖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簡稱ANT)的態度是否有所轉變。沉吟了半晌,Yearley 告訴我,他之前曾針對拉圖的另本名作《自然的政治》(Politics of Nature)撰寫書評。「我還是認為」,Yearley 說,「拉圖談論非人行動者的方式高度仰賴自然科學家的見解,這樣的立場讓他的分析如果不是實證主義式的,就是直覺式的。」我認為這樣的評語頗適合用來形容拉圖於中研院的演講。
即便我不是很欣賞拉圖把台下聽眾當成小朋友的姿態(雖說他很和藹地替學生簽書,也祝我的研究生「生日快樂」,讓我十分歡喜),我還是不相信拉圖晚近就人類世、全球氣候變遷的思考真的如此空洞。我不免會問自己,之所以會覺得拉圖的演說空洞,是不是因為我對拉圖的認識還是侷限在《我們從未現代過》、《科學在行動》、《巴斯德的實驗室》(對此我必須辯解,我畢竟是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大本營訓練出來的—在取得博士學位之前,我對拉圖與行動者網絡理論實在少得可憐,也從來不覺得這樣的「少」意味著某種學術訓練上的缺陷。我還記得好友對於行動者網絡理論的批評:「拉圖總把世界想成平的」。幾年前的我覺得實在不能同意再多了,現在的我倒挺想翻白眼的—阿不然咧?)

另外,儘管拉圖的演講是「對公眾開放」,該演講之所以得以「對公眾開放」,仰賴的還是公眾的納稅錢。如果說拉圖的中研院演講其實是要「付費」的,那麼,我下定決心,我一定要從中得到一些東西。於是我開始睡不著了。既然拉圖習慣把他所有的著作都放上網,而且(正如絕大多數的學術工作者一般),每場新演講往往是來自既有演講與研究成果的重新組裝,只要花點工夫,我們不難自行把拉圖演講中的大洞補起來-而不用癡癡地等待他即將於今年七月出版的新書:《面對蓋亞:就新氣候體制的八場演講》(Facing Gaia: Eight Lectures on the New Climatic Regime)。
關鍵區:在生物圈之外殼上的一個點
我想補的一個大洞是「關鍵區」(critical zone)的概念。只要稍微地檢索,不難發現這概念出現在拉圖於 2014 年的《「關鍵區」此概念於地緣政治上的幾處優勢》(some advantages of the notion of “critical zone” for geopolitics)一文,發表在 Procedia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上。如同「人類世」(anthropocene)概念一般,拉圖認為,「關鍵區」此概念意味著當前研究者在處理「地球之生命維繫系統」時的一處「有趣轉折」,乃至於一種思考「geography」、「geophysics」以及「geopolitics」中的「geo」 到底是什麼意思(在拉圖的中研院演講中,他是以「地質學」-關於「大地之品質」的學問開場)。但在此之前,拉圖要我們重新思考什麼叫做「politics」。拉圖建議我們將 「politics」重新理解為「共同世界的進步組合」(progressive composition of the common world)。
之所以如此地定義政治,拉圖認為理由包括下列數點:首先,這樣的定義意味著沒有什麼「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或「我們的『共同』未來」之類的—因為關於這個世界的「共同性」其實是組合出來的(這不難理解,不論是自然科學家還是人文社會科學家還在試著透過各類經驗研究來拼湊出世界的全貌,更不用說「我們共同的未來」往往隱含或明示著一種各類差異完全弭平的想像)。第二,這樣對「politics」的重新定義之所以是「進步」的,理由在於它揭示了一類「前進」的方向,也意味著他是可以開放地—也容許曠日費時地—討論。第三點則牽涉到行動者網絡理論的精髓。當我們把世界的「共同性」視為「politics」運作的結果,拉圖告訴我們,我們就不會把「politics」這檔事視為「眾人的事」,而可以設身處地地思考人與非人間的 「politics」是怎樣一回事。

緊接著拉圖提出他對「關鍵區」定義:「在生物圈之外殼上的一個點」(a spot on the envelope of the biosphere),而這個「點」可以小至一處花園,大至亞馬遜盆地。拉圖主張,如果說「人類世」這樣的概念強迫我們去思考人類的行為如何改變了地球整體的生態體系,乃至於該如何作為以追求地球上的種種人與非人的未來,關鍵區會是比較適合的研究單位,讓我們可以經驗地思考與作為。如「星球般地思考」顯然是強人所難,且這樣的思考尺度如不是預設了有種大寫的、無內在差異的「人」(Human)是如何改變大寫的、無內在差異的「自然」(Nature),便是預設了自然與社會都是種「系統」。面對全球氣候變遷帶來的挑戰,拉圖強調,我們必須選擇一個在目前科研能力能掌握的時空尺度,進而從事詳實的跨領域研究,從而透過人與非人是透過何種機制形成巨大網絡,而非一味強調「人類」在改變「自然」上的角色,或社會與自然系統是如何互動與自我調控而已。

最後,拉圖解釋他為什麼以「區」(zone)一詞來畫出人類世下(或全球環境變遷)的處境下我們賴以思考與行動的單位。拉圖指出,相較於其他的空間單位,如土地、領域等,「區」這個字比較不容易帶出如下古早的地理學想像:即我們可以關心與賴以行動的空間單位是個邊界清楚、可在二維的地圖上清楚標出位置與邊界的點。這就涉及到拉圖長久以來對傳統地理學的批判。例如,在 1996 年的一篇題為《On Actor-network Theory: A Few Clarifications Plus More Than a Few Complications》的文章中,拉圖寫道,就行動者網絡理論而言,任何透過地理學來定義的「距離」(distance)或「鄰近」(proximity)均是「無用的」(useless)。
事實上,拉圖指出,在以網絡來定義何謂 ANT 所稱的連結時,研究者面對的困難為「地理學的盛行」與「暴政」。事實上,早在其著名的《Give me a laboratory and I will move the world》一文中,拉圖便以巴斯德的實驗室為例,說明行動者網絡是一種無內外、無尺度的拓樸學構造。順著這樣的思路,我認為,拉圖提出「關鍵區」的目的是在澄清「全球挑戰、在地行動」這樣的行動綱領。所謂的「在地行動」,就拉圖而言,完全不意味著我們得在社區、部落、村里等單位中行動,也不代表我們必須「心懷全球」地以具體行動來處理種種與地方生活息息相關的議題。正如拉圖在《我們從未現代過》以及《Politics of Nature》等書中均有提及的,他關心的,還是如何建立一種「物的議會」(Parliament of things),除了讓「人」可在其中暢所欲言,如土壤、大氣、蟲魚鳥獸等「非人」也可有發言權與投票權。
當然拉圖在這裡不是提倡什麼萬物有靈論,他的見解也不能以生態中心論來簡單涵蓋。他還是期待,生物學家、大氣學家、土壤學家、鳥類學家、森林學家等以「非人」為研究對象的科學家們,能確實地為其關注的「非人」代言。一旦如此,拉圖期待,面對全球挑戰,不是人在某個有範圍或邊界的「在地」中行動—相反的,是這個「在地」本身,這個糾纏著種種人與非人元素的網絡本身,就是個足以行動的行動者。
現在是下午六點整。離拉圖的中研院演講已經過了一天。大僧遶境,小僧解經。我現在的心裡充滿了平安喜樂,也期待各位可以一起放下我執。大僧之所以為大僧,還是有其理由。
- 本文轉載自 Kuang-chi Hung,《Latour 到底說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