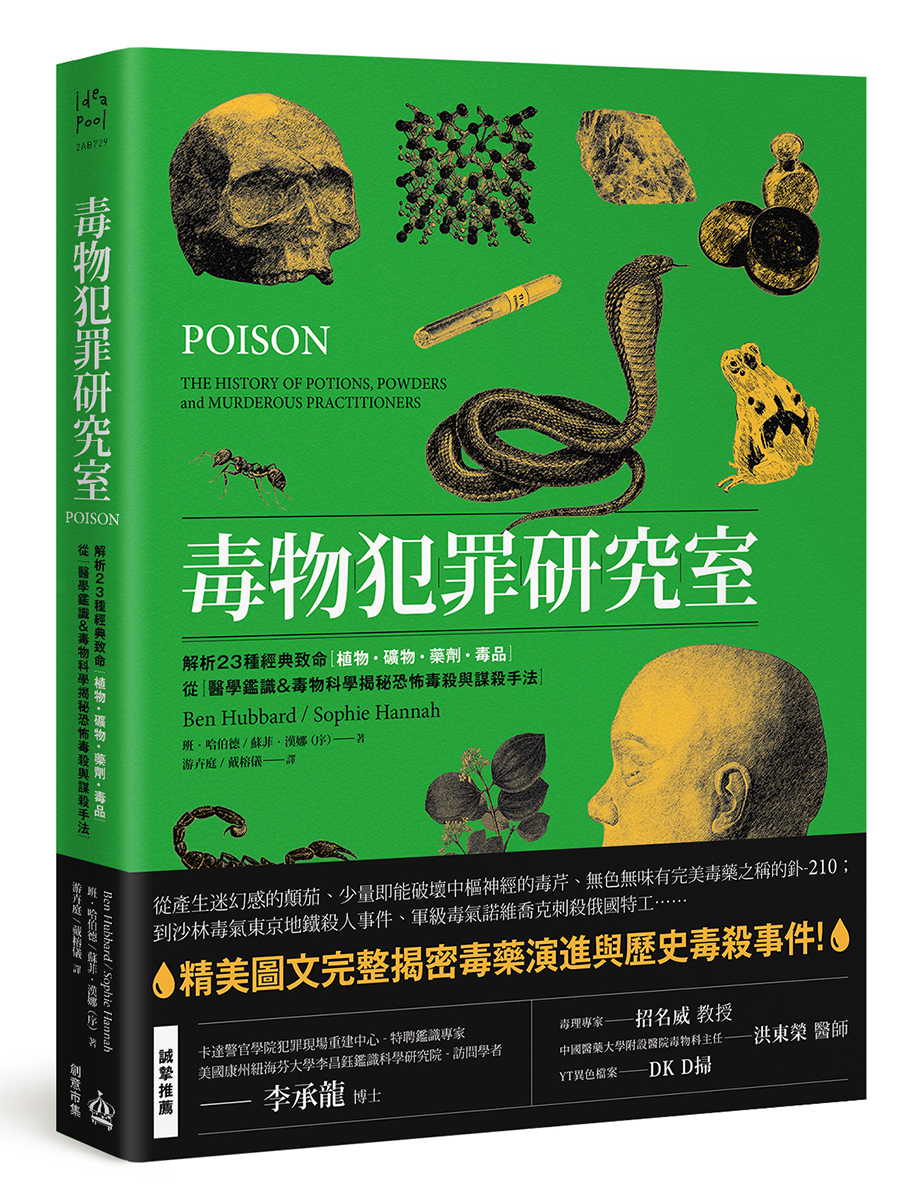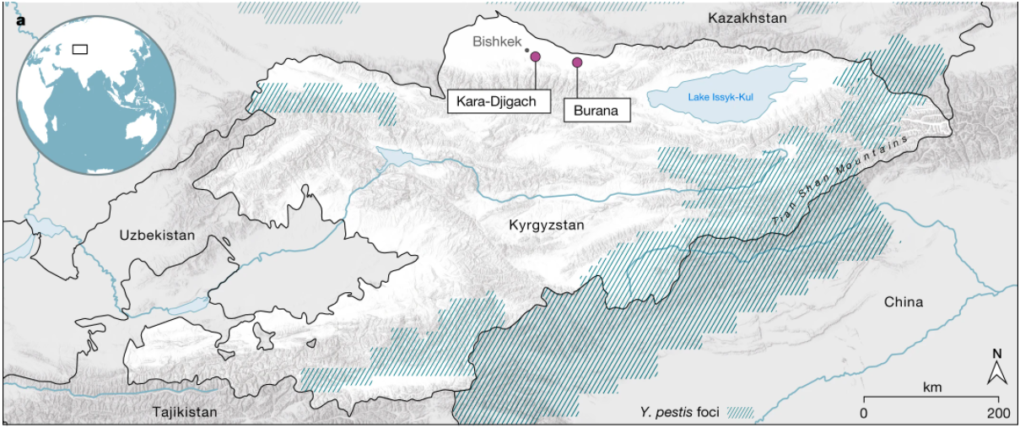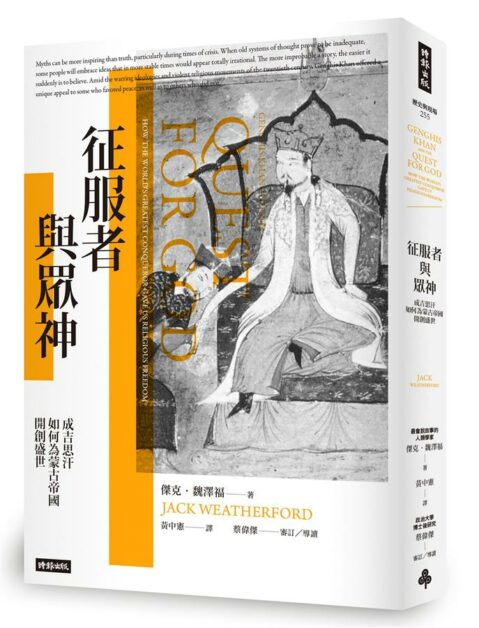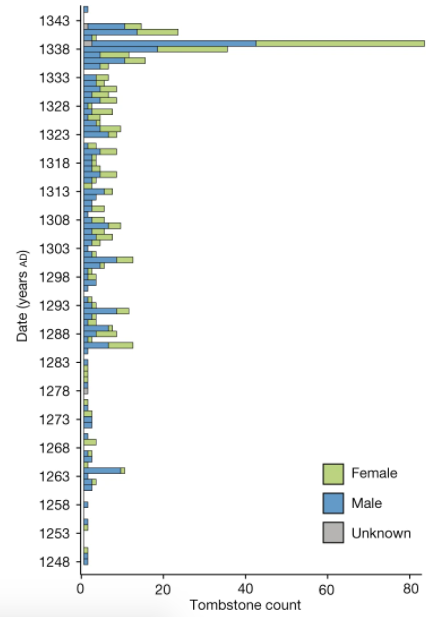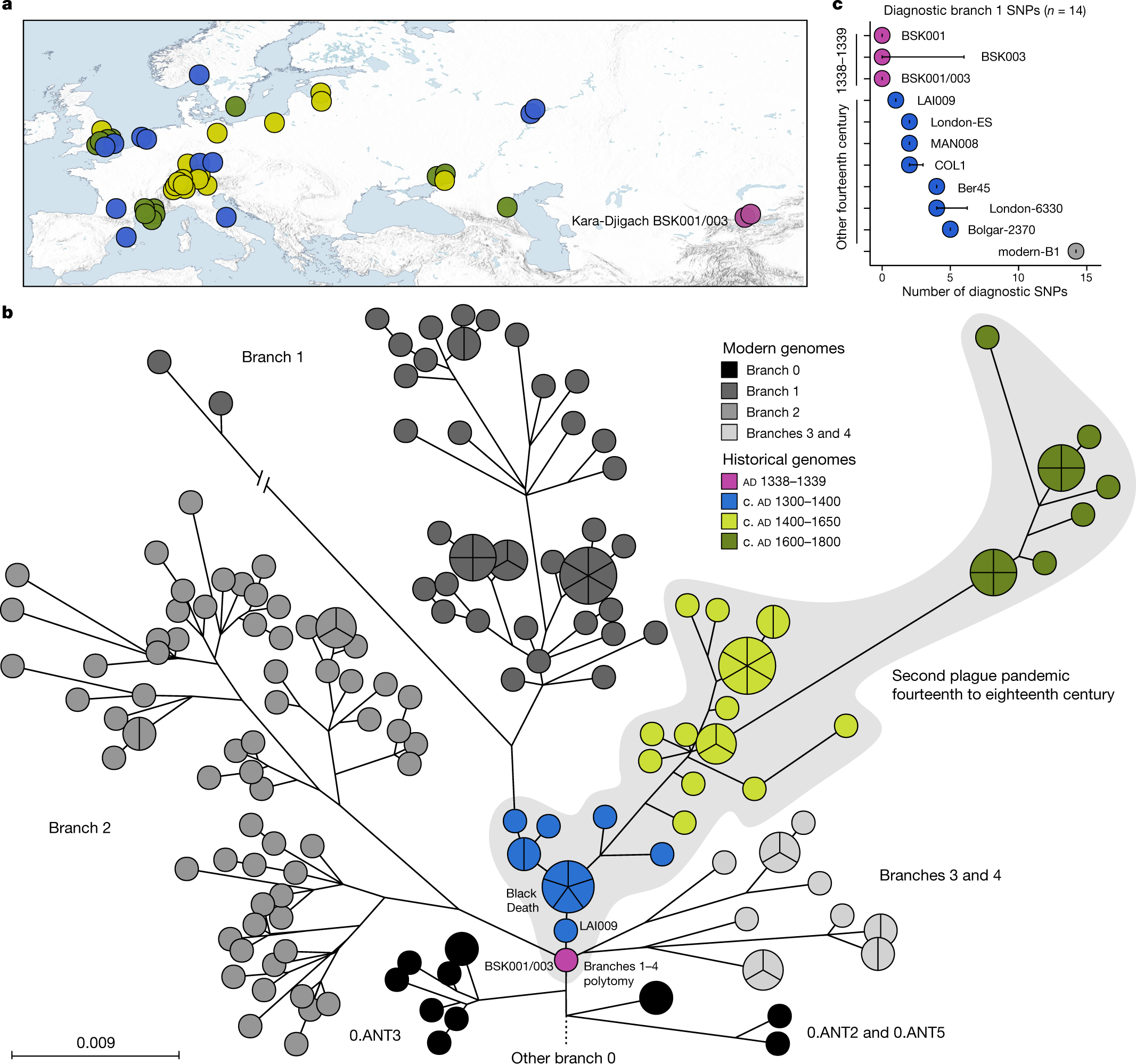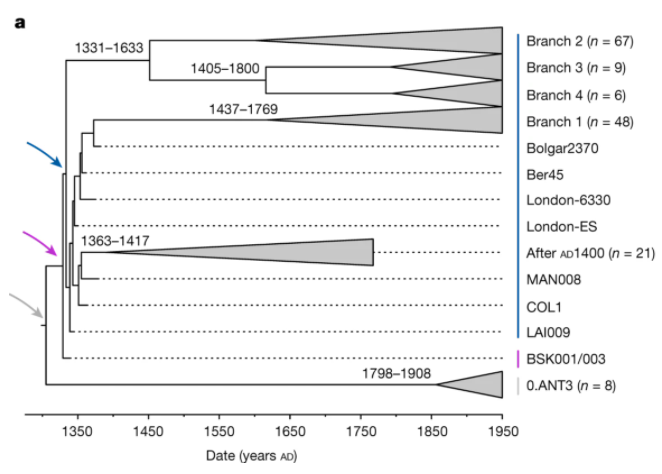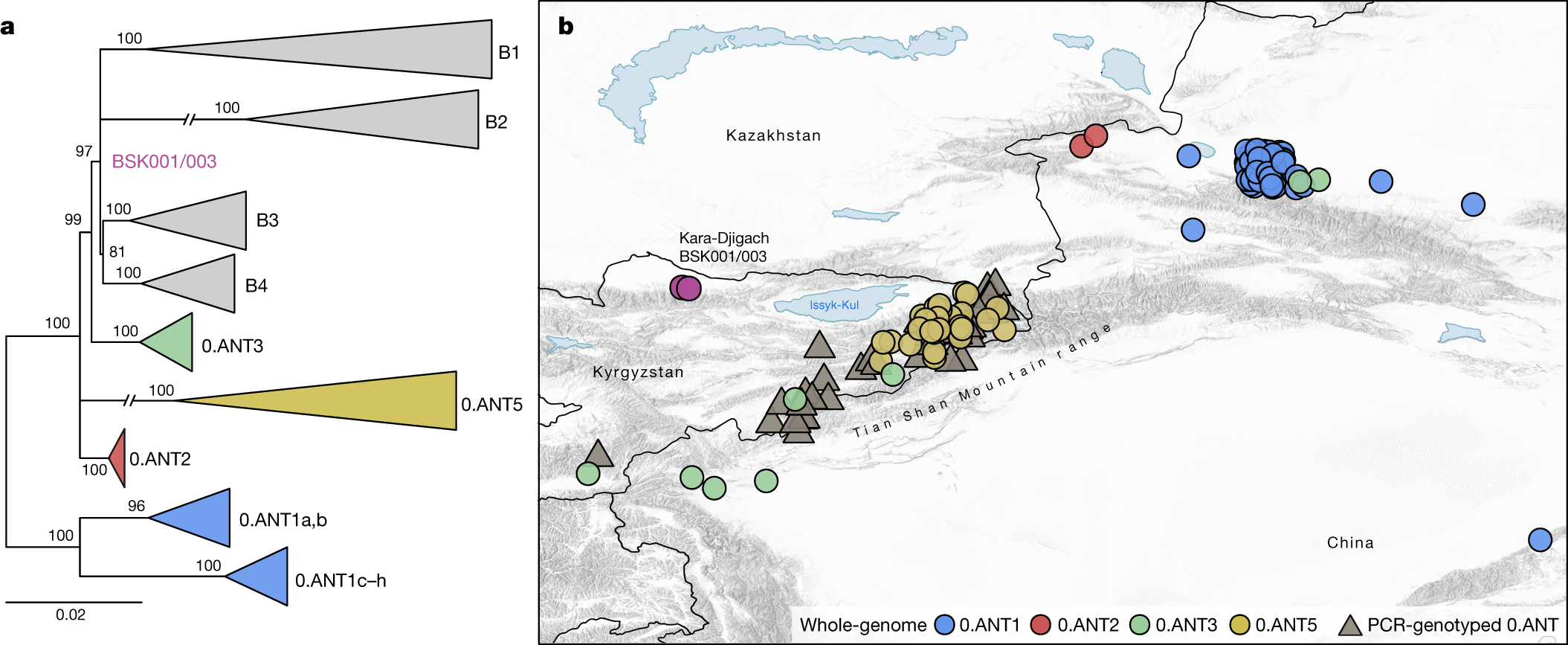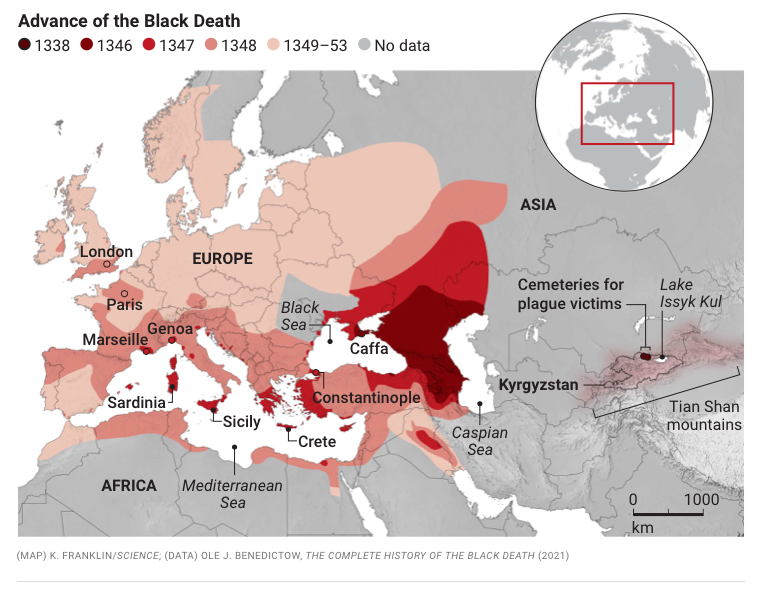- 導讀 / 翁振盛(中央大學法文系助理教授)
- 書籍作者 / 阿爾貝.卡繆 (Albert Camus);譯者 / 陳素麗
不只是瘟疫
卡繆的《瘟疫》(La Peste)出版於一九四七年,二次大戰結束後不久。為了創作《瘟疫》,卡繆的準備工作絲毫不馬虎。他努力鑽研歷史上、醫學上的各類文獻。《瘟疫》的寫作過程頗為漫長。早在一九四一年,他就曾提到要書寫一部瘟疫的小說。
《瘟疫》可能是卡繆除了《異鄉人》之外大家最熟知的作品。小說甫出版即廣受讀者歡迎,並且獲得「批評獎」(Prix des Critiques)。
《瘟疫》和卡繆的其他作品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小說中觸及的諸多主題(生命、死亡、愛情、幸福)延續卡繆的《反與正》(L’Envers et l’endroit)。《瘟疫》一書中透過一個雜貨店老闆娘談到一則發生在阿爾及爾的社會新聞,明顯指涉先前問世的《異鄉人》。
《瘟疫》是卡繆「反抗系列」(Cycle de la révolte)中的一部作品。小說中以李爾醫生為首的幾個人物竭盡一切反抗瘟疫,拒絕不戰而降。和《異鄉人》不同的是,《瘟疫》的文本生成無法與其歷史情境切割開來。《瘟疫》中有許多片段和卡繆在二次大戰期間在地下抗暴刊物《戰鬥報》(Combat)發表的文章以及《致一位德國友人的信》(Lettres à un ami allemand)極為相似。有別於卡繆早期的著作,《瘟疫》讓卡繆真正進入了歷史,讓他從個人邁向群體。
在新冠肺炎肆虐全球的今日,這部「應景」的作品不僅在法國,在世界各地,都重新燃起讀者的興趣,銷售量也扶搖直上。小說中刻畫疾病的變異、防堵的措施、隔離檢疫、防疫宣導、疫苗注射,一切與現今何其相似。
書寫災難
小說名稱明白預告了即將發生的事件:名為《瘟疫》,也真的會爆發瘟疫。書中多次提到歷史上的大瘟疫以及宗教典籍上出現的瘟疫。西洋文學史上與瘟疫或大型傳染病相關的作品並不罕見。比較遠的有薄伽丘《十日談》、笛福《大疫年記事》;比較近的像是湯瑪斯.曼《威尼斯之死》,吉歐諾《屋頂上的騎兵》。瘟疫或為故事的核心議題,或作為故事背景框架,或變成推動故事的主要驅力,或左右故事的關鍵元素。
如果卡繆習慣透過虛構的作品來宣揚其理念或道德觀的話,他鮮少會因此而犧牲故事,《瘟疫》也不例外。不論故事的架構、演進、時間安排、空間描繪、敘述和對話的調配還是人物的營造,在在皆可看出這是部成熟作家的成熟作品。
李爾醫生為貫穿整部小說的靈魂人物。醫生之所以雀屏中選,主要因為他的專業讓他可以對疾病作出適切的觀察和處置,並且讓他接觸到許多歐蘭城的居民,知曉許多內情,獲取的訊息也成為故事推進的主要動力。
紀事和/或敘事
《瘟疫》有別於典型的傳統小說,遊走在紀事和敘事之間。紀事與敘事存在著矛盾,因為紀事依照事實的時間先後依序羅列出發生的事件,而敘事則建立在邏輯因果關係上。也因此,通常會打亂時間次序,重新安排組織。
這部小說採取常見的事後追述的方式,也就是說,敘述的事件在敘述之時已經發生。小說從頭到尾,時間指示十分清楚。事件大致依循時間次序敘述,但是免不了出現回溯的情形,比如在門房過世後敘述者提到尚.塔胡的雜事本,談到他初到歐蘭城的時候。
小說中的紀事者眼觀四面,耳聽八方,逐日逐月詳實記錄下他的所見所聞。他可以證實、擔保發生過的事情。紀事者偶爾洩漏他的形影。不時出現的「我們的市民們」證明他很可能亦是其中的一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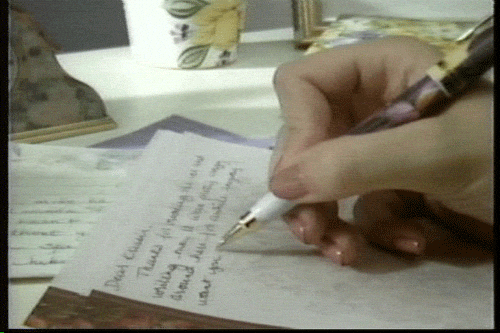
此一紀事者亦是敘述者。當他說明其敘事策略、走向或選擇時,也會讓讀者意識到他的存在(例如,「在詳述新時期的種種事件之前,敘述者認為提供另一位證人對於上述時期的觀點,該會有所助益」)。
特別的是,敘述者使用第三人稱(「他」)來指稱自己,就像一個全知全能的敘述者。他巨細靡遺地敘述某些人物的日常生活(比如藍伯),就好像他一直待在他的身旁。但有些地方他似乎又暗示他並不是全知全能的敘事者,比如,「敘述者深信他可以代表所有人來寫下他的感受,因為他跟所有市民共同經歷了這段時期」。整部小說不斷擺盪在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之間。一直要到故事最後敘述者才會披露自己的身分。
除了敘事視角的混淆,口語化的語言是小說的另一特色。人物說話直白,大半時候只說該說的話,彷彿目的只在於傳達字面的意思。敘述的部分也類似。大致都是訴諸再尋常不過的語彙,甚至就像日常談話一樣,不假思索就脫口而出。話語除了字面的意思外,常常還蘊含有意無意抑制的情感。表面的平和掩蓋不住內在的溫熱,就像小說起始李爾醫生和妻子車站道別的那一幕。或許因為詞語大都安然置放在應該放置的地方,因而,即便醜陋可怖的畫面也往往會發散出奇異的魅惑。第一章中不少場景刻畫垂死掙扎、奄奄一息的老鼠,生動而鮮明。
封鎖的城市,囚禁的人
小說一開始的題詞預示了歐蘭城居民未來的命運和處境。他們面臨的不只是實質的禁錮,更是心靈的禁錮。封鎖的城市隔離了人們。裡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進不來。
卡繆筆下的歐蘭城,骯髒沉悶卻同時又迷人。卡繆對於這個城市並不陌生。一九四0年初,他人就在歐蘭城。此時他的肺結核又復發。卡繆在歐蘭城一直待到一九四二年八月。小說起始,時間的故意模糊(「這篇紀事報導中的詭異事件是發生在一九四幾年間的歐蘭城」)並沒有降低或移轉自傳的色彩,反倒使其顯得欲蓋彌彰。
李爾醫生因為封城無法與他的妻子相見,藍伯也被迫和愛人分開。分離和放逐的苦痛,卡繆本身也經歷過。二次大戰期間,卡繆離開歐蘭城到法國治療,由於政治局勢的丕變,有兩年多的時間他被迫與待在北非的妻子和親人分隔兩地。
卡繆在年輕時曾罹犯肺結核,長期治療和休養。書中對病人(例如門房)發病症狀、病況的變化、瀕死的身體的描述十分貼切。Jacqueline Lévi-Valensi 亦指出,肺結核和某一類型的瘟疫症狀極其相似。
《瘟疫》聚焦於瘟疫底下生活的歐蘭城居民。歐蘭人的態度大相逕庭,每個人以自身的方式回應這場瘟疫。紀事者或敘述者統籌這一切,消化、轉述他從居民接收到的訊息,並發表評論。
災難和極端的情境改變了人們,讓他們正視自己的情感,就像老醫生卡斯特和他的妻子。景物的描繪適時反映了人物心境的變化。李爾醫生不停移動,隨時隨地觀察周遭的景物(「醫生依然看著窗外,窗戶外是一片春天清澈的天空」)。景物的描繪突顯了瘟疫爆發前後的對比,例如,「這一帶的人平時都在門口坐上一整天,而現在各個大門深鎖,百葉窗拉下」。不僅如此,景色和物件還不時被賦予象徵的意涵。例如,在疫情趨緩的一月,天空終於浮現「前所未見的湛藍」。
不只是瘟疫
卡繆宛如時代的眼睛,對世上任何不公不義都無法視而不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前到戰後,卡繆可以說是無役不興,尤其在大戰期間積極投入抗暴運動。
納粹黨被稱為「褐色的瘟疫」(Peste brune) 。卡繆明白揭示:《瘟疫》遙指二次大戰德軍佔領下的法國。小說中有多處類比瘟疫和戰爭:「世界上的瘟疫跟戰爭一樣多」;「疫情已全線撤退[……]最後終於讓眾人確信勝利業已在握,瘟疫正在棄守陣地」。小說第五部,瘟疫終結,禁令解除,眾人歡欣鼓舞,湧上街頭,不正像是大戰結束,熱烈慶祝解放的法國?依循卡繆的解讀,瘟疫暫時跳離了歐蘭城,沾染了濃郁的政治色彩。事實上,小說中有不少細節都可以和大戰產生連結。閱兵廣場蒙塵的共和女神像似乎暗指被德軍佔領的法國。屍體草率的集體掩埋,焚屍爐火化的場景更讓人聯想到納粹的集中營。
如果戰爭也是一種瘟疫,恐怖主義、新集權主義等風潮亦可視為瘟疫的變種或變異。一如瘟疫,政治的狂熱激情也會相互感染,在短瞬的時間之內蔓延開來,一發不可收拾。面對這些新舊型態的瘟疫,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卡繆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致謝詞清楚闡明他的藝術理念以及對作家的定位。他認為作家的角色「離不開艱困的責任」。藝術家不能孤芳自賞。他必須認知到他與沉默的芸芸眾生是相似的,並且願意為他們發聲。真正的藝術家勇於面對社會的問題,擔負起時代賦予的責任。
卡繆一生熱愛的工作都是一些「團體」的活動。踢足球,參與劇場演出,投身新聞業,他在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夥伴之間相濡以沫,並肩作戰,就像小說裡的李爾醫生、尚.塔胡、格蘭……
如果承認人與人的命運休戚與共,一如瘟疫籠罩下的歐蘭人,也許承擔責任和互助團結才會是對抗瘟疫的終極藥方。今日,距離《瘟疫》問世已有七十餘年,卡繆的思想隨著時間開枝散葉,深入人心,過往的實踐和經驗已經一次又一次證明其效力與價值。




























裡出現的布拉德福德糖果中毒案。在維多利亞時期的英格蘭,食物摻假貨是一大問題。.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