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科愛看書之本月選書】當科學家面對納粹統治,應該共謀還是抵抗?在《為第三帝國服務:希特勒與科學家的拉鋸戰》中以三位諾貝爾獎得主:彼得.德拜、馬克斯.普朗克和華納.海森堡為主角,敘述他們在納粹統治時期如何面對科學、面對政治。德拜是個局外人,雖然在德國擁有傑出的職業生涯,卻堅持拒絕入籍德國。面對國家社會主義者的干擾和要求,普朗克的反應是苦惱且支吾。海森堡尋求官方的認同,卻又拒絕承認自己的妥協所帶來的後果。
普朗克在會見希特勒的描述中,有個部分我們可以毫無疑問的接受,那就是他擔憂在達勒姆的威廉皇帝物理化學和電化學研究所所長哈柏(Fritz Haber)的命運。父母都是猶太人,儘管哈柏已經受洗,偶爾也去教堂做禮拜。但是以亞利安主義的教條來看,他仍是猶太人。仇恨猶太人的人知道他們的敵人仍舊流著原本的血液。

哈柏的化學武器
哈柏對於德意志帝國一直很有用處。正如普朗克對希特勒所說的,他不僅發明由氮轉化為氨的製程,氨對於炸藥來說是重要的先質;他也策劃了生產氯氣的化學武器 。沒有人能夠指責哈柏在化學的軍事應用上缺乏貢獻。
就在氯氣於 1915 年用於伊普爾的戰場上後不久,他出發到東部戰線去監督它的使用──他出發前一天,他的第一任妻子克拉拉(也是化學家)用丈夫的軍用手槍自殺,自殺原因顯然是對於丈夫的研究方向感到羞辱和恐懼。然而,哈柏對於這個戰時工作並不後悔,在戰爭結束後仍舊在柏林的研究所繼續毒氣的研究。氰化物氣體氫氰酸 A 於 1920 年代研發出來作為殺蟲劑使用。納粹發現另外的應用,後來修改為氫氰酸 B。

哈柏在化學武器上的成果經常被視為證據,說他是沒有道德感的怪物,或者說他是科學中的異形。但是,在戰爭期間,盡可能為軍隊服務又幾乎是舉世都認同的義務。哈柏在戰爭中的工作為他贏得了同時代人的尊重,讓他成為高尚的德國人,也沒有人懷疑他的愛國精神。此外,他希望化學戰的衝擊能夠結束壕溝戰的僵局,迫使早日解決戰爭,最終得以挽救生命。
狠不下心開除猶太人同事,只能自己離開
在 1933 年,威廉皇帝研究所中有許多成員都處於公務員法的模糊地位中。因為這些研究所是由政府和工業界的合股公司提供資金,他們的大部分工作人員並不完全算是政府雇員。然而,哈柏的威廉皇帝物理化學研究所並不一樣,因為那裡是由政府直接控管。
新的法律並沒有威脅哈柏個人,因為他的交戰紀錄讓他得以豁免,但他被告知要開除他的猶太人同事。該研究所中「非亞利安人」的研究人員比例很高,大約有四分之一,這一點讓反猶太分子更有證據宣稱猶太人如何照顧自己人。負責執行解雇的帝國教育部科學局長伯恩哈德.拉斯特(Bernhard Rust)斷言,可以理解他們會這樣做。但是,他堅持,「我不能讓這種情況發生……我們必須讓大學裡產生新的亞利安人世代,否則我們將失去未來。」 拉斯特讓好的德國猶太人保證,「我對於那些心中想要把自己當成德國人一分子的人深深感到難過……但是為了未來著想,我們必須執行規則。」

哈柏被下令要解雇他的許多主要工作人員,因此認為,唯一的正直行為就是自己也辭職。他帶著極大的尊嚴下台,在四月時寫信給拉斯特:
我的傳統思想要求我,在我的科學立場,當我選擇同事時,只考量專業成就和申請人的個性,不問他們的種族。你不能指望一個 65 歲的男人改變這種引導了他 39 年大學生涯的思維方式。
納粹「站在破碎的玻璃前」,士氣低落的哈柏在 5 月告訴洛克斐勒基金會的韋佛。「他們現在了解,他們其實並不想打破它,而且他們不知道該拿碎片做什麼。」 韋佛視哈柏為「可憐卻不失高貴的人物。他在沉船時拯救了他唯一能夠救的東西,那就是他的自尊。」
哈柏紀念活動
哈柏的辭職讓普朗克悲痛欲絕,但他的回答顯示出盲目的投入不合時宜的禮節裡,如何麻痺了他。「我該怎麼辦?」當梅特納抗議不公時,他這麼問,「這是法律。」 普朗克知道解雇的合法性並不會讓他們變得正確,但在他看來,法律讓人難以反駁。
正如拜爾岑所說的,「這個人面臨著抗議法律的違法性這樣矛盾的位置,說法律違法在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可能有其道理,但在德國卻沒有。」
當普朗克要選擇哈柏的接班人時,他深刻了解威廉皇帝學會的自主性是個謊言。普朗克向拉斯特提議了哈恩,但是拉斯特卻任命格哈特.漢德爾(Gerhart Jander)這位在哥廷根大學任教的平庸化學教授,但重要的是,他是忠誠的黨員。他將協助拉斯特的副手魯道夫.曼澤爾(Rudolf Mentzel),實際上是受他指揮。曼澤爾之後穿著他的黨衛軍制服出現在威廉皇帝學會理事會的會議中。漢德爾很無能,但在 1935 年,他的位子由彼得.阿道夫.泰森(Peter Adolf Thiessen)所接替,泰森是納粹黨的「老戰士」與全能的科學家,他把研究所轉換成政權的有效工具。研究所的工作變得愈來愈集中在化學戰,而晚上的聚會和「深化同志情誼」的陣營充滿著發泡啤酒的酒杯互相碰撞的聲音。
這種情況是否表示,如果主要代表人物離職,會有什麼事降臨到所有的德國科學領域──可能由不稱職的領導者所經營,也可能成為納粹事務的附庸?這就是普朗克和海森堡害怕會發生的事。對於海森堡來說,就只是罷工離開這個國家是失職,不是道德的抗議行為。

可憐的哈柏帶著破碎的心離開德國。受到這個他所愛的國家排斥帶來的痛苦,清楚的呈現在他於 1933 年 12 月從英國寫給波希的哀怨字句中:「我從未做過任何事,從未說過任何話,會保證讓我變成現在德國執政黨的敵人。」 一個月之後,他在瑞士死於心臟疾病。威廉皇帝學會的自然科學界堅決抵制一體化可以從勞厄所寫的訃告中看出,在訃告中,他堅持宣告哈柏在德國文化中的地位:「他是我們的一員」,他如此寫道。
普朗克、勞厄和其他人決定在 1935 年 1 月 29 日,也就是哈柏的一週年忌日,在位於柏林哈納克大廈的總部舉辦一場追悼會。但是,威廉皇帝學會大多數的研究人員並未正式列入官方的禁令,而他們之中有幾個參加了追悼會,知道這件事會上報當局。這些人包括波希、梅特納、哈恩,他們的學生弗里茲.斯特拉斯曼(Fritz Strassmann)和馬克斯.德爾布呂克(Max Delbrück),以及普朗克本人。誰也不知道是否會用武力阻止聚會,但是結果有人踴躍參加,也和平度過。普朗克對他們的前同事說了幾句感謝的話:「哈柏堅守著我們,」他宣稱,「我們將繼續對他保持忠實 。」

哈柏的紀念活動有時會被標榜為德國科學家的確做出反對納粹行為的證明。但其實並非如此,不過仍舊是反對反猶太主義的象徵性抗議。對於普朗克來說,這只是適當的遵守傳統:在請求帝國教育部的拉斯特同意該次活動時,他將此捍衛成一個「古老的習俗」 ,沒有政治含義。雖然拉斯特嚴厲的回答:「哈柏對科學和德國有許多貢獻,但納粹黨做了更多」 ,他同意普朗克繼續聚會。而且一旦該部禁止任何一所大學的教授出席,他說,這將被視為挑釁行為,學者就不能參加 。連勞厄都遵守這個規定,並正確的假設納粹間諜將會出席活動。
因此,儘管政府並不情願,又可想而知會不允許發表活動紀錄,但是哈柏紀念活動實際上是國家認可的。歷史學家約瑟夫.哈柏雷爾(Joseph Haberer)稱哈柏紀念活動為「一個證明公民勇氣已經潰散的手段」 ,表達出咒罵但至少部分必要的評判。這次集會再次表明了國家社會黨可能會怎麼容忍這些科學家讓他們覺得可笑的舉動和儀式,或許他們了解,只要讓這些科學家以非政治化的方式釋放他們的不滿,這些微不足道的讓步就能夠讓更多人順從。
而且普朗克充分而明確的讓世人知道他願意妥協。他於 1936 年威廉皇帝學會 25 週年時再次談到哈柏的成就(並且因此受到斥責),但是在該活動的出版紀錄中,他卻一直不讓哈柏的名字出現。普朗克也在發給希特勒的電報中提及這個慶祝活動,感謝他「仁慈的保護德國科學」 。
普朗克後來聲稱,在國家社會黨的統治下,威廉皇帝學會認為,權宜之計就是表現得「像在風中的樹」,必要的時候彎曲,但是等壓力過去,就會再次變得挺直 。他從來沒有真正了解,納粹只關心他們彎曲的時候。
本文摘自《為第三帝國服務:希特勒與科學家的拉鋸戰》,麥田出版。本書為泛科學 2017 年 2 月選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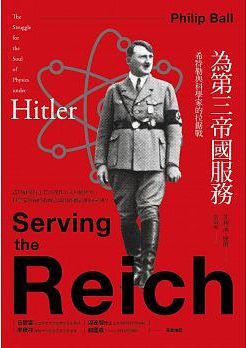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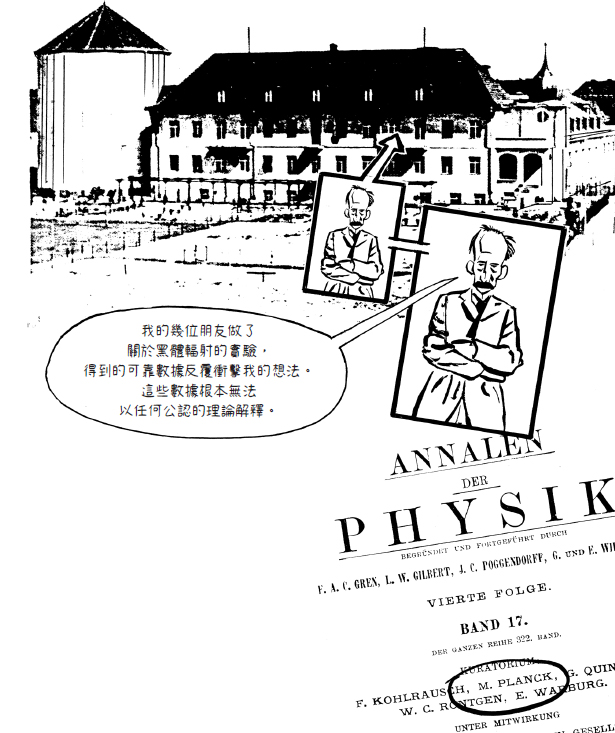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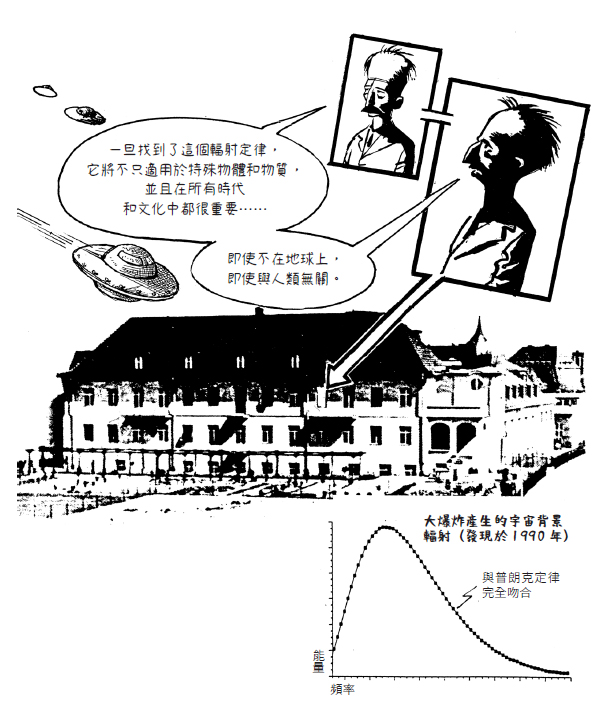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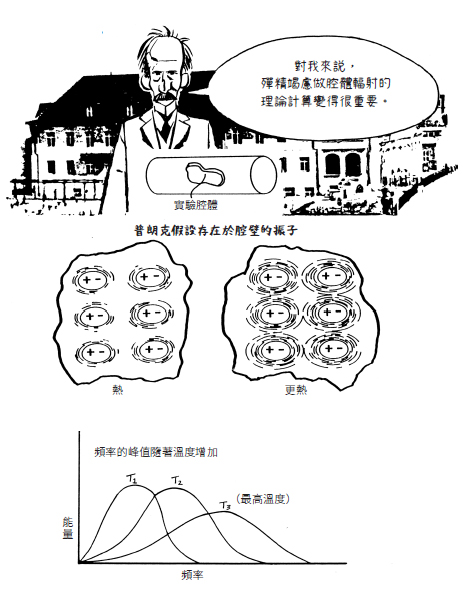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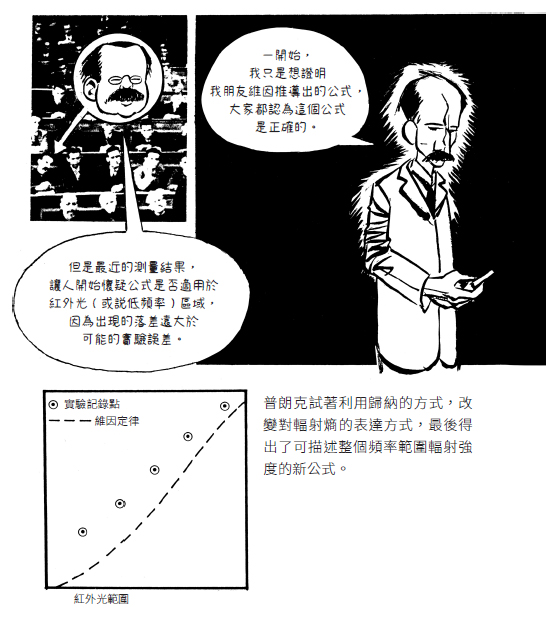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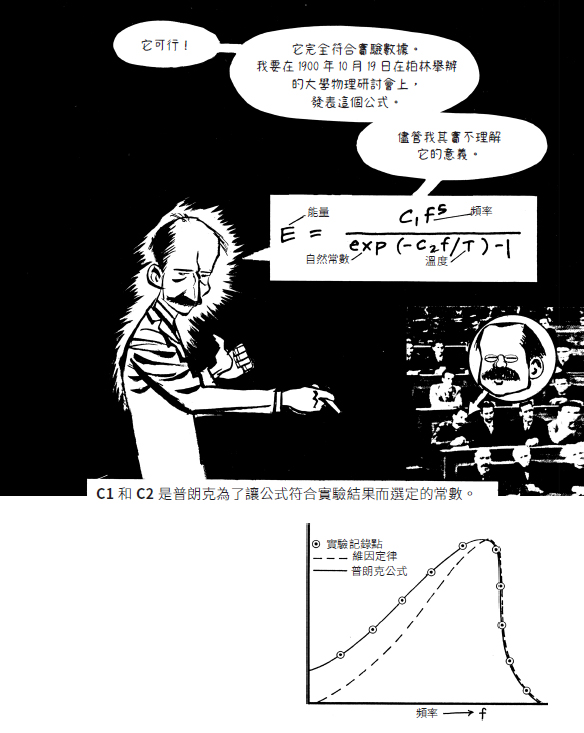






-200x200.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