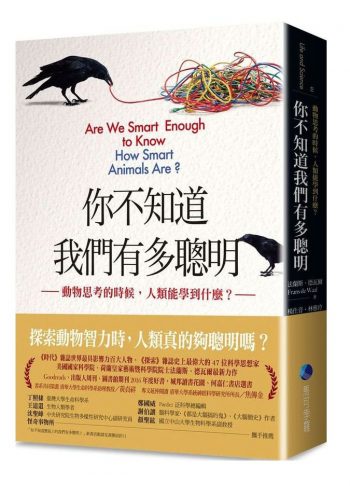撇開動物行為學與行為主義之間的差異,這兩個學派其實有個共通點:都反對過度詮釋動物的智力。他們對「民間」的解釋持懷疑態度,並且駁斥傳聞報導。行為主義的抗拒更加激烈,他們認為行為是我們唯一必須遵循的,內在心理歷程則大可被忽略。
因此,有了這則關於行為主義全然依賴外在線索的笑話:一名行為主義者會在做愛之後向另一名行為主義者問道:「剛剛你覺得很棒。那我呢?」

十九世紀,人們可以自由談論動物的精神和情感生活。達爾文就寫了一整套關於人與動物情感表達的相似之處。達爾文是一位細心的科學家,他仔細查核了消息來源,然後進行觀察驗證。相較於達爾文的細心,其他人則顯得有點過了頭,就像參加一場互相比拚誰的想法最瘋狂的比賽。
動物們擁抱彼此,就能代表他們相愛嗎?
然而,達爾文的門生兼繼承者,出生加拿大的喬治.羅曼尼斯(George Romanes),卻掀起一場如同動物謬誤事蹟的大崩壞。羅曼尼斯收集的動物故事近半數都看似頗有道理,另一半則不是過度渲染,就是明顯不可能發生。這些荒唐故事範圍廣大,例如老鼠會排成一列,用前腳一個接一個將偷來的雞蛋細心運進自牆上鑿出的洞;或是某隻被獵人以子彈擊中的猴子,向獵人伸出沾滿鮮血的手,而讓獵人深感內疚等。
羅曼尼斯知道這種行為所需的心理運作,再經由自己的推斷得出結論。他過度依賴單一事件,且過於信任個人經驗。我並不否定任何動物軼事,特別是經由相機拍攝或錄影記錄的故事,或來自值得信賴且了解動物的觀察者;我也把這些軼事視為研究的起點,但絕不會是終點。給完全蔑視軼事的人一個忠告:請記住,幾乎所有動物行為的有趣研究,都源於一則引人注目或令人費解的事件。軼事提醒了我們有哪些事可能發生,同時挑戰我們的想法。

不過,我們也不能因此忘記有時事件只是偶發,或是忽略了某些關鍵的決定因素。觀察者也可能因為基於某種臆測而無意識地遺漏了重要細節。這些問題不能只靠收集更多軼事來解決。就像俗話說:「重複出現的軼事不能當成數據盡信。」
諷刺的是,當輪到自己挑選門生與繼承者時,羅曼尼斯選擇了勞埃德.摩根(Lloyd Morgan)。摩根終結了所有來自羅曼尼斯的天馬行空。一八九四年,英國心理學家摩根系統化地闡述了所有心理學最引人注目的一句話:
如果一個行動被解釋為一個位在較低心理量表上的結果,那麼,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不能將這個行動視為一個更高心理能力運作的結果。
每一代心理學家皆忠實重現了摩根原則(Morgan’s Canon),認定動物是一種遵守刺激反應機制的機器。可是摩根的意思並非如此。事實上,他補充道:「簡單的解釋絕對不是真相的必要條件。」用以表達他不認為動物只是沒有靈魂的盲目機器。任何一位自重的科學家都不會想要談論「靈魂」,而否認動物擁有「任何」智能和意識,已十分接近談論「靈魂」了。
這些觀點讓摩根頗為吃驚,因此又在他的原則添加了一項準則:如果物種已被證明具有較高智力,那麼更複雜的認知解釋便沒有什麼不對。面對黑猩猩、大象和烏鴉等動物,我們已有充分的認知證據,因此我們真的無須在每次震驚於看似聰明的行為時,得再從頭開始解釋;我們無須經由像大鼠之類較低等的動物,來解釋牠們的行為。即使是被低估的大鼠,零也不太可能是最好的起點。

追求認知簡約往往與演化簡約衝突
摩根原則過去被視為奧坎剃刀(Occam’s razor)的變形。奧坎剃刀是十四世紀修道士奧坎(William of Occam)提出的問題解決原則,即在眾多假說中,應該挑選假設最少的那一個,也就是應以最少的假設尋求解釋。這是個崇高的目標,但我們如何能以一個極簡主義的解釋原則來解釋奇蹟呢?從演化角度來看,在人類擁有認知的同時,動物卻不具備任何認知,那才真是個奇蹟。追求認知簡約往往與演化簡約衝突。
我們相信演化是漸進修正的,但卻沒有生物學家願意付出努力,去解釋認知也是漸進演化而來。我們不喜歡提出、也沒有實際提出相關物種間存有認知差距的解釋。如果自然界沒有任何基礎,人類該如何攀上理性和自覺的臺階呢?摩根原則避開了人類,僅嚴格地應用在動物身上,促進了躍變論者(saltationist)的觀點,人類的心靈因此懸吊在空蕩蕩的演化空間中。摩根自知他原則的不足之處,敦促我們不要混淆了簡單與現實。
很少人知道動物行為學當初也是崛起於對主觀解釋的懷疑。丁伯根和其他荷蘭的動物行為學家,深受由兩位小學老師所寫的暢銷圖文書影響,他們在書中教導對自然抱持愛與尊重,堅持野外觀察才是真正了解動物的方法。此舉激發了一場大規模青年運動,荷蘭青年每個星期天會進行戶外實地考察,孕育出一代熱情的自然主義者。
然而,這並未與荷蘭的「動物心理學」(animal psychology)傳統成功結合,其主要代表人物即是約翰.百靈斯.德哈恩(Johan Bierens de Haan)。學識精深、頗有學者風範的國際知名教授百靈斯.德哈恩,看起來並不像會出現在野外實驗場的人,但他其實偶爾會拜訪丁伯根的野外實驗場,場地位於荷蘭中部的許爾斯霍斯特(Hulshorst)溪床沙洲。
實驗場裡的年輕人穿著短褲、手拿捕蝶網跑來跑去,這位老教授則西裝筆挺地緩步行走。這些拜訪是兩位科學家在研究變得南轅北轍之前,關係密切的證據。年輕的丁伯根很快地開始質疑動物心理學的原則,例如其所依賴的自省方式。漸漸地,丁伯根的思想與百靈斯.德.哈恩的主觀主義漸行漸遠。另一方面,與百靈斯.德哈恩來自不同國家的勞倫茲,對這位老人家的耐心就比較少,還常拿他的名字開玩笑,頑皮地把他叫成德.比爾哈恩(Der Bierhahn,德文意為啤酒水龍頭)。

今日,丁伯根以他的四個為什麼(Four Whys)聞名於世,這四個為什麼即是四個行為的補充提問,不過都未明確提及智能或認知。那時的動物行為學避開了所有有關內在狀態的形容,對於一個新興的經驗科學來說,這種方式也許至關重要,因為任何敏感話題都可能讓一門剛萌芽的學科旋即滅亡。
因此,動物行為學當時短暫地闔上了認知的大門,著重於行為的生存價值,自此種下了社會生物學(sociobiology)、演化心理學(evolutionary psychology)和行為生態學(behavioral ecology)的種子,進而提供了繞過認知的捷徑。一旦出現關於智力或情緒的問題,動物行為學家就會迅速地以功能重新表達這些問題。例如,如果一隻倭黑猩猩對另一隻尖叫的同伴做出緊抱的舉動,古典動物行為學家首先會想到這種行為有什麼功能。他們會討論受益最多的是表現者還是接受者,而不會想要了解兩隻倭黑猩猩彼此的關係,或者為什麼一隻的情緒會影響另一隻。他們不會問是否有可能出自猿類的同情?或倭黑猩猩是否會考量對方的需求?即使到了今日,這些與認知相關的問題還是會令許多動物行為學家感到不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