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一月,卡拉哈里沙漠的狐獴(meerkat),在清晨五點,就把鼻子探出土丘外面;其他的族群則多睡了一個小時多。經過十一年多的觀察,研究人員發現每個狐獴族群有自己的時間表,即便一個族群內,原始的成員都已經死亡。狐獴會在族群間移動,所以這個差異不會是遺傳性的;移民會適應當地的「習慣」,而幼體則從成體學習起床的時間。這些證據顯示,不是只有人類具有「傳統」。
在一月,卡拉哈里沙漠的狐獴(meerkat),在清晨五點,就把鼻子探出土丘外面;其他的族群則多睡了一個小時多。經過十一年多的觀察,研究人員發現每個狐獴族群有自己的時間表,即便一個族群內,原始的成員都已經死亡。狐獴會在族群間移動,所以這個差異不會是遺傳性的;移民會適應當地的「習慣」,而幼體則從成體學習起床的時間。這些證據顯示,不是只有人類具有「傳統」。
資料來源:ScienceShot: Meerkats Have Their Own Traditions [ 6 July 2010]
 在一月,卡拉哈里沙漠的狐獴(meerkat),在清晨五點,就把鼻子探出土丘外面;其他的族群則多睡了一個小時多。經過十一年多的觀察,研究人員發現每個狐獴族群有自己的時間表,即便一個族群內,原始的成員都已經死亡。狐獴會在族群間移動,所以這個差異不會是遺傳性的;移民會適應當地的「習慣」,而幼體則從成體學習起床的時間。這些證據顯示,不是只有人類具有「傳統」。
在一月,卡拉哈里沙漠的狐獴(meerkat),在清晨五點,就把鼻子探出土丘外面;其他的族群則多睡了一個小時多。經過十一年多的觀察,研究人員發現每個狐獴族群有自己的時間表,即便一個族群內,原始的成員都已經死亡。狐獴會在族群間移動,所以這個差異不會是遺傳性的;移民會適應當地的「習慣」,而幼體則從成體學習起床的時間。這些證據顯示,不是只有人類具有「傳統」。
資料來源:ScienceShot: Meerkats Have Their Own Traditions [ 6 July 2010]
本文與 PAMO車禍線上律師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走在台灣的街頭,你是否發現馬路變得越來越「急躁」?滿街穿梭的外送員、分秒必爭的多元計程車,為了拚單量與獎金,每個人都在跟時間賽跑 。與此同時,拜經濟發展所賜,路上的豪車也變多了 。
這場關於速度與金錢的博弈,讓車禍不再只是一場意外,更是一場複雜的經濟算計。PAMO 車禍線上律師施尚宏律師在接受《思想實驗室 video podcast》訪談時指出,我們正處於一個交通生態的轉折點,當「把車當生財工具」的職業駕駛,撞上了「將車視為珍貴資產」的豪車車主,傳統的理賠邏輯往往會失靈 。
在「停工即停薪」(有跑才有錢,沒跑就沒收入)的零工經濟時代,如果運氣不好遇上車禍,我們該如何證明自己的時間價值?又該如何在保險無法覆蓋的灰色地帶中全身而退?

過去處理車禍理賠,邏輯相對單純:拿出公司的薪資單或扣繳憑單,計算這幾個月的平均薪資,就能算出因傷停工的「薪資損失」。
但在零工經濟時代,這套邏輯卡關了!施尚宏律師指出,許多外送員、自由接案者或是工地打工者,他們的收入往往是領現金,或者分散在多個不同的 App 平台中 。更麻煩的是,零工經濟的特性是「高度變動」,上個月可能拚了 7 萬,這個月休息可能只有 0 元,導致「平均收入」難以定義 。
這時候,律師的角色就不只是法條的背誦者,更像是一名「翻譯」。
施律師解釋「PAMO車禍線上律師的工作是把外送員口中零散的『跑單損失』,轉譯成法官或保險公司聽得懂的法律語言。」 這包括將不同平台(如 Uber、台灣大車隊)的流水帳整合,或是找出過往的接單紀錄來證明當事人的「勞動能力」。即使當下沒有收入(例如學生開學期間),只要能證明過往的接單能力與紀錄,在談判桌上就有籌碼要求合理的「勞動力減損賠償 」。

根據警政署統計,台灣交通違規的第一名常年是「違規停車」,一年可以開出約 300 萬張罰單 。這龐大的數字背後,藏著兩個台灣駕駛人最容易誤判的「直覺陷阱」。
陷阱 A:我在紅線違停,人還在車上,沒撞到也要負責? 許多人認為:「我人就在車上,車子也沒動,甚至是熄火狀態。結果一台機車為了閃避我,自己操作不當摔倒了,這關我什麼事?」
施律師警告,這是一個致命的陷阱。「人在車上」或「車子沒動」在法律上並不是免死金牌 。法律看重的是「因果關係」。只要你的違停行為阻礙了視線或壓縮了車道,導致後方車輛必須閃避而發生事故,你就可能必須背負民事賠償責任,甚至揹上「過失傷害」的刑責 。
數據會說話: 台灣每年約有 700 件車禍是直接因違規停車導致的 。這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心態,其巨大的代價可能是人命。
陷阱 B:變換車道沒擦撞,對方自己嚇到摔車也算我的? 另一個常年霸榜的肇事原因是「變換車道不當」 。如果你切換車道時,後方騎士因為嚇到而摔車,但你感覺車身「沒震動、沒碰撞」,能不能直接開走?
答案是:絕對不行。
施律師強調,車禍不以「碰撞」為前提 。只要你的駕駛行為與對方的事故有因果關係,你若直接離開現場,在法律上就構成了「肇事逃逸」。這是一條公訴罪,後果遠比你想像的嚴重。正確的做法永遠是:停下來報警,釐清責任,並保留行車記錄器自保 。

另一個現代駕駛的惡夢,是撞到豪車。這不僅是因為修車費貴,更因為衍生出的「代步費用」驚人。
施律師舉例,過去撞到車,只要把車修好就沒事。但現在如果撞到一台 BMW 320,車主可能會主張修車的 8 天期間,他需要租一台同等級的 BMW 320 來代步 。以一天租金 4000 元計算,光是代步費就多了 3 萬多塊 。這時候,一般人會發現「全險」竟然不夠用。為什麼?
因為保險公司承擔的是「合理的賠償責任」,他們有內部的數據庫,只願意賠償一般行情的修車費或代步費 。但對方車主可能不這麼想,為了拿到這筆額外的錢,對方可能會採取「以刑逼民」的策略:提告過失傷害,利用刑事訴訟的壓力(背上前科的恐懼),迫使你自掏腰包補足保險公司不願賠償的差額 。
這就是為什麼在全險之外,駕駛人仍需要懂得談判策略,或考慮尋求律師協助,在保險公司與對方的漫天喊價之間,找到一個停損點 。
除了有單據的財損,車禍中最難談判的往往是「精神慰撫金」。施律師直言,這在法律上沒有公式,甚至有點像「開獎」,高度依賴法官的自由心證 。
雖然保險公司內部有一套簡單的算法(例如醫療費用的 2 到 5 倍),但到了法院,法官會考量雙方的社會地位、傷勢嚴重程度 。在缺乏標準公式的情況下,正確的「態度」能幫您起到加分效果。
施律師建議,在談判桌上最好的姿態是「溫柔而堅定」。有些人會試圖「扮窮」或「裝兇」,這通常會有反效果。特別是面對看過無數案件的保險理賠員,裝兇只會讓對方心裡想著:「進了法院我保證你一毛都拿不到,準備看你笑話」。
相反地,如果你能客氣地溝通,但手中握有完整的接單紀錄、醫療單據,清楚知道自己的底線與權益,這種「堅定」反而能讓談判對手買單,甚至在證明不足的情況下(如外送員的開學期間收入),更願意採信你的主張 。
在這個交通環境日益複雜的時代,無論你是為了生計奔波的職業駕駛,還是天天上路的通勤族,光靠保險或許已經不夠。大部分的車禍其實都是小案子,可能只是賠償 2000 元的輕微擦撞,或是責任不明的糾紛。為了這點錢,要花幾萬塊請律師打官司絕對「不划算」。但當事人往往會因為資訊落差,恐懼於「會不會被告肇逃?」、「會不會留案底?」、「賠償多少才合理?」而整夜睡不著覺 。
PAMO看準了這個「焦慮商機」, 推出了一種顛覆傳統的解決方案——「年費 1200 元的訂閱制法律服務 」。
這就像是「法律界的 Netflix」或「汽車強制險」的概念。PAMO 的核心邏輯不是「代打」,而是「賦能」。不同於傳統律師收費高昂,PAMO 提倡的是「大腦武裝」,當車禍發生時,線上律師團提供策略,教你怎麼做筆錄、怎麼蒐證、怎麼判斷對方開價合不合理等。
施律師表示,他們的目標是讓客戶在面對不確定的風險時,背後有個軍師,能安心地睡個好覺 。平時保留好收入證明、發生事故時懂得不亂說話、與各方談判時掌握對應策略 。

從違停的陷阱到訂閱制的解方,我們正處於交通與法律的轉型期。未來,挑戰將更加嚴峻。
當 AI 與自駕車(Level 4/5)真正上路,一旦發生事故,責任主體將從「駕駛人」轉向「車廠」或「演算法系統」 。屆時,誰該負責?怎麼舉證?
但在那天來臨之前,面對馬路上的豪車、零工騎士與法律陷阱,你選擇相信運氣,還是相信策略? 先「武裝好自己的大腦」,或許才是現代駕駛人最明智的保險。
PAMO車禍線上律師官網:https://pse.is/8juv6k
討論功能關閉中。
費洛蒙是一種非常大的分子,會從動物體內散發出來並影響其他動物身體的行為。
這種物質當初是在 1959 年由德國生物化學家阿道夫.布特南特(Adolf Butenandt)發現, 這位科學家在二十年前就因為首次合成出性激素而獲得諾貝爾化學獎,說他是化學界的搖滾巨星都還不足以形容他的貢獻。

他的研究發現,費洛蒙的功能和激素一樣,但是只對附近的相同物種個體有效。
舉例來說,如果動物 A 在動物 B 附近釋放出性費洛蒙,動物 B 的身體會吸收這些分子,整體行為也會受到影響。這其實代表動物 A 具有像丘比特的能力,只不過用的不是箭,而是分子。
基於以上的原因,費洛蒙有時會被稱為「環境激素」(eco-hormone),因為這類分子的運作方式就像是體外的激素。
和激素相同的是,費洛蒙有各式各樣的結構。有些分子非常小,有些則相當大,不過全都是揮發性分子,這表示分子在特定條件下會輕易蒸發。揮發性物種通常很好辨識,因為會帶有強烈的氣味(像是汽油或去光水)。

研究人員決定把這種分子命名為費洛蒙(pheromone),是因為字面上的意思是「轉移興奮感」,而這正是費洛蒙的功能。
強大的費洛蒙分子可以傳送幾種不同主題的訊號給附近的同類,例如食物、安全狀況或者性。舉例來說,螞蟻會在巢穴和食物之間的路徑散發費洛蒙,來通知彼此食物來源在哪裡。
狗在散步時對消防栓撒尿是為了標示自己的領域,這時釋放的就是領域費洛蒙。就連雄鼠也會散發出性相關的費洛蒙來吸引雌鼠,同時也會導致附近的雄鼠變得更有攻擊性。

人也會散發出任何一種類型的性費洛蒙嗎?
出乎意料的,人類不會散發任何一種形式的性費洛蒙。不過我們自以為有費洛蒙的原因在這裡:1986年,溫尼弗雷德.卡特勒(Winnifred Cutler)發表的研究宣稱,她成功分離出第一種人類性費洛蒙。
在這項研究計畫中,她蒐集、冷凍並解凍來自幾位不同對象的性費洛蒙。一年之後,她將這些分子塗在許多女性受試者的上唇,接著便宣稱她觀察到和大自然的動物類似的結果。
事實上,卡特勒的研究完全是一派胡言。她根本沒有分離出人類性費洛蒙;而只是把奇怪的氣味塗在隨機受試對象的上唇,其中包括——請做好心理準備——腋下的汗水。
與其說是分離出純費洛蒙,不如說她蒐集的是人流汗時排出的電解質,而且還抹在別人的臉上。

直到今天,卡特勒的噁心科學研究還流傳在網路上的各個角落,這表示如果有人在 Google 上搜尋「人類性費洛蒙」,就會和得到一堆錯誤資訊。有些研究人員堅信我們總有一天會發現性費洛蒙,不過在這本書出版的當下,科學界尚未找到任何人類性費洛蒙。
一直以來有不少相關研究在執行和重複進行,也盡可能針對各種變數進行調整,而所有的研究團隊都得出相同的結論:二十一世紀的人類大概沒有性費洛蒙。
但人類有史以來就是這樣嗎?如果大多數的其他哺乳類都有性費洛蒙,包括兔子和山羊,為什麼我們沒有?
答案其實意外簡單:人類學會了溝通。
我們可以用語言(和蠟燭……還有性感內衣……)告訴伴侶我們有興趣滾床單,而雪貂則必須往理想交配對象的方向散發性分子。

——本文摘自《完美歐姆蛋的化學》,2022 年 12 月,日出出版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輾轉反側,徹夜難眠的時候,您幾點起床?就算醒了,工作效率是否異常低落?
在此,請您非但別只想到自己,還要拿出一點同理心:因為被剝奪睡眠的澳洲喜鵲,也深受困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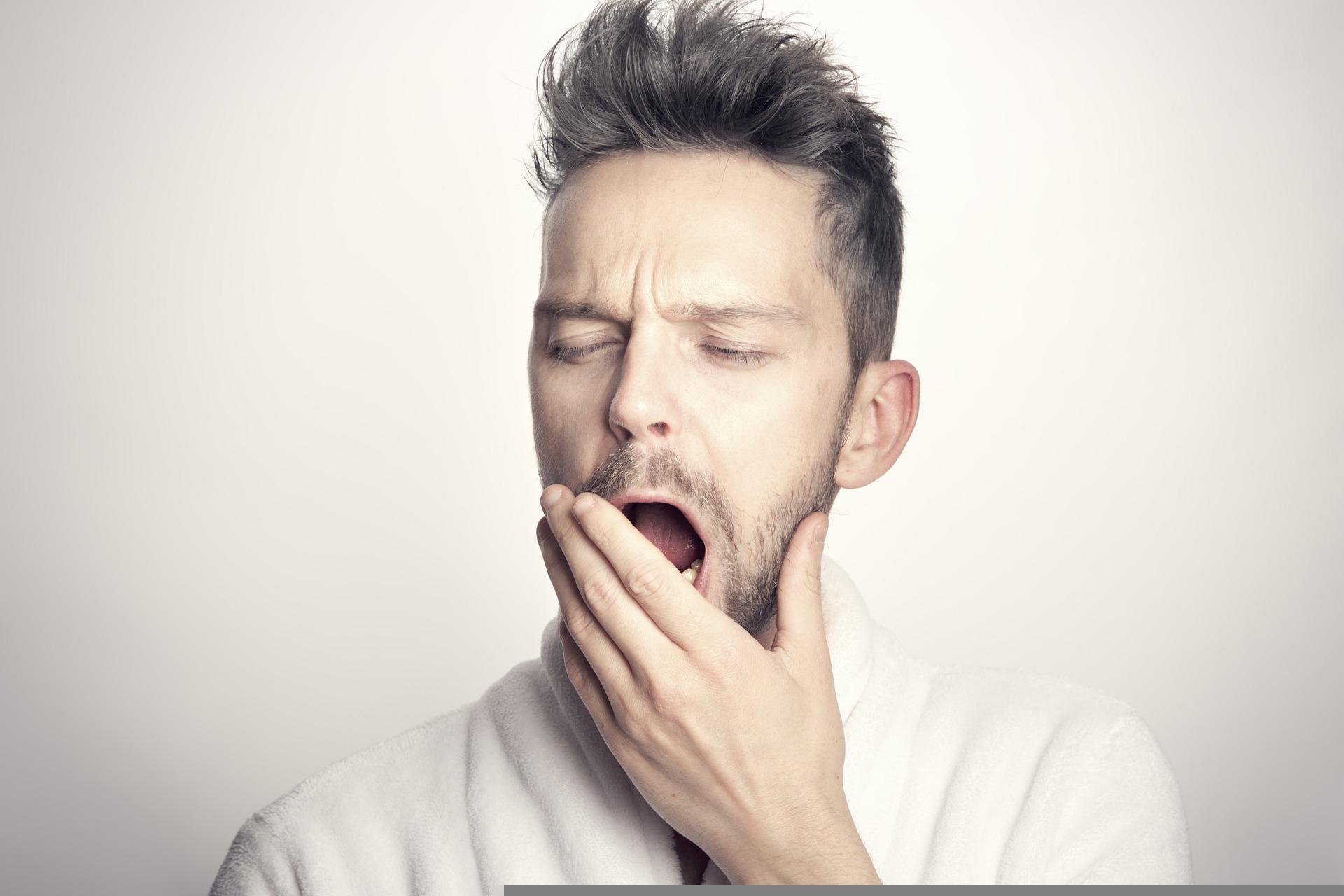
2022 年 4 月的《科學報告》期刊,有一篇標題冗長的論文,叫做〈失眠削弱澳洲喜鵲的認知表現並改變其歌曲產出〉[1]。其第一作者澳洲 La Trobe 大學博士候選人 Robin Johnsson,認為歌唱的時辰與類型,對於喜鵲的社交生活相當重要,並以此做為研究主題[2]。且不論在 COVID-19 疫情之前,有些人就已經沒什麼社交生活,更不要談呼朋引伴一起歡唱 KTV,人家喜鵲可是隨時都過得多采多姿。
於是,牠們就被科學家抓去做實驗了。
首先,研究團隊架設陷阱,用起士誘捕野生喜鵲。為牠們戴上標有序號的腳環之後,再關進裝有監視器的房間裡。接著,為了測量腦電波圖(electroencephalogram, EEG)與肌肉電位圖(electromyogram, EMG),科學家把無辜的喜鵲抓來開刀。於其腦部表面和頸部肌肉,植入電極貼片(electrodes),方便之後記錄睡眠狀態[1]。
然後,喜鵲們就去接受特訓。
研究團隊準備了一種木製食器,左右各挖一個淺槽。其中一個槽裡,盛裝少量起士和麵包蟲。第一次食物直接攤在眼前,不加以掩飾;第二次猶抱琵琶半遮面;第三次開始蓋子完全擋住凹槽,令喜鵲啥也看不見。在訓練的初期,全部的食器都採用灰色蓋子。直到最後的「聯想學習」(associative learning),蓋子被換成黑色或白色。喜鵲掀開特定顏色的蓋子,發現下面藏有食物。這樣重複 15 次,讓牠們不把「食」、「色」的關係兜在一起也難[1]。

結訓後,研究團隊把食器裡的獎勵換成「不會動的麵包蟲冷盤」(chilled, unmoving mealworms),為喜鵲舉辦驗收成果的模擬考。除了執行「聯想學習」的覓食活動,科學家也期望牠們展現「反轉學習」(reversal learning)的能力。將蓋子的顏色調換,要喜鵲嘗試選出有食物的凹槽。這個階段有一些評分要點[1],例如:
凡是順利通過模擬考的喜鵲們,便能晉升至下一關。
在實驗的主要階段,喜鵲們被劃為三組,分別體驗下列三種睡眠模式之一:無干擾睡眠、6 小時睡眠剝奪,以及 12 小時睡眠剝奪。研究人員防止喜鵲睡著的花招,包括:迫近或拍打鳥舍、發出噪音,或是輕撫充滿睡意的喜鵲[1]。如同可憐的臺灣中學生,明明前晚都沒睡飽,隔天還得參加考試。研究人員存心要看失眠的喜鵲,怎麼失常。
正式測驗的結果不出所料,沒睡飽的喜鵲容易犯錯,而且要花較長的時間,才能選出正確答案。有些喜鵲甚至失去參與測驗的動機,傾向找機會補眠。其實以前的研究便顯示,失眠也會降低人類的認知表現。諸如參與動機、清醒程度(alertness)、注意力、警戒等級(vigilance)等,都會受到負面影響[1]。
除了喜鵲考試的成績,科學家也記錄了牠們社交行為的變化。失眠的喜鵲寧可睡覺,也不要唱歌。最後就算唱了,單曲的長度卻意外地延展。原本的晨曲改在中午演出,頻寬變得狹窄,內容相較貧乏,顫音也明顯減少。這與人類的口語溝通,大同小異。當一個人睡眠不足,說話的速度會緩慢下來,咬字不如平常清晰,語句重覆的機率提高,甚至可能妨礙聽眾理解講者所要傳達的訊息[1]。
澳洲喜鵲有複雜的家族。牠們用歌聲來劃定疆域,分辨敵友,並建立「鳥」際關係。失眠不僅會害喜鵲把歌唱得七零八落,也會進一步危及其社交生活。既然以往的人類睡眠實驗結果,與喜鵲有那麼多的相似處,下次在抱怨疫情害自己沒朋友之前,我們是不是應該先睡飽,再來思考怎麼社交呢?

備註:此實驗結束後,參與受試的澳洲喜鵲,均在 2019 年 7 月被野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