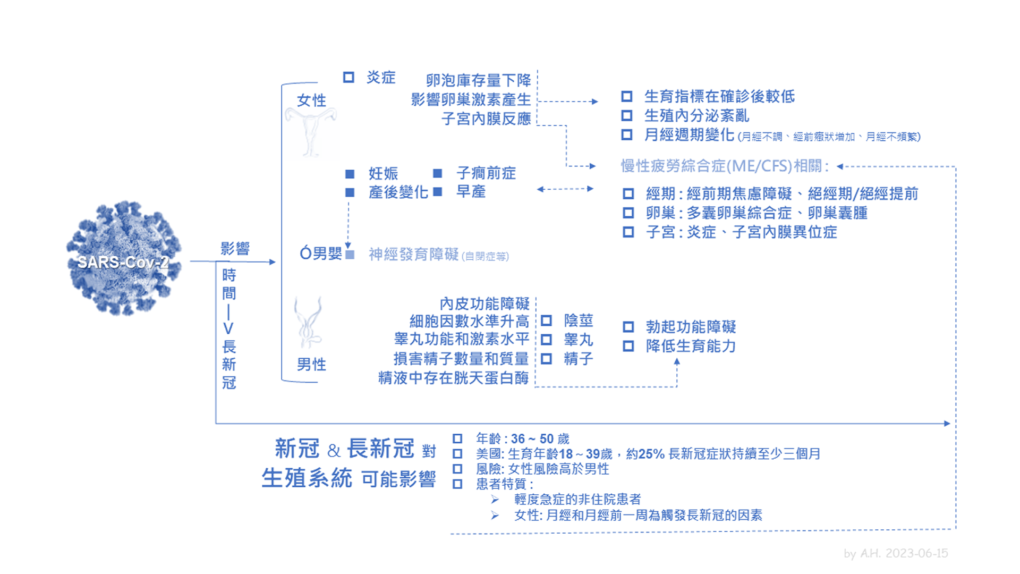沃恩相信感冒病毒對人類文明造成威脅,其實有些疾病是靠著文明才存在的。麻疹就是個例子。由於麻疹只要感染一次就會終生免疫,麻疹病毒在小城鎮很難生存,因為找不到足夠可以感染的人類。如果沒有人繼續被感染的話,病毒就無法存續。流行病學家計算出,麻疹需要至少五十萬相當密集的人口才能不斷延續。
感冒病毒就不同。鳥類是它們自然的宿主,所以它們不必依賴文明。不管人類存在與否,它們的香火都可以延續。

流行性感冒爆發之前二十年,威爾斯 (H. G. Wells) 寫了一本小說《世界大戰》 (War of the Worlds) ,想像火星人入侵地球的情形。它們的死亡戰艦登陸地球,無人能抵擋。火星人以地球人為食物,從骨髓吸走地球人的生命力。人類十九世紀征服世界各角落,成就史無前例,但在火星人面前顯得脆弱無比。在書中,人類沒有任何武器、技術、策略,也沒有任何國家或個人可以藉著勇氣或努力阻擋這批入侵者。
威爾斯寫道:「我覺得過去的一個模糊念頭現在變得很清楚,它在我的腦海中盤旋了好幾天,那是一種統治權被奪走的感覺,我不再是萬物之靈,只是諸多野獸中的一種⋯⋯人類的恐懼和國度已經不再⋯⋯。」
但是就當人類即將滅絕的時候,大自然發揮了力量,入侵者也被侵入。地球上的傳染病殺光了火星人,大自然做到了科學無法完成的事。
對於感冒病毒,自然規律也開始作用。
這個規律在開始時讓感冒病毒變得更兇狠。不管病毒是在堪薩斯州或是其他地方從動物轉移到人類身上,它在從人到人之間的傳染過程不斷突變,逐漸變得更有效率,從一九一八年春天流行的溫和感冒轉變成秋天那波爆發力強勁、手段毒辣的殺手。但當它的威力接近頂點時,另外兩個自然律就出現了。
一個是免疫力的進化。當病毒掃過某個群體之後,這個群體就會發展出某種抵抗力。同一種病毒在抗原漂變前不會再感染同一個人。一九一八年感冒病例在一個群體中從出現到消失的週期大約是六到八個星期。在人群密集的軍隊中,這個週期大約是三到四個星期。
之後可能還有零星病例,但是大流行已結束,結束得相當突然。流行的曲線呈鐘形,但感染數字到了高峰之後會像懸崖般直瀉而下,只剩下少數幾個個案,接著就全部消失。

以費城為例,十月十六日那個星期裡有四千五百九十七位市民死亡,流感讓這個都市崩潰,街道成為鬼域,人們傳說著黑死病降臨。但十天之後新病例急速減少,十月二十六日當局解除了關閉公共場所的命令。到十一月十一日大戰終止時,感冒已經從整個城市消失,來勢洶洶的病毒在燒光所有燃料後,很快就熄滅了。
另一個自然律發生在病毒本身。它只是感冒。感冒病毒本身是危險的,它的危險超過平常想像的發燒或疼痛,但很少像一九一八年那樣造成殺戮。一九一八年那次病毒的毒性比史上任何已知的流行性感冒要強烈得多。
但一九一八年那波病毒和所有病毒一樣突變得很快。數學上有個觀念是回歸常態,也就是極端的事件之後,常跟隨著較不極端的事件。但這並不是定律,只是個可能性。一九一八年的病毒是個極端的例子,任何突變只會降低它的致命性,這是個事實。
所以正當病毒快要像中世紀的黑死病那樣消滅文明時,它的突變朝向常態發展,變成像大多數的感冒病毒一樣。隨著時間推移,病毒便不再那麼致命。
病毒襲擊時間越晚,威力就越小
這個現象首先出現在美國境內的許多軍營裡。在全美最大的二十個營區裡,前五個爆發流行的營區有百分之二十的病患感染肺炎,感染肺炎的人中有百分之三十七點三死亡。
俄亥俄州的雪曼軍營的官兵死亡率最高,是首先遭到感冒襲擊的營區之一,有百分之三十五點七的病患得到肺炎,感染肺炎的人中有百分之六十一點三死亡。雪曼軍營的軍醫因此被烙上汙名,但是軍方的調查發現他們的能力並不遜於其他軍營,他們也做了所有其他軍營做的事。只不過攻擊他們的病毒是所有病毒裡毒性最強的。
三個星期之後,最後五個受襲擊的營區裡只有百分之七點一的患者發生肺炎;得到肺炎的人中只有百分之十七點八不治。

另一個可能的解釋是軍醫在預防和治療肺炎方面變得比較有經驗,但是科學家和流行病學者們卻找不到支持這種論點的證據。軍方的調查小組領導人是喬治.舒柏 (George Soper) ,後來他被韋爾契提拔去主持美國的第一個大型癌症研究計畫。舒柏檢視所有書面報告,並約談多位醫官,他的結論是所有營區中唯一對抗感冒的有效措施是隔離感冒患者,甚至整支被感染的部隊。
但是這些措施「若沒有小心執行就失敗⋯⋯嚴格執行時會有一些效果。」除了病毒本身的突變之外他看不到任何有效、可以改變疫情的辦法。病毒襲擊時間越晚,威力就越小。每個營區裡同樣模式也在發生。同一個營區中在最初十天到兩週病倒的官兵死亡率遠高於在疫情後期被傳染,或是流行結束後才感冒的同袍。
第一批被病毒攻擊的都市:波士頓、巴爾的摩、匹茲堡、費城、路易士維爾、紐約、紐奧良,還有一些較小的城市都發生重大傷亡。同一個城市裡較晚被感染的人病情就比早期被感染的患者輕,死亡率也比在最初兩個星期被感染的人要低。

疫病後期才爆發流行的城市也有較低的死亡率。對一九一八年的流行病學研究中,一項非常小心的研究報告中指出,在康乃迪克「影響死亡率高低有個因素,就是爆發流行的時間與新倫敦發生流行日期的距離,後者是疾病首次進入康乃迪克州的時間⋯⋯病毒在剛進入康州時最為猛烈,然後逐漸趨於緩和。」
全美國,或者說全世界,都是這種模式,不過這並不是絕對的預言,因為病毒是永遠不會穩定的。在較晚被攻擊的地方病毒似乎更容易散播。
德州聖安東尼奧市有最高的患病率,但死亡率卻最低。病毒感染了百分之五十三點五的人口,全城有百分之九十八的家庭至少有一名感冒病患。但那時病毒已經變得溫和,感冒的人中只有百分之零點八的人病故(這個數字仍然是一般感冒死亡率的兩倍)。
病毒本身操有誰生誰死的生殺大權,不是任何醫護照顧可以相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