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彼得.凱夫(Peter Cave);譯者/丁宥榆
我遭受到嚴重的歧視。
我是誰?我是你幾年前、去年或一會兒之前,在你不肯發生性行為,或採取避孕措施時沒能創造出的那個人。有千千萬萬個像我這樣的人,全都受到不公平的對待。
你們這些被生下的幸運兒,把人類生命價值講得頭頭是道,盡最大努力使人好好活著。你們建立法律系統、道德壓力、制衡原則,好保護人類不被殺害。
你們發明醫院、疫苗接種、篩檢計畫,建立安全網、健康法規、男女保健診所,為的都是協助生命延續。一聽到殺嬰、殺幼童、殺嬰兒,幾乎人人為之震驚。

大部分人對於晚期墮胎都十分反感。你們倒是說說看,殺一個在子宮裡快要出生的胎兒,與殺一個剛出生的小嬰兒,在道德上到底有什麼差別?
墮胎和謀殺是一樣的嗎?
你們當中有些人認為,就道德上來看,墮胎與謀殺無異。若晚期墮胎等同殺嬰,為道德所不容,那更早一點的墮胎呢?再更早呢?
如果一天一天倒數回去的話,一個十六週大的胎兒跟十六週少一天的胎兒,於道德上有什麼不同?再小一天呢?用這種方式來思考,再小一天、小一天,直到受孕的那一刻。
受孕!這就是差別所在啊。受孕之前,是不存在所謂成長為人的個別實體的。一個潛在的人根本不存在。卵子要受精才有發展為人——擁有感情和智力、有愛與慾望的可能性。
我要控告你們是「唯距離主義者」和「唯數目主義者」,要不是哲學家對以下這個詞的理解很奇怪,我本來還要說「唯物主義者」。
是沒錯,卵子和精子在受孕之前是有點距離(在結構和物質上都相隔甚遠),但那是數量和地理上的事實,關道德什麼事?雖然兩個是不同的元素,不代表它們不可能變成一個人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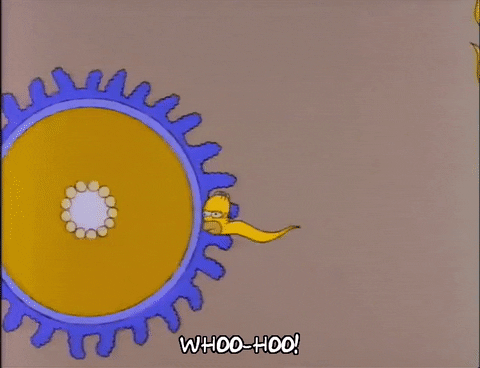
的確,我們無法預先判定游向那個卵子的眾精子中,誰會率先使卵子受精,這裡指的是將發展為胚胎、胎兒、嬰兒、小孩、大人的那一個卵子。
可是毫無疑問,在受精之前一定存在那個特定的精子,我們叫它「精姆斯」好了,它最終將與特定的一個卵子結合,假設叫「卵薇娜」。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受精卵不會出現。
每當(不管是什麼時候)各位進行安全的性行為時,就是在阻止精姆斯和卵薇娜在一起,也就無法產生受精卵,更無法長成胎兒、嬰兒、孩童,也不會有各位如此珍惜的大人人生了。
如果殺人有罪,避孕是不是也有罪?
為了直達問題的核心,我們來討論剛出生的嬰兒吧。畢竟上述問題太好回答。有人會說,人都有求生意志,但是還沒生出來的人不會有需求——好吧,是還沒有需求。
殺嬰有什麼不對?若答案只是「剝奪他往後的人生」,那麼在道德上來看墮胎也不對,因為一旦墮胎,往後他可能成為兒童、大人的人生也沒了。

如果一開始避孕成功,就阻止了胎兒的形成,胎兒就不能長成小孩,小孩無法長大成人,這亦是剝奪了一個未來的人生。進一步往回推,禁慾也不對喔,如此一來就不會有小孩,沒有小孩也就沒有大人。懷孕本身當然也剝奪了其他胎兒形成的機會。
這裡不是要爭論所有潛在的生命都有被創造出來的可能。
假如我們養不活孩子,創造更多的生命也不是好事。
這裡的難題在於,如果,我說如果,殺嬰與墮胎錯在於剝奪一個本來會有未來的人,那麼避孕、甚至於禁慾等諸如此類的行為同樣不對。守貞者與殺嬰者一樣可惡——至少就剝奪本來可存在的未來生命而言。
然而,我們多數人卻認為下這種結論簡直是瘋了。這種似是而非的結論,讓那些誓言守貞的修士修女們一下子成了殺人兇手。
針對這個「如果」我們能怎麼想?
也許我們可以說,以下的思考本身就是錯的:殺人之所以有罪,是因為剝奪他人未來的人生。
另一個似是而非的說法是,那個人會因為失去生命而蒙受損失,所以殺人是不對的。假設有個人叫愛絲梅達,她只是個普通人,她意識到她的自我可以延續下去,若是殺了她,她的渴望、目標、意圖全部落空。
基本上愛絲梅達是想要活下去的,這就是為什麼殺害她是不對的,也是為什麼殺害真正不想活的人很可能不算錯,為什麼自願安樂死和輔助自殺應該被通過。
再者,若有一個存有(being),它沒有意識到自我可延續,於是缺乏讓那個自我延續的渴望,那麼如果用不痛苦的方式結束它的生命,便不會傷害到它。當然了,也許還會有其他很好的理由,說明殺害這樣的個體仍然是不可以,譬如可能會造成他人的痛苦。

照這樣說來,禁慾、避孕和墮胎對那些沒能順利發育的個體,便不算是不道德行為,因為它沒有可延續下去的自我意識,意即上述這些行為並沒有對此個體造成直接傷害。沒人當真認為卵子和精子有慾望也有意圖,亦沒人當真認為胎兒有慾望及意圖。
就此而言,很小的嬰兒也沒有這樣的自我延續意識。
但是殺嬰和某些墮胎仍有可能是不對的,只要這麼做會給其他人帶來傷痛,尤其是母親。我們只是凡人,對晚期墮胎及殺嬰感到難過和痛苦是很正常的,以理智去壓抑的話,恐怕會產生不良的連鎖反應。
對於上述要我們無須擔心那些沒被創造出的人,而且覺得這樣很合情合理的這番解釋,若要做出回應的話,不妨想想這句做人的道理:「推己及人」,你希望別人怎麼待你,你就怎麼待人。
大多數人來到這個世上是歡喜的(他們是這樣說啦,是不是自欺就不知道了),假如你今晚打算來做人,可能被你創造出的那個人,會因你將自己想望的對待──即被創造出來──施予他而感到開心!
所以造人算是做好事嗎?是的話,你知道今晚搭訕時該怎麼說了吧。
但是小心、小心喔,後果自負喔!
——本書摘自《機器人會變成人嗎?33 則最令現代人焦慮的邏輯議題》,2019 年 10 月,EZ 叢書館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