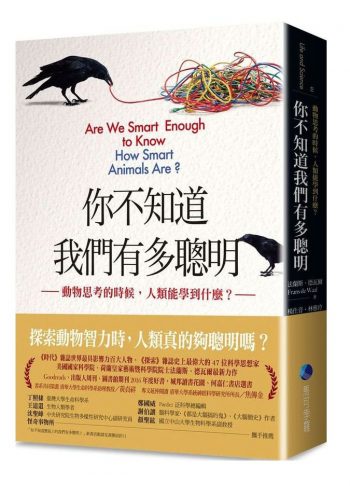由於中斷觀點(discontinuity stance)本質上屬於前演化(pre-evolutionary),我就直接把它稱為新創世論(Neo-Creationism)吧。千萬別把新創世論和智能設計論(Intelligent Design)混為一談,後者只是舊瓶裝新酒的創世論。新創世論比較巧妙,因為它接受了半套的演化論,其中新教條是我們的身體演化自猿類,但是我們的心智並非如此。雖然沒有明確表明,但它假定演化已停格在人類頭上。
在許多社會科學、哲學和人文學科領域,這種想法依然普遍。新創世論認為人類心智是如此原創,除了為其確立特殊地位之外,將人類心智與其他動物相比並沒有任何意義。既然明明沒有能夠比較之處,我們為何還需要關心其他物種?這種跳躍式觀點是基於人類必定在演化過程中發生了重大變化而與猿類分道揚鑣,這個過程可能是在近幾百萬年間。儘管這種神奇變化籠罩著神祕色彩,但今日已被授予一個專有名詞--「人化作用」(hominization),其中經常伴隨了火花、間隔和鴻溝等詞彙。該領域的現代學者顯然不敢提到什麼神聖的火花,更不敢說「特殊創造論」(special creation),但仍然很難撇除此一立場背後的宗教影響。
在生物學中,「演化停格在人類頭上」的概念被稱為華萊士難題。
一顆能譜曲、算數的大腦,是生存必需的嗎?
艾爾弗雷德.羅素.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是與達爾文生活在同一時代的偉大英國自然學家,被認為與達爾文同是天擇演化的發想者。事實上,天擇的概念也被稱為達爾文-華萊士理論。儘管華萊士毫無疑問地支持演化論,但是他為人類心智領域畫上一條界線。他對所謂的「人類尊嚴」抱持強烈情感,無法忍受拿猿類來與人類做比較。達爾文認為,所有特徵都是功利主義的產物,只有生存才是真正的必要條件,但華萊士認為此規則必定有例外—-那就是人的心智。

為何生活單純的人類,需要一顆能夠譜寫交響樂或計算數學的大腦?他寫道:「天擇,只賦予野蠻人稍微優於猿類的大腦,然而,也許這些野蠻人實際上擁有一顆不輸上流社會人士的大腦。」在東南亞旅行期間,華萊士開始對非使用文字的民族產生高度敬重,他認為我們之間「沒有差多少」的觀念,在當時盛行的種族主義觀點下是一項重大進展,當時認為這些野蠻民族的智力介於猿類和西方國家人民之間。雖然華萊士並無宗教信仰,但他將人類的高超智力歸因於「看不見的精神世界」。他認為人的靈魂幾乎無從解釋。達爾文對於看到他所尊敬的同僚援引上帝之手(無論以何種方式呈現)深感不安。他覺得根本不需要任何超自然的解釋,可是華萊士難題仍然潛伏在學術界四周,意圖讓人類心智擺脫生物學的束縛。
我最近前往聆聽一位著名哲學家的演講,聽眾大多為「意識」主題慕名而來,沒想到他在演講時突然提及人類在這方面「明顯」遠高於其他物種。我感到疑惑而搔了搔頭,這樣的說法代表他對於靈長類動物的看法其實有著矛盾,因為這位哲學家給人們的印象是正試圖尋找意識演化的成因。演講中,他提到大腦存在龐大的交互作用,指出意識源於神經相連的數量和複雜度。有位機器人專家也說過類似的話,認為如果電腦擁有足夠數量的微晶片,必定會出現類似意識的現象。我頗為願意相信這番言論,只是目前似乎無人知道如何從連結中產生意識,也不確定意識到底是什麼。
萬物之靈的大腦,有什麼特別的嗎?
若是把重點放在神經的連結,我不禁懷疑要如何看待腦部比人類的 1.35 kg 還重的動物。海豚的腦有 1.5 kg 重、大象 4 kg 、抹香鯨 8 kg,難道這些動物比我們「更有意識」嗎?還是該取決於神經元的數量?我們在這方面的了解還不足。過去我們一直以為,即使不考慮腦的大小,人類腦部的神經元數量是所有物種中最多的,後來發現大象腦部神經元的數量是我們的三倍-—高達兩千五百七十億個。不過,這些神經元的分布位置與我們有異,大象的神經元多分布在小腦。厚皮動物(如大象)的腦部如此巨大,有人推測其中的連結分布非常廣泛,就像額外加上的高速公路系統,大大增加複雜度。

面對人類腦部,我們往往強調被譽為理性所在的額葉(frontal lobe),但額葉在最新的解剖報告中並沒有那麼特別。目前,研究人員認為人類腦部是靈長類動物的「線性放大」,這表示人類不同腦區的大小比例和靈長類動物並無不同。總而言之,神經連結的差別似乎不足以支持人類獨特性的論點。如果我們真的能找到測量意識的方法,可能還會發現到意識是很普遍的現象,在那之前,我們可以參考達爾文提出的某些理論。
我並非否認人類的獨特性,在某些方面我們確實具有獨特性。不過,若是抱持這樣的假設看待所有生物的認知能力,我們便將遠離科學領域而進入信仰範疇。身為任職於心理學系的生物學家,我通常以不同方式探究這個問題。生物學、神經科學和醫學領域都默認了連續性(continuity)。若非如此,治療人類恐懼症時,為何要在實驗室研究大鼠杏仁核(amygdala)對於恐懼的反應?能如此實驗的前提,當然就是所有哺乳類動物的腦部皆相似。對這些領域而言,所有物種間的連續性是理所當然的,就算人類有多麼重要,也不過是全體自然界裡的一點塵埃。
心理學領域正逐漸朝向這個方向發展,但其他社會和人文科學仍然抱持傳統的不連續性假設,所以我每次在面對這些觀眾的演講中都會強調這一點。我的演講難免會提到人類與其他人科動物的相似之處(但也不是每次都會提到),聽眾每每不約而同地問道:「那麼,身而為人到底有什麼特別呢?」以「那麼」做為問題的起頭,就是想把人類與其他物種的所有相似性都推到一旁,並且只想突顯我們和其他物種有何不同。我通常會用冰山的譬喻回答此類問題,描述我們和靈長類親戚之間在認知、情感和行為上存在龐大的相似度,但當然也有類似冰山一角的差異。自然科學領域試圖理解整座冰山,然而其他學科比較想要從冰山的頂端開始研究。
人是什麼?
西方國家迷戀這座冰山一角已久,而且還沒有要停止的跡象。人類的獨特總是被視為正面,甚至是高貴,但真要說出幾個不光彩的特點也沒想像中困難。我們一直在尋找人類的「獨特之處」,無論是拇指對生、合作、幽默、純粹的利他主義、性高潮、語言或是喉部結構。這個現象的源頭也許起始於柏拉圖(Plato)和第歐根尼(Diogenes)的辯論,他們試圖找出最簡潔的人類定義。柏拉圖提出人類是唯一的無毛兩足行走動物,但這個定義很快就被反駁了,當時第歐根尼帶了一隻毛被拔光的雞到柏拉圖的講學地點,一到柏拉圖面前,他便放手讓雞走路並說道:「瞧!我給你帶個人來。」人類的定義因此多添加了一條:「擁有寬指甲」。
一七八四年,約翰.沃夫岡.馮.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興奮地宣稱自己找到了人類生物學起源的證據:一小塊人類上顎骨頭,被稱為「頷間骨」(os intermaxillare)。雖然所有包括猿類在內的哺乳類動物都有這塊骨頭,但在此之前一直未能在人類身上找到,因此始終被解剖學家標誌為「較原始的」骨頭。人類也總是把身上找不到這塊骨頭視為值得自豪的現象。身為詩人的歌德也是一位自然科學家,他非常高興能找到這塊與哺乳類動物共享的原始骨頭,就此讓人類與自然界其他物種連結起來。歌德在達爾文提出演化論前的一個世紀就有這種想法,顯示演化概念已經醞釀許久。
直到今日,連續性和例外主義(exceptionalism)之間的張力依然存在,人類的獨特之處一次次地被點出,再一次次地被反駁。就像剛剛提到的頷間骨,人類獨特性的主張通常會歷經四個階段:言論會不停地被傳頌,隨後有人提出新證據反駁,該主張開始逐漸沒落,最後一腳踏進不光彩的墳墓。我常常覺得被這些主觀的論點打擊,這種吸引大眾目光的人類獨特性論點不知從何而來,大家好像也都忘了我們以前根本不覺得這些特質有什麼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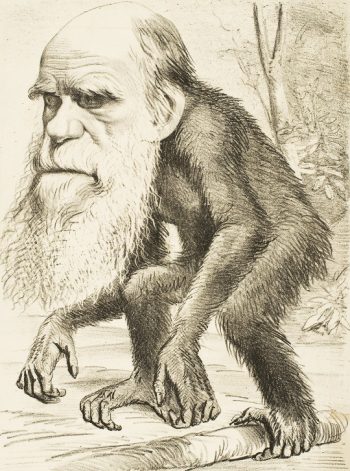
例如,在英語當中(其他語言也是如此),模仿行為的動詞常常用到我們的動物近親,暗示當時認為動物會模仿沒什麼大不了,而且這些行為由人類和猿類所共享。不過,當模仿被重新定義為是複雜的認知行為(也就是「真正的模仿」,”true imitation”),突然間,人類搖身一變成為唯一能掌握這種能力的物種。
這些論點的奇異共識是:「人類是唯一能模仿的猿類」。另一個例子關於心智理論,心智理論其實最早源自於靈長類動物研究。某種程度上,它曾經被重新定義成猿類沒有心智功能。定義與重新定義的循環讓我想起《週六夜現場》節目裡喬恩.洛維茲(Jon Lovitz)扮演的角色,他一直期待能合理化自己的行為,因此不停地思索和尋找理由,直到他能相信自己,於是帶著滿足的假笑說:「是的!這正是我要的!」
討論技術能力時也發生過同樣狀況。早期的印刷品和繪畫通常會將猿類描繪成手持拐杖或其他道具,最令人難忘的圖片是在卡爾.林奈(Carl Linnaeus)於一七三五年出版的《自然系統》(Systema Naturae)。猿類會使用工具眾所皆知,當時也從沒出現過一點爭議。二十世紀時,人類學家將工具使用提升為智力的跡象,因此提出這些藝術家讓牠們手持工具的原因,可能只是想要讓牠們看起來更像人類。此後,猿類的工具使用技術便飽受審視和質疑,甚至是嘲笑,而發生在人類身上的同樣能力則被推舉為智力超群的證明。
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發現(或重新發現)野生猿類會使用工具的現象才會如此令人震驚,但人類學家仍試圖淡化其重要性。我聽過他們表示,黑猩猩可能是向人類學會如何使用工具,彷彿向人類學習使用工具會比自己發展出工具更為容易。這個提議顯然還沒碰到把模仿能力視為人類特有行為的論點。當李奇說我們不是選擇把黑猩猩當成人類,不然就得重新定義人類或重新定義工具,科學家總是直接擁抱第二個選項。重新定義人類永遠不會過時,每當我們找出一個新的特質時就會歡呼:「是的!這正是我要的!」
比起宣稱只有人類的胸腔會跳動(這其實是所有靈長類動物的特點),更過分的是貶低其他物種。嗯,被貶低的不只有其他物種,認為白種男性的基因優於其他人種的觀點也是歷史悠久。種族優勝主義(ethnic triumphalism)的信念延伸至我們自身物種,於是有人會取笑尼安德塔人(Neanderthal)是頭腦簡單的野蠻人。不過,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尼安德塔人的腦容量還比我們稍微大一點,我們的部分基因亦來自他們,而且他們擁有使用火、懂得墓葬、使用手斧和樂器等能力。即使尼安德塔人最終也許會獲得一點尊重,但每當談到猿類時,我們仍然充滿蔑視。
二○一三年,英國廣播公司(BBC)在其網站調查「您是否和黑猩猩一樣笨?」。我很好奇他們是如何確立黑猩猩的智力程度。後來發現該網頁(之後被移除了)只包含有關人類世界事務的測試,跟黑猩猩一點關係也沒有,標題如此只是想要與人類對比。不過,為什麼要拿猿類對比呢?為什麼不選擇蝗蟲或金魚?究其原因,顯然假定每個人都相信我們是最聰明的物種,只是很多人並不了解這些物種與我們的親緣關係。熱愛比較人類與其他人科動物的行為反應出我們沒有安全感,這也出現在書名上,例如《不止是黑猩猩》(Not a Chimp)和《只是隻猿類?》(Just Another Ape?)。
表現超過人類的黑猩猩阿步
面對黑猩猩阿步(Ayumu the chimpanzee)的表現,也有人展現同樣的不安。他們在網路上觀看阿步展現才能的影片,要不是不相信,就是認為這純粹是場騙局,或是做出「我不能接受我比黑猩猩還笨!」的評論。美國科學家認為這個實驗冒犯了他們,因此必須接受特殊訓練好擊敗這隻黑猩猩。當主導阿步研究計畫的日本科學家松澤哲郎第一次聽到這種回響時,他把頭靠在手上沉思。以下是維吉尼亞.莫瑞爾(Virginia Morrell)在報導演化認知領域背景時,描述了松澤哲郎的反應:
我真不敢相信他們有這種反應。如你所知,我們透過阿步發現黑猩猩在一種記憶測試中表現得比人類更好。這是黑猩猩能立即做到的事,但也只有這件事做得比人類好而已。我了解這讓有些人感到沮喪,但是現在居然有研究人員想透過訓練變得跟黑猩猩一樣好。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我們必須在所有領域都是最優秀的。
儘管冰山已經開始融化了數十年,態度轉變的程度仍然很有限。我不打算深入探討這些問題,或是一一介紹最新的人類獨特性主張,在此我想帶領你們了解一些目前逐漸退流行的論述。這些言論描述了智力測試的方法論,這對於我們為動物進行的研究結果至關重要。我們該怎麼對黑猩猩、大象、章魚或馬進行智力測驗呢?這聽起來很像是在開玩笑,但這其實是科學界面對最棘手的問題之一。人類的智力差異本身就已經充滿爭議,尤其在比較不同文化或種族時,然而當我們在不同物種身上討論這個議題時,衝擊更是劇烈。
我會樂意接受最近一項發現愛貓人士比愛狗人士更聰明的研究,假如研究裡探討的是貓和狗之間的智力比較,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這兩個物種間的差異如此之大,很難設計出可以讓兩者同時以相似方式接收和回應的智力測驗。然而,具爭議的不只是如何比較兩種動物,還包括我們往往視而不見、有關動物與人類之間的比較,而我們還經常在這方面放棄所有嚴謹的審查。
科學界對於動物認知領域的新發現都謹慎以待,但是對人類智力的主張卻是反其道而行。只要這些主張如我們預期,科學界就會全盤接受,於是阿步的壯舉便超出了理解範圍。大眾也因此感到困惑,因為不管有人宣稱了什麼,總會有人提出反駁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結論的變動通常是方法論的問題,討論研究方法也許很無聊,但能直指問題核心—我們有能力知道動物有多聰明嗎?
所有科學研究都有其方法論,因此科學家非常重視研究方法。當我們研究的捲尾猴在觸碰螢幕的臉部辨識測試表現不佳時,我們會不斷追蹤數據,直到發現牠們會在每週特定的某天表現得很差。後來我們才發現原因出自一位學生志工,雖然她在測試過程中會仔細地遵循流程,卻做出了分散捲尾猴注意力的行為。這個學生不安且緊張,不斷地改變身體姿勢或調整頭髮,因此也讓猴子感到緊張。我們將這位年輕女性從這個計畫調走後,猴子的表現便大幅提升。
此外,最近也發現在進行小鼠(mouse)研究時,男性研究人員會帶給牠們過多的壓力而影響表現,女性研究人員則沒有這種現象。如果將男性穿過的衣服放在實驗室裡,也會造成相同效果,顯示嗅覺是關鍵。意指男性與女性研究人員執行的小鼠實驗可能有不同的結果。研究方法細節的重要性比我們想像的重要多了,這在進行物種間的比較時尤其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