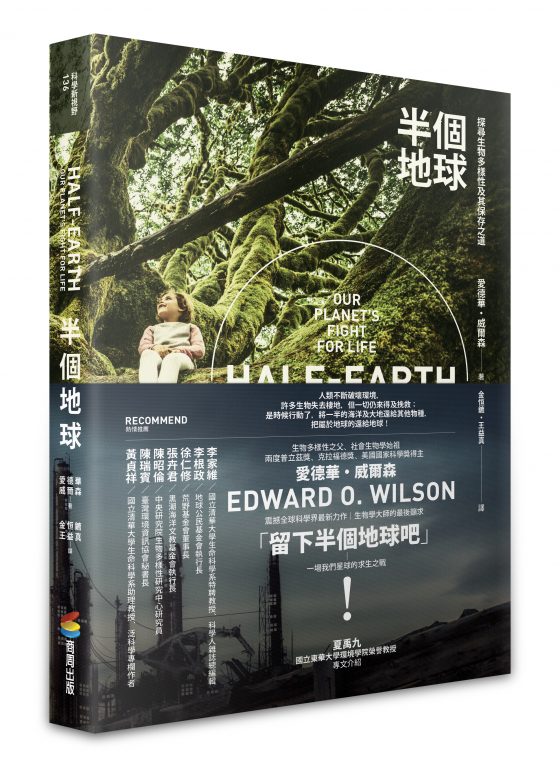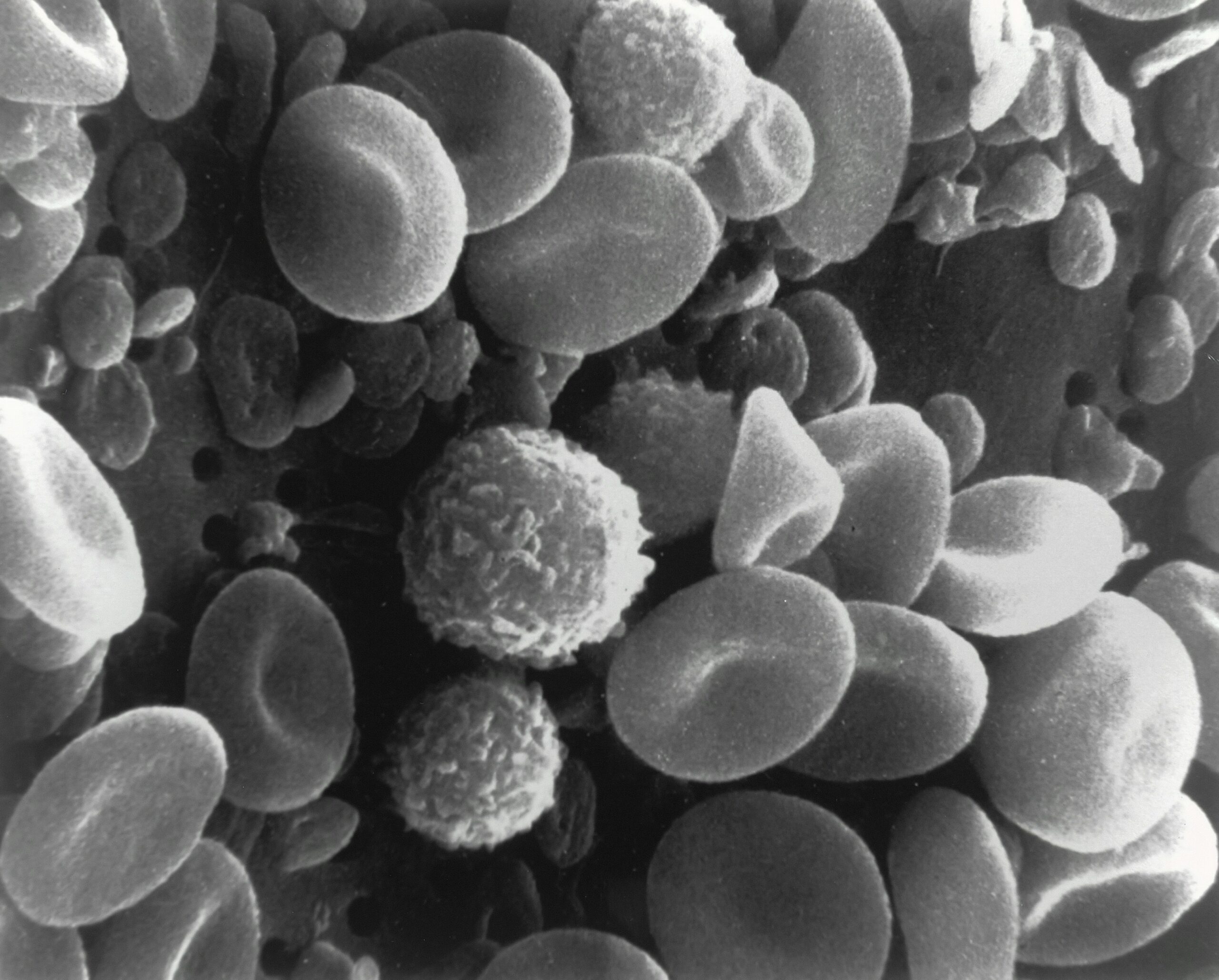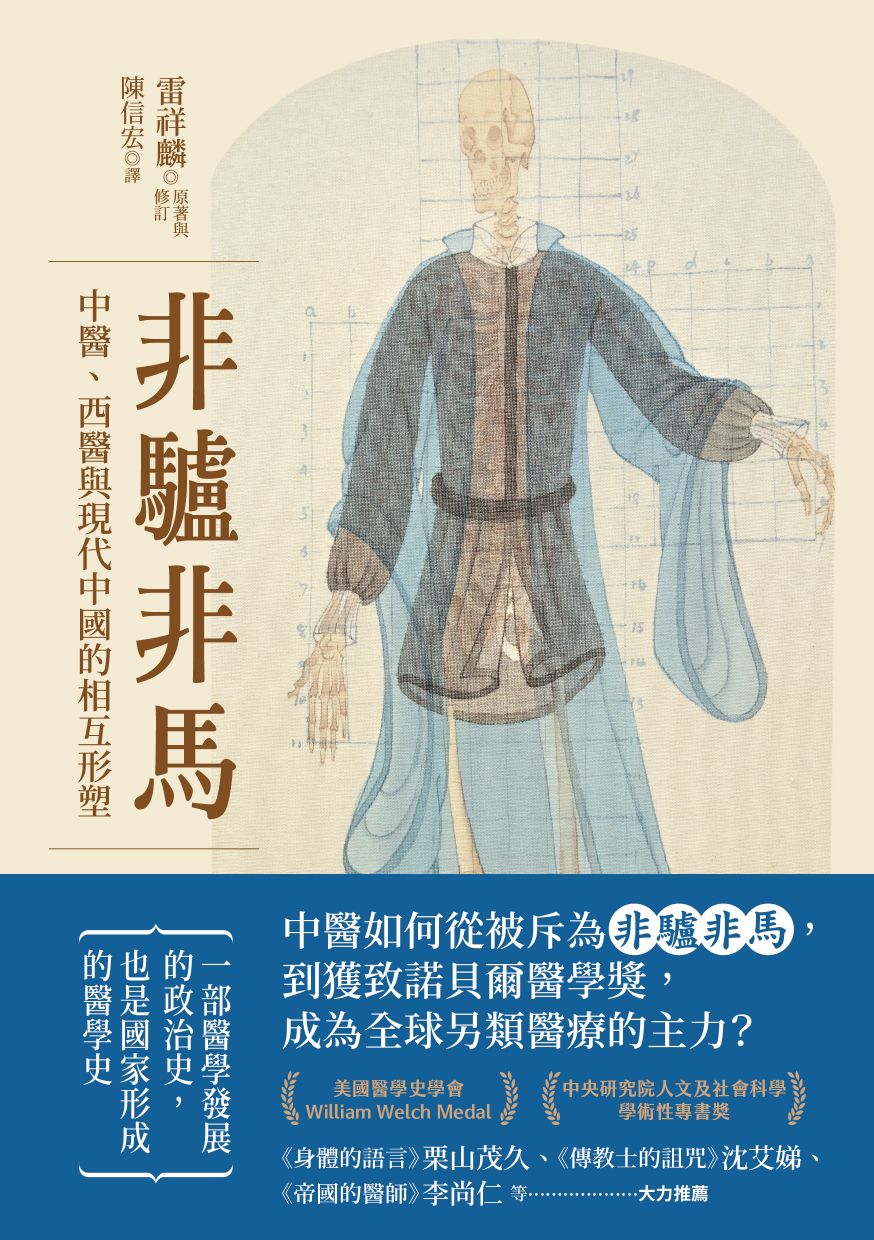世界上的犀牛現存有二萬七千頭。一個世紀以前,曾有數百萬頭犀牛奔蹄在非洲平原上,或漫步在亞洲雨林裡。犀牛一共有五種,但全都處在瀕危險境。現存犀牛以南方族群的白犀牛為大宗,分布在南非,並受到武裝衛隊的嚴密保護。

二○一四年十月十七日,一頭名叫蘇尼(Suni)的北白犀死於肯亞的奧佩傑塔自然保護區(Ol Pejeta Conser vancy)。牠的去逝使世界上最後僅存的北白犀數目減到只剩六頭,其中三頭在奧佩傑塔、一頭在捷克共和國德武爾.克拉洛維(Dvůr Králové)動物園,另兩頭在美國聖地牙哥野生動物園(San Diego Zoo Safari Park)。這幾頭北白犀都已屆高齡,且沒有後代。一來牠們殘存的族類四散於各地,二來在豢養下的北白犀一般來說難以繁殖,因此北白犀在生理機能上已然滅絕。即便把牠們自然的長壽考慮在內,但幾可確定,牠最後的族類到了二○四○年也將死去。
犀牛粉治癌迷思,成了犀牛的間接殺手?
在此同時,黑犀牛的西部族群已完全滅絕,個體早已杳無蹤跡,連豢養的也沒有。曾經有一度,這些具有長而彎角的龐大動物是非洲野生動物的象徵。牠們為數眾多,遍布於喀麥隆到查德的稀樹草原與乾旱熱帶森林之間,南至中非共和國、東北至蘇丹。牠們的數目開始逐漸減少,始於殖民時代的狩獵者,接著是盜獵者;盜獵者割取犀牛角,做成儀式用的匕首刀柄,主要在葉門,但也見諸中東其他地區與北非。最後致命的一擊,則來自中國與越南。他們將犀牛角粉做為傳統中醫的藥材,且需求龐大。
增加的消費量係因毛澤東的煽風點火所致:他青睞傳統中醫,輕視西方醫學。迄今犀牛角粉仍廣泛用來治病,包括性功能障礙與癌症。中國的人口於二○一五年已躍升至十四億,因此只要當中有極微百分比的人們訪求犀牛角,對犀牛而言就是天大的災難了。每公克犀牛角粉價格已飆至與黃金等價。然結果真是既苦又辣的反諷:犀牛將步入滅絕之境,即使犀牛角的醫藥效果並不比人類指甲好。
犀牛角市場招致了一批盜獵之輩與不法之徒。他們志在趕盡殺絕,不留一隻活口;他們不惜以生命做為代價,只為了一個雙手可捧的無生命之物。對所有的五種犀牛來說,面臨的衝擊似乎無寧之日。在一九六○到一九九五年間,西黑犀牛的族群減少了百分之九十八。一九九一年,牠們的最後據點喀麥隆還有五十頭,但到一九九二年就只剩下三十五頭。盜獵者的追殺步步進逼,喀麥隆政府也束手無策,找不出解決之道。到了一九九七年,只剩下十頭黑犀牛。
黑犀牛與白犀牛不同,白犀牛往往相聚成群,可多達十四隻(巧的是,英文字的犀牛「群」稱呼,與「撞毀」同一個字);但黑犀牛除了繁殖期外,平常都是獨來獨往。在西黑犀牛的最後時日,殘存者散布在喀麥隆北部的廣大地區,其中僅有四頭相距夠近,有相遇與交配的機會;但事與願違,最後全都遭到獵殺。數百萬年的榮耀演化,劃上了休止符。
目前全世界最罕見的陸地大型哺乳動物是爪哇犀牛。做為棲息在濃密雨林的居住者,爪哇犀牛原初分布於泰國到華南一帶,之後則進入印尼與孟加拉。直到最近,還有十頭爪哇犀牛隱密地生活在越南北部一片未受保護的森林裡,大體不為人知,且該地已劃設為吉仙國家公園;不久後,牠們的聲名遠播,所有的犀牛都遭到盜獵者的毒手。最後一頭在二○一○年四月慘死於獵槍口下。

犀牛的守護者:繁殖科技、飼養員與公園守衛
現今碩果僅存的爪哇犀牛族群,位於爪哇島最西端的烏戎庫隆國家公園,全數不到五十頭(有位專家告訴我是三十五頭)。在這種情況下,只消一場自然大災難,或是一小群嗜殺成性的盜獵者,一夕之間爪哇犀牛就會無一倖免。
另一個罕見度及危機度與爪哇犀牛不相上下的,是蘇門答臘犀牛,生活在亞洲濃密雨林的另一個物種。蘇門答臘犀牛與爪哇犀牛一度普遍分布在東南亞地區;曾幾何時,農耕地霸占牠們大部分的棲地,加上盜獵者的覬覦,蘇門答臘犀牛現今幾乎只侷限在數個圈養的動物園,及在蘇門答臘面積日縮的森林裡;也許還有幾頭,隱藏在婆羅洲偏遠的角落。
從一九九○年到二○一五年間,全世界的蘇門答臘犀牛族群數遽降為三百頭,然後是一百頭。在獸醫師泰瑞.羅斯(Terri Roth)與她在美國辛辛那提動物園與植物園的隊友努力下,她們用人類的現代繁殖科技拯救犀牛,堪稱是一項壯舉。如今她們成功繁殖了三代犀牛,且小心翼翼地把幾隻首創的犀牛周全護送回蘇門答臘的保留區。這套過程不但費時費事、困難重重、花費昂貴,而且成敗難卜。況且,總是有一批日以夜繼的覬覦盜獵者,為了眼前的一隻犀角與終身的溫飽,甘願賭上性命。
如果,捕獲後飼養的工作人員與印尼公園的守衛沒能達成任務,蘇門答臘犀牛便會因此消失。一個特殊的大型動物血脈就此中斷,數千萬年來漫長的演化也歸於塵土。蘇門答臘犀牛的最近親緣是北極的毛犀牛,牠們在上一個冰河期消失了,可能是被石器時代的獵人逼死的。這些獵人(至少在歐洲)在洞穴壁上為犀牛作畫自娛,如同現在的我們也從中得到樂趣一般。

回想一九九一年,兩頭犀牛正值年輕
一九九一年九月底,我應愛德.馬盧斯卡(Ed Maruska)園長之邀訪問辛辛那提動物園,去要看一對新近在蘇門答臘捕獲、從洛杉磯動物園專程送來的蘇門答臘犀牛:一隻叫埃咪(Emi)的母犀,及另一隻叫依普(Ipuh)的公犀。雖然兩頭犀牛都還年輕力壯,但不被期望能活太久,因為蘇門答臘犀牛的壽命與家犬一般不相上下。
近晚,我們抵達動物園旁邊的一座空倉庫。陣陣震耳欲聾、古里古怪、無關動物園管理的搖滾樂轟擊著倉庫的內牆。馬盧斯卡解釋說,這噪音是為了保護犀牛。偶爾飛機會來來回回地低空掠過,飛向鄰近的辛辛那提機場;有時突如其來地,還會有警車尖嘯聲,及隔街疾駛而過的消防車呼嘯聲。深夜裡突發的噪音會驚擾犀牛,造成衝撞而傷到自己。搖滾樂的演奏聲勝過同樣大聲但突然地、諸如樹倒下的轟然聲或虎的接近聲,那是牠們家鄉真正的危機所在;或是獵人的腳步聲──從原始到現代,蘇門答臘犀牛在亞洲獵人的視線下已暴露了超過六萬年之久。
當晚,埃咪與依普被分別關在超大的籠裡,如雕像般立著,我真不知道牠們是否入睡了。當我們走向這兩隻犀牛時,我問馬盧斯卡是否可摸摸牠們。他點了頭,我摸了牠們。我用指尖輕輕地、快速地滑過。在當下,一陣神聖與永恆的感覺襲上心來,那是難以用文字表達的感覺──就是現在,內心也不可名狀地起伏。
本文摘自《半個地球:探尋生物多樣性及其保存之道》,商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