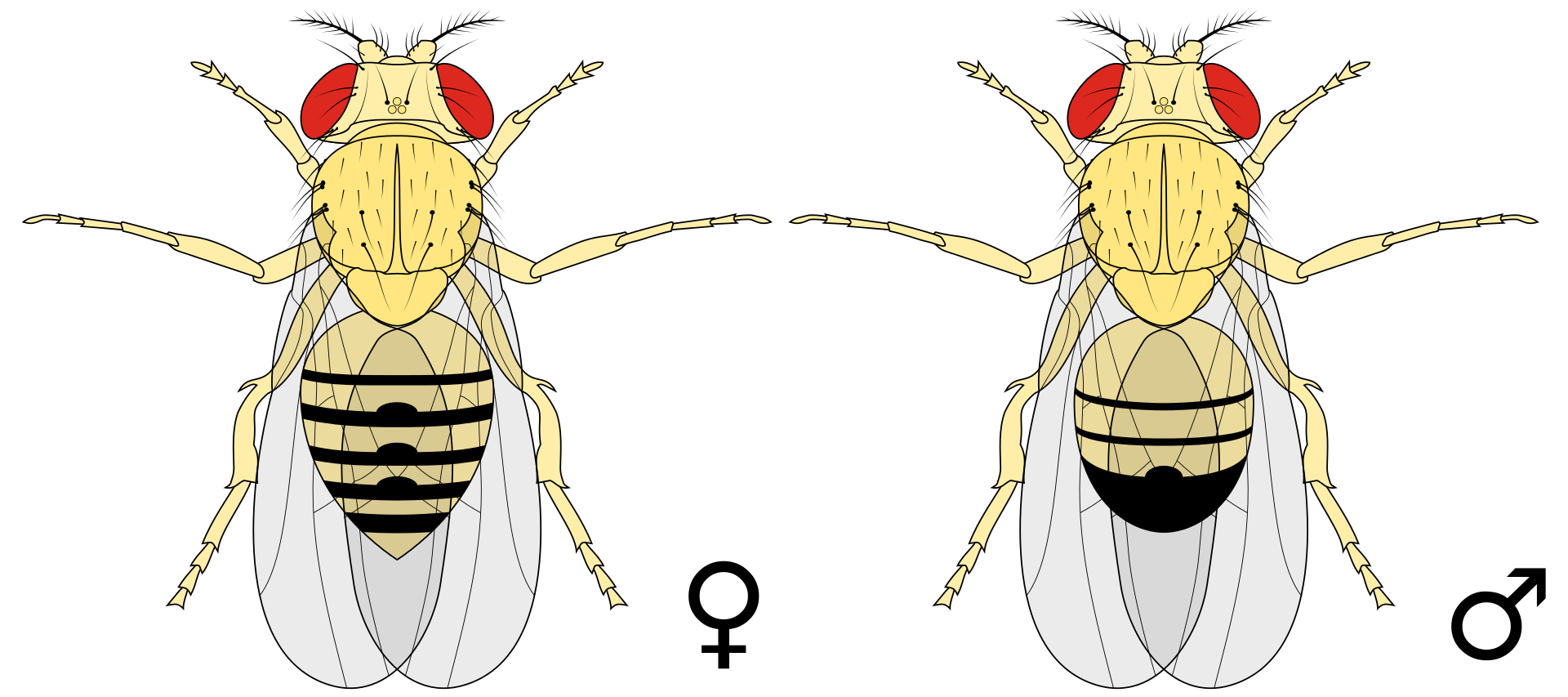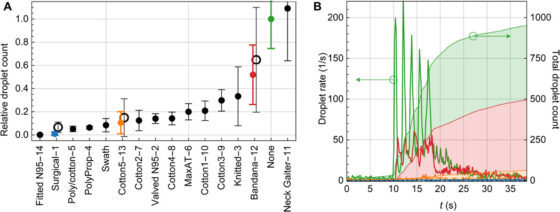你咀嚼麵包時,就能嘗到這種過程。你的唾液和澱粉混合,一股甜甜的味道油然而生。把一滴唾液加入一匙蛋奶糊裡,沒幾秒鐘整個就會清清如水。
這讓人不禁聯想,唾液(或嬰兒口水更好)應該可以拿來預先處理食物汙漬。洗衣粉或洗衣精總是吹噓含有酵素成分,那真的是所謂的消化酵素嗎?我寄電子郵件去問「美國清潔協會」,這名字聽起來像是什麼尖端研究機構,原來只是一個貿易組織,它先前的名號較不響亮,叫做:「肥皂與清潔劑協會」。
協會發言人桑索尼(Brian Sansoni)沒有顯出絲毫為自己的嘲諷讚賞之意,把我轉介給一位名叫斯皮茲(Luis Spitz)的化學家。斯皮茲博士回信說:「抱歉,我只知道和肥皂有關的題材。」桑索尼(還是沒有一絲喜悅)又給我一位清潔劑專業顧問格萊姆(Keith Grime)的電話號碼。
等我自覺能從容應對,才打了電話給格萊姆。答案是肯定的。比較高檔的清潔劑至少含有三種消化酵素:澱粉酶分解澱粉汙漬、蛋白酶分解蛋白汙漬、脂酶則分解油脂汙漬(不只是食用脂肪,還包括身上的油脂,例如皮脂)。洗衣粉根本就是裝在盒子裡的消化道。洗碗精也一樣:晚餐客人沒吃完的食物,蛋白酶和脂酶會把它們吃掉。
利用消化酵素來清潔,這個好主意要歸功於化學家及樹脂玻璃的發明者羅姆(Otto Röhm)。一九一三年,羅姆從家畜的胰臟中萃取出酵素,用它們來預浸髒布,有可能是幫屠宰場員工預洗衣物以交換胰臟;歷史久遠細節已不可考。從動物的消化道裡萃取消化酵素,成本昂貴且相當費工。以首次商業化生產的洗衣酵素來說,科學家用的是某種細菌生產的蛋白酶。商業用的脂酶不久後也應運而生,其基因被轉殖到某種真菌。真菌類比較大,比較容易處理,不需要用顯微鏡來觀察那些畜群或農作物(或和真菌類有關的任何集合名詞)。
格萊姆告訴我,有一種在森林地面發現的酵素,能分解死掉倒下的樹木纖維素。從前他在寶僑公司工作時,曾試圖用它來做為纖維柔軟劑。(柔軟劑的作用,正是溫和的消化纖維。)結果沒有成功,但是這種酵素具有更厲害的功效。它能消化細棉纖維,亦即毛衣上起糾結的毛球。(過分的是,「抗起毛球酵素」對純羊毛衣竟然沒效。)
我們談唾液已經談得老遠,卻還沒有提到我打電話真正想問的問題。該是從森林回歸正題的時候了。
「如果你吃東西時,襯衫不小心滴到什麼東西,」我問格萊姆:「用唾液塗一塗行得通嗎?會不會像是天然洗衣預浸作用?」
「這個想法很有意思。」
格萊姆博士隨身帶著汰漬(Tide)去漬筆。他不會用自己的口水。
藝術品修護師會用口水。「我們拿棉花團和竹籤做成棉花棒,放在嘴巴裡弄濕,」謝法列(Andrea Chevalier)說,她是博物館館際維護協會的資深繪畫修護師。唾液對於容易受損的表層特別有用,因為溶劑或水可能會將它們溶解。一九九○年,一群葡萄牙修護師拿口水來與四種常用的非解剖清洗液相比較。評比以清潔能力為主,但不能損傷「水貼金金箔」及低溫彩繪黏土表面,唾液被評為「最佳」清洗液。變性唾液(除去其中酵素分解的能力)也經過測試,結果證明比不上純口水。
繪畫修護師和洗衣配方設計師一樣,對於比較典型的清潔工作,也會採用商業生產的消化酵素。蛋白酶可用來溶解以蛋白或皮膠做成的淡彩。(古時候修護師的知識沒那麼強,習慣把兔皮做成的膠塗抹在油畫布上,以強化剝損的繪畫。)脂酶則可穿透層層的亞麻籽油,十八、十九世紀的畫家用亞麻籽油來增加光線的折射效果,以及把繪畫作品的表面「餵飽」。
謝法列自己爆料說,有些修護師的唾液明顯比別人的清潔效果更好,常讓人不免暗忖,這些人中午到底喝了多少馬丁尼。實際上,人體唾液的化學組成,天生就有很大的個別差異。
每個人的「流量」也有很大的差異。拿希雷提和我來說好了,我們咬棉花團的時間一樣長,我產生○‧七八毫升的刺激性唾液;她產生一‧四毫升。她試著安慰我,「這並不代表你的唾液有多好,或我的唾液有多好。」
本文選自《大口一吞,然後呢?:深入最禁忌的消化道之旅》,天下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