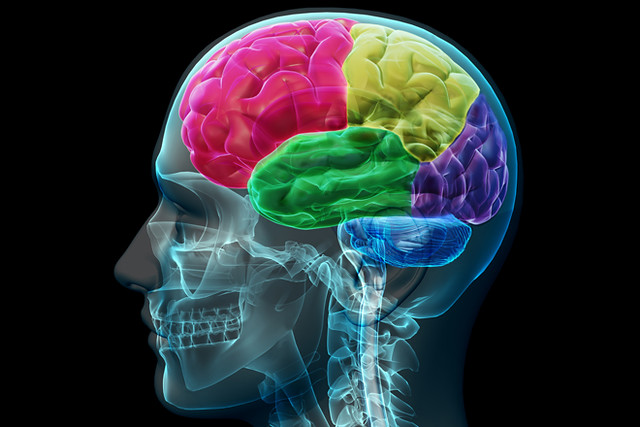難得有空抽手出來寫長文,再加上最近《我推的孩子》正紅,來聊聊最近這段時間一直很想講的擬社會互動(parasocial interaction)好了。(不過雖然講了這麼多,還是不足以涵蓋擬社會互動的所有面向跟相關議題,如果對此議題感興趣歡迎去找其他論文來看,或是在下面提問,我會盡可能回應)(倒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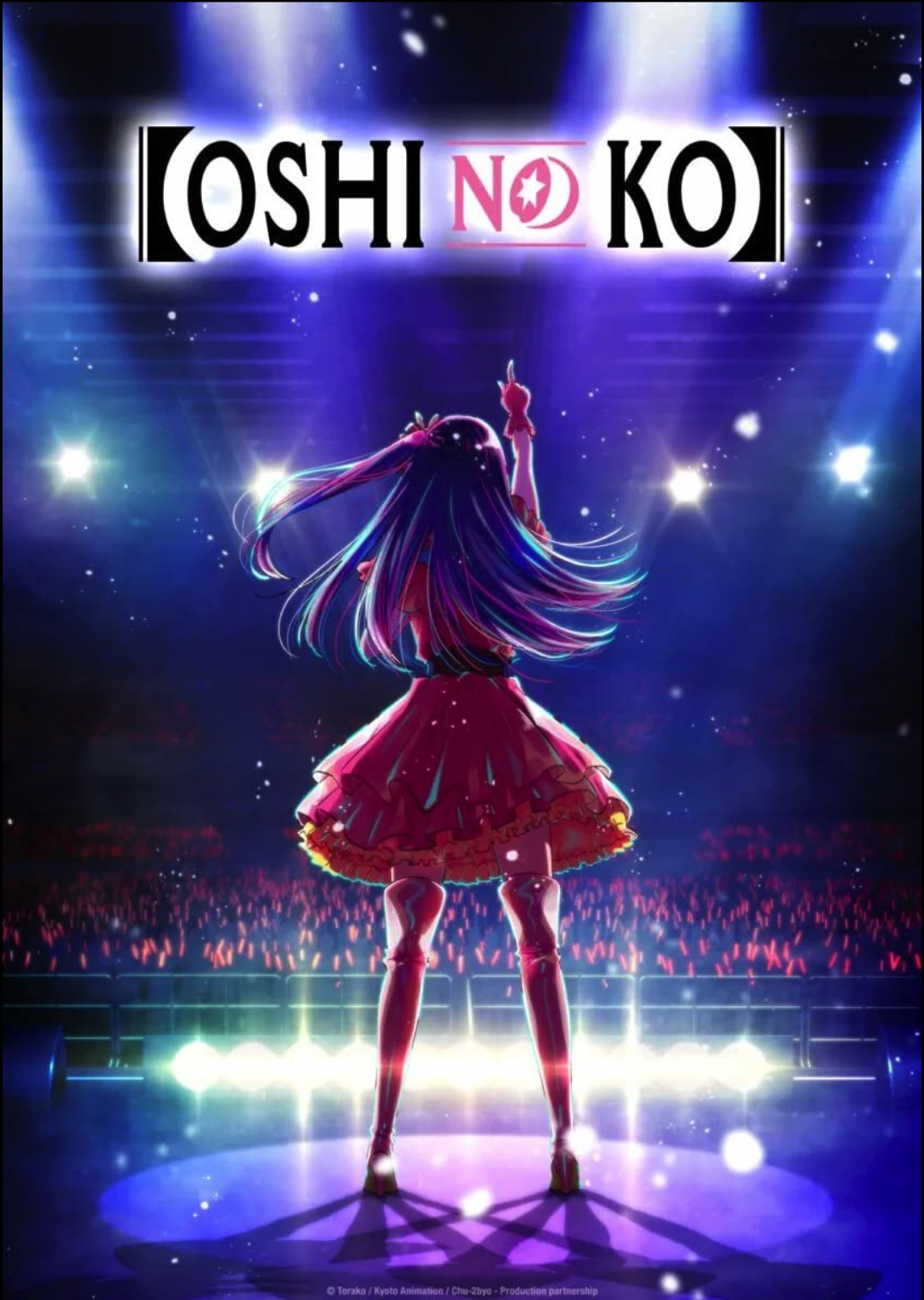
擬社會互動是什麼?
擬社會互動,是指某人透過某種媒介,在對方不知情的前提下建立的單向人際關係。
正常的人際關係,歸功於人際互動中的各種你來我往,讓參與者可以在有覺察(或未覺察)的情況下逐漸修正自己的行為,最終找到適合的平衡點。然而擬社會互動的本質是虛構的「擬態」、欠缺實際互動打底,其內涵完全取決於建立者的想像,很容易發生極端的偏差甚至是扭曲。
現在在討論擬社會互動時,最常舉的例子是網路紅人,包括 YouTuber、VTuber,以及其他在社群媒體上活躍的公眾人物。確實,網路世界的可觸及性大幅度擴張了擬社會互動發生的規模,個人資訊在無意間被洩漏、濫用的風險也在過去十年呈現指數級的飆升。
精心設計的「人物設定」
當受眾不再受制於實體線路與媒介,「紅人」們要面對的粉絲組成自然更複雜,導致雙方對這段關係的認知落差越來越嚴重。特別是當網紅的工作便是討好受眾時,單方面的不對等訊息,能潛移默化粉絲認知中的人際界線,讓他們覺得自己在某種程度上與這位網紅建立起情感連結——即便對那位網紅來說,他很可能只是在扮演「角色(persona)」,對一顆鏡頭、一行網路 ID 說話。
這也是擬社會互動的癥結點之一。當事人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投射情感的對象,很可能只是組精心捏塑、下班後就會跟灰姑娘禮服一樣消失不見的「人物設定」。
「畢竟是死忠的」 資訊不對等下的盲目心理
想當然,會有部分網紅(或其經紀公司)瞄準這個心理現象,利用擬社會互動,吸引死忠且願意付出實質資源的追隨者。例如幫後援會取親暱的綽號、透過(類)會員制的小圈圈分享私生活等。這些看似沒有特定指涉對象的粉絲回饋(當然還有更親近的互動,但那已非擬社會的範疇),其實都會助長擬社會互動,在粉絲心中種下虛妄的關係種子。

除了網紅產業,政治領袖也是受益於擬社會互動的群體(之一)。尤其是主打親民、大家長形象的政治人物,刻意塑造擬社會互動有助於昇華支持者的動機,從單純的理念或利益相符上升到更加私人的情感連結。一但支持者對政治人物產生家人般的親暱感,他們對於瑕疵的包容度也會提高,甚至陷入盲目的認知失調。
即便對方是真誠展現自我,不是在刻意討好受眾,不對等的問題依然存在。
如同演唱會時歌手對著舞台某處揮手,至少會有數十甚至數百人產生「我跟他對到眼了!他在跟我揮手」的錯覺。但歌手眼中,很可能只看見一片密密麻麻的黑點,連你頭髮的顏色都分辨不出來。
在聚光燈的照射下,每位觀眾都只是歌手眼中的「之一」,但歌手卻是每位觀眾眼中的「唯一」。
擬社會互動引發的社會問題
從這個比喻出發,不難看出擬社會互動確實有助於強化粉絲黏著度。但長遠來看,這個心理現象並不全然是優點,反而有不少潛在風險需要注意。
像《我推的孩子》裡面的危險瘋狂粉絲並不是想像出來的產物,而是當前人類社會真實存在的問題。因為當事人無法覺察到擬社會互動的存在,很難及時做出正確的應對,往往都得等到對方開始越界、侵犯到自己的私領域,才驚覺事態嚴重,卻已來不及阻止。

擬社會互動與明星們的自我揭露
拆解擬社會互動,這份單向的人際關係認知,有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不對等的自我揭露(self-disclosure)上。
這並不奇怪,自我揭露本就是人際關係的基礎,是互信關係的體現。我們願意對自己信任的人敞開心胸,同樣也會在被人傾訴時感受到自己「被需要」、「被信賴」的溫暖,進而建立起正向的迴圈,加深彼此的情感連結。
正是「距離」產生信任
但這理所當然的心理現象,有個尷尬的例外。出於奇妙的心理機制,比起半生不熟的點頭之交,人類更容易對僅是萍水相逢的人放下戒備。
大家可能都看過社群媒體或網路論壇莫名其妙變成告解室或團體治療空間,又或者你曾經對計程車司機或首次見面的酒保傾訴積壓在心裡、不敢讓身邊人發現的苦水。這既是一種健康的宣洩,也可能成為建立新關係的基石。
但這與其說是信任眼前的陌生人,倒不如說我們信任的是這份陌生感,以及它代表的「距離」。
因為相信彼此只會有這一次的相遇機會,分別之後繼續兩不相干,所以反而能把對方當成秘密樹洞,什麼東西都往裡面倒。這份「陌生」帶來的安全感是如此真實,讓它成為心理師能締結治療關係、引導個案打開心防的重要工具之一。

自我揭露 讓人誤解的熟悉感
但問題在於,對沒有對等認知的接收端(受眾)來說,這些自我揭露帶來的熟悉感很容易混淆他們的判斷。明明沒有真的見過面,卻知道對方的好惡、星座血型、休閒嗜好、時尚品味,甚至連深入許多的童年創傷跟過往戀情都能如數家珍,這些照理說只有熟識朋友才會了解的個人訊息,都是擬社會互動的基礎。
有趣的是,在相關心理學研究中,發現具有焦慮與矛盾型依附的人,特別容易對物理上未曾接觸過的人產生擬社會互動的依賴。
或許是擬社會互動欠缺實體交流、單向的本質,讓這些依附型有了可以放心透放不安全感的對象——畢竟,想像總是最美。就像蒙娜麗莎的微笑,明明他只是盯著前方的某塊虛空,卻讓每個觀畫者都覺得自己與之有了眼神交流,甚至迷戀起這份完美。
事情從此開始,會變得有些麻煩。
擬社會互動與情愛妄想
程度嚴重的擬社會互動,有可能發展成臨床診斷上的情愛妄想(erotomanic delusions),開始相信自己與擬社會互動的對象發展出不存在的親密關係。
不容易被人覺察的「妄想」
值得注意的是,在精神疾病的臨床診斷上幻想(fantasy)、幻覺(hallucination)與妄想(delusion)是不同的症狀。前兩者涉及經驗事實上不存在的刺激或想像,後者則是過度解讀或扭曲既存的瑣碎,最終得出與客觀現實有所出入的結論。
妄想必須有所依據(例如把超商店員的營業用笑容當成調情,又或者覺得鴿子都是政府派出來監視你的生化兵器),這也代表妄想者的「失現實感」,往往只會體現在與妄想對象有關的事物上,比明顯與現實脫節的幻覺或幻想症狀更難在第一時間被他人覺察,遑論獲得需要的幫助(甚至是外力介入)。
妄想引發的過激行為
畢竟在認為對方有精神疾病之前,一般大眾更傾向把妄想內容視為刻意為之的謊話,又或者是虛榮心作祟的自欺欺人。這些針對妄想的否定,可能刺激妄想者去證明妄想為真,進而做出對他人有危害的過激行為。

不只是情愛妄想,諸如被害妄想、嫉妒妄想,或是身體臆形妄想,都有惡化出自傷傷人的案例。
需要理解的是,妄想者不一定是帶著惡意去傷害他人,很多時候在他們的世界觀裡自己才是受害者,被客觀不存在的加害者逼著進行困獸之鬥。
以情愛妄想為例,當妄想者的「愛意」滿溢而出、不再受控,等待他們的往往是拒絕、排斥,還有赤裸裸的嫌惡與恐懼。這些與妄想不符的負面回應有可能一記暮鼓,把妄想者帶回現實;但若情況惡化,無法被捨棄的妄想,會迫使當事人合理化明顯與想像相悖的現實。至於如何合理化一個你深信與自己相愛的人,突然明確表達出對你的排斥,甚至宣稱根本不認識你?嗯,看一些社會新聞,應該能理解這樣的思考歷程有多危險。
惹出一堆麻煩的擬社會互動
講了這麼多關於擬社會互動的壞話(?),那要該怎麼避免擬社會互動呢?
真的,很難。
人類本就內建對自我揭露有情感反應的迴路,而自我揭露又是人類社會中不可避免的一環,這個微妙的因果關係又在資訊科技的一日千里下被無限制地放大,在我們還沒學會如何自處前,便先製造出各種各樣的麻煩。
老實說,擬社會互動根本不是現代的特產或文明病,只是建立起這類情感連結的人,有了更多手段去「實踐」他心中認定的關係,大幅度提升了潛在風險。
但就前面所提到的依附相關研究結果可以看出,大多情況下擬社會互動都不是一個「選擇」,而是自然發生的「現象」。當事人能力所及的,很可能只有事後覺察,然而這又回到老問題:當你意識到它的存在,它已經對你產生足夠顯著的影響或傷害了。
早期論述會把擬社會互動歸咎於現實生活中匱乏人際互動,但這點已被近代心理學研究駁斥。
個人認知的孤獨感與社會支持可能扮演催化劑的角色,但卻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強加因果關係反而會讓我們忽略其他重要變項。包括前面提到的依附型,還有成長過程中在社交場合經驗到的正向與負向刺激,都可能潛移默化人們對社交行為的期許與需求,進而驅使他們投向擬社會互動營造出來的舒適圈。

擬社會互動一定不好嗎?
近年來有些研究指出適量的擬社會互動,能為現實生活的離群分子提供一定程度的社會支持、社群凝聚力,甚至藉由效仿情感連結的對象而成長(當然也有負面的案例)。有些學者則認為擬社會互動是現代人適應網路生活的重要策略,與其排斥不如接受它、完善它。
然而不管是哪種論述,大多都有一個共識:適可而止。越界的擬社交互動,就跟任何其他社會互動一樣,只會造成別人的困擾喔。
本文亦刊載於作者 facebook 同名專頁。













-200x2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