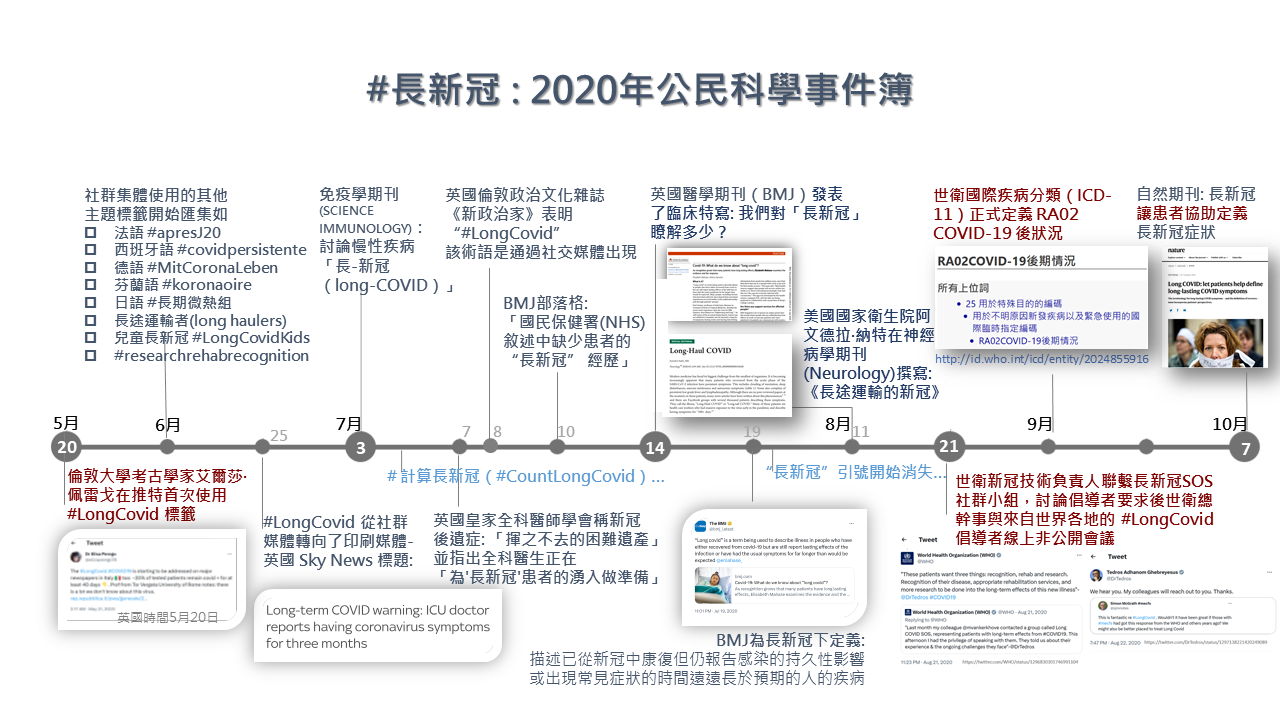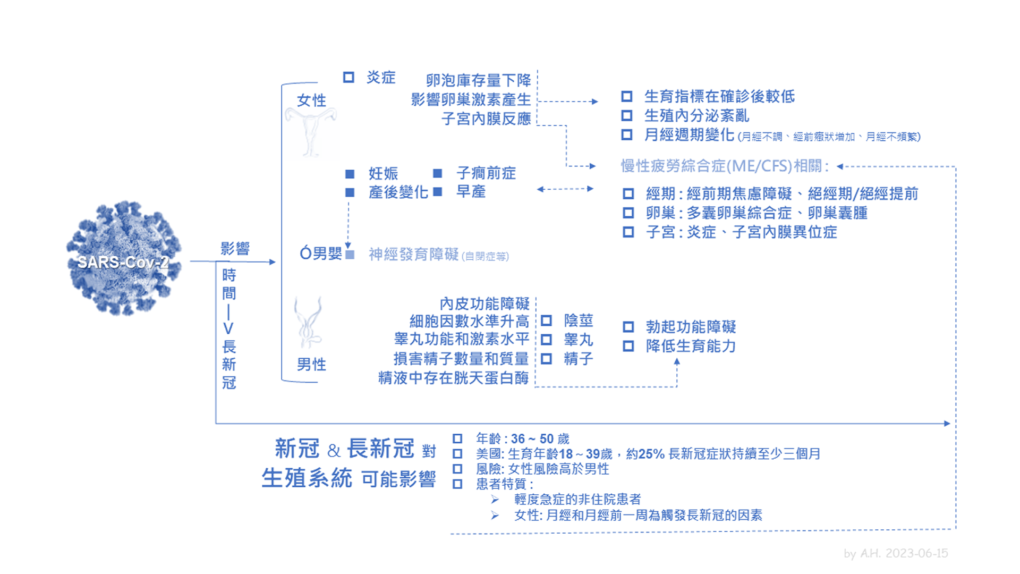這兩天最受矚目的一個新聞,是高端疫苗的二期試驗「解盲」,相信應該有不少人知道結果是好的,卻不見得太理解解盲,到底是解了什麼盲出來。
做實驗就做實驗,特別分成所謂的「安慰劑組」與「實驗組」,還有個「雙盲」(double-blind)實驗法,到底有什麼意義?
所謂的「安慰劑組」,是指沒有被施打任何疫苗、而是注射中性物質(例如生理食鹽水)的受試者。
這個過程中,會採用「雙盲」的設計,受試者與施打者在整個過程中都不會知道誰是誰,所有關於受試者所屬組別的資料都統一由知情的第三方保管,直到實驗結束才會公開、進行統計分析。

這樣在執行者與受試者都不知道誰是誰的狀況下完成實驗,便是過去幾天不斷在媒體上出現的「雙盲」法。
這個乍看之下有點反常識的設計法,其實有它的道理在。因為做臨床研究——特別是這種疫苗或新藥開發——有時最麻煩的,反而是受試者的「心」。
「安慰劑效應」假裝開藥病還真的好了?
惡名昭彰(?)的「安慰劑效應」(placebo effect)是指病人在相信自己接受了治療的情況下,因為心理狀態的正向變化,使得症狀減輕、甚至是痊癒。
用更直白的話,就是「我什麼都沒做,你怎麼就(從病房)出來了」。
安慰劑最常見的應用就是在一些小感冒上。過去有不少醫生為了應付只是輕微病症卻又要求藥物治療的患者,會用「胃藥」或「維他命」來假裝成所謂的「特效藥」,是真正意義上讓患者吃「心理健康」的。

這並不全然是逃避責任的作法,過去已經有許多研究發現,心理壓力會導致免疫系統失調,讓一些本來沒事的小病小痛惡化成棘手的狀況
特別是對那些打從心底「依賴」(也可以讀作ㄌㄢˋㄩㄥˋ)現代醫藥的患者來說,「得不到藥物治療」本身對醫病雙方來說都是不必要的壓力源,反倒不如開個對身體有益無害的東西吃吃,大家都開心多好(?)。
但就是這個「就算什麼都不做也會自己好」的可能性,讓安慰劑效應成為所有臨床研究者的惡夢。
安慰劑效應為什麼在臨床研究中這麼重要?因為這是「成效」的重要指標。
簡單做個加減計算。今天一個特效藥宣稱 A 疾病患者連續服藥 5 天後有 99% 的痊癒率,但如果你發現今天就算什麼都不做(安慰劑組)也會有 90% 的 A 疾病患者在 5 天後痊癒,那你還會覺得這個藥有其宣稱的效力嗎?
正因為在沒有反面對照的情況下,單看正面數據,很容易讓人高估藥品的效力,因此才會要求臨床研究必須做安慰劑的對照組,確保實驗結果是可信的。

所幸的是,安慰劑效應主要體現於現存症狀減輕,也就是免疫系統的正常運作上。在疫苗開發的試驗中,安慰劑效應是沒有辦法讓人「無中生有」出不應該存在的抗原抗體。
這也是為什麼你在高端解盲的數據中,安慰劑組的血清陽轉率(seroconversion rate)是 0,後續的中和抗體幾何平均效價(GMT titer)、以及GMT倍率比值(GMT ratio)更是直接不討論安慰劑組。
反過來說,要是安慰劑組驗出抗原,那反而會是一件很麻煩的事,因為要麼受試者在實驗過程中染疫、要麼是安慰組的分配有問題⋯⋯光想就覺得很可怕(抖)。
「打疫苗」的心理作用:我覺得不舒服,所以不舒服
說完影響效力的安慰劑效應,再來聊聊另一個讓大家很重視的部分——疫苗的副作用。
在高端疫苗的解盲中,有出現下列數據:
「全身性不良事件分析(所有事件,不區分等級),發燒比率:疫苗組為 0.7%,安慰劑組 0.4%;疲倦比率:疫苗組為 36.0%,安慰劑組 29.7%;肌肉痠痛比率:疫苗組為 27.6%,安慰劑組 16.6%;頭痛比率:疫苗組為 22.2%,安慰劑組為 20.0%;腹瀉比率:疫苗組為 15.1%,安慰劑組為 12.6%;噁心嘔吐感比率:疫苗組為 7.7%,安慰劑組為 6.7%。」

很多人看到這些數據之後,一方面慶幸高端疫苗的副作用發作比率不高,另一方面也開始自嘲台灣人到底有多過勞,不然沒打到疫苗的安慰劑組,怎麼出現身體不適的比例怎麼跟疫苗組那麼接近。
然而,這個「哈哈你看我們怎麼跟有打疫苗的人一樣慘」的說法其實是有失公允的。因為不管你相不相信,其實單單「相信自己被打了疫苗」真的就足以讓人產生上述那些難受的「副作用」了。

影集《怪醫豪斯》(House, M.D.)劇情充滿各式各樣的疑難雜症,第 3 季的第 18 集中,主角豪斯在搭飛機時發現機上出現發燒、嘔吐、起紅疹等症狀的病患。
這些症狀最初被懷疑是細菌型腦膜炎,結果在豪斯與夥伴爭論的過程中,周遭許多乘客也開始出現類似症狀,在短時間內變成可怕的大規模傳染。不只是乘客,最後就連跟豪斯的夥伴也出現被感染的症狀,形式越發嚴峻。
結果,在經過一系列的騷動後,豪斯發現最初被懷疑罹患腦膜炎症狀的乘客是因為前一天去玩了深度潛水,身體尚未從壓力急遽變化中恢復過來才產生這些症狀。待飛機在豪斯指示下降低高度、讓氣壓稍微恢復後,該名患者的症狀就有顯著改善。
換言之,打從一開始就沒有「大規模傳染」的問題。其他疑似被感染的患者都只是因為「聽到飛機上有__症狀的傳染病」以及「因為身邊的人開始嘔吐/起疹子/暈眩」而出現疑似染病症狀。

這個現象名為「群體心因性疾病」(mass psychogenic illness)。雖然被好萊塢簡化許多,但本質上它的確是指患者在沒有任何生理基礎,單純因為群體經受相似心理壓力而導致的類傳染病症狀。這可不是什麼獵奇的怪病,而是在過去百年間不斷有相關臨床證據出現、也引發不少研究熱潮的嚴重議題。
如果你曾經誤喝到感冒親友的水杯或飲料,並且在發現之後感覺自己喉嚨發癢、體溫開始升高。恭喜你,這就是心因性疾病的第一手經驗。
不需要實際被病菌感染,光是「覺得自己有病」就足以讓我們的身體產生不適反應,誤以為自己吃到髒東西(例如在飯碗裡看到蟑螂腳之類的)而反胃也是類似的機制。我們的身體並不是在對抗實際存在的入侵者,只要能冷靜下來讓「放羊的大腦」釐清錯誤訊息,症狀自然就會跟著趨緩。
將心因性疾病納入考慮後,再回來看前面關於疫苗副作用的數據,我們其實可以假設安慰劑組裡面應該有人事先知道他牌疫苗可能會有的副作用,因此在施打後因為心理預期出現了相應的心因性症狀。
當然,以嚴謹的雙盲實驗來說,實驗施行者是絕對不會事前告知受試者打了疫苗後可能會出現哪些症狀,但是問題在於台灣並不是在搶開發「第一支疫苗」。

早在高端開始二期之前,關於各廠疫苗的不同副作用早就廣為流傳,就算沒真的打過至少也讀過幾篇文章、知道基本會有哪些副作用。這些先入為主的認知,再加上「說不定我就是打到疫苗」的期待,讓安慰劑組的人出現心因性症狀也不足為奇。
雖然腰痠背痛、頭痛或腸躁症都是台灣人很普遍有的毛病,筆者我自己現在就因為長時間寫稿肩頸痠痛到爆炸(沒人在乎)。但是所謂「數據是死的」,我們看到的只是一個片面、概略的描述,當中實際的因果還會受到許多個體差異影響。
如發燒這種有明確診斷標準的症狀還好說,其他像是「肌肉痠痛」、「頭痛」或「噁心」、「腹瀉」等比較主觀的判定,每個人心中的衡量標準也不同。例如我現在到街上請人想像「滿分 10 分中 5 分的疼痛」,100 人很可能會給出 100 種舉例。
又或者像是臺南人說飲料「不甜」、四川人說菜「不辣」、俄羅斯人說酒「不烈」、日本人說拉麵「不鹹」,這通通都是刻板印象因為成長環境造成他們對於特定感覺的閾值變化,形成所謂的「耐受性」(tolerance)。
上述這些會影響資料收集準確性的變項都是不可抗力,也是我們把「人」當成實驗對象時必然會遇到的問題。
也正因為我們沒辦法專門培養一批嚴格控管生長環境、接觸刺激甚至是遺傳基因的「實驗用人類」,所以才得靠其他方法嚴格控制住所有能被控制的外部變項,避免已經有不少限制的研究出更多問題。
之所以「盲」,是為了更清楚地「看」
雙盲法作為一種實驗設計看起來很複雜,但是平心而論,它並不是為了找研究者麻煩而存在的。
相反的,雙盲法的存在目的其實是要「簡化」實驗程序。透過減少人為干擾的可能,讓研究者在分析數據時,能更有效率地將現有成果與目標變項連結在一起。

這裡也得拉回到今天的主軸:高端疫苗的解盲。
我知道大家都很關注高端疫苗的解盲,不管是滿心企盼又或者看戲唱衰的,我都希望在閱讀相關報告時,要有一個認知上的「保險」:
做研究這種事,打從一開始就沒有標準答案,只有最適合當下的最佳解法。
每種研究方法都有自己的利弊優缺,只有「適合」與「不適合」的差別,並不存在絕對的優劣。高端二期試驗採用雙盲法,因為那是在現有條件下能消除最多潛在干擾的設計,並非因為它是某種神奇的萬能仙丹,用進實驗裡就什麼都不用擔心了。
說白了,這世上本就不存在「完美」的對人實驗設計,因為「人」本身就是最大的外部變項。
之所以要雙盲,就是不想橫生變數,在已經有變因的前提下把其他部分做到最好。並不是為了讓大眾搞不清楚研究在做什麼、更不是在黑箱,而是唯有經過這樣的保密程序,才能去除不必要的雜質、呈現出我們現在看到的簡潔、具有可信度的報告。
參考文獻
- Clements, C. J. (2003). Mass psychogenic illness after vaccination. Drug Safety, 26(9), 599-604.
- Colligan, M. J., & Murphy, L. R. (1979). Mass psychogenic illness in organizations: An overview.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psychology, 52(2), 77-90.
- Harrington, A. (Ed.). (1999). The placebo effect: An interdisciplinary exploration (Vol. 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Kienle, G. S., & Kiene, H. (1997). The powerful placebo effect: fact or fiction?. Journal of clinical epidemiology, 50(12), 1311-1318.
- Kirsch, I., & Weixel, L. J. (1988). Double-blind versus deceptive administration of a placebo.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102(2), 319.
- Jones, T. F., Craig, A. S., Hoy, D., Gunter, E. W., Ashley, D. L., Barr, D. B., … & Schaffner, W. (2000). Mass psychogenic illness attributed to toxic exposure at a high school.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42(2), 96-100.
- Margraf, J., Ehlers, A., Roth, W. T., Clark, D. B., Sheikh, J., Agras, W. S., & Taylor, C. B. (1991). How” blind” are double-blind studie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9(1), 184.
- Moerman, D. E., & Jonas, W. B. (2002). Deconstructing the placebo effect and finding the meaning respo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