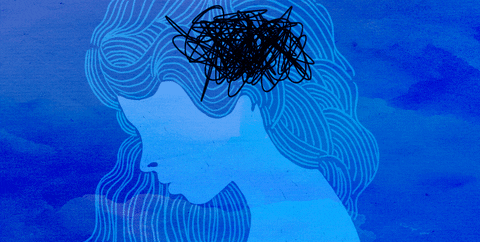- 文 / 雞湯來了特約作者 吳婕語
- 校稿 / 雞湯來了 陳世芃、張芷晴
- 製圖 / 雞湯來了 黃珮甄

「我不夠好,我不值得活。我不夠好。」——《靈魂急轉彎》22號靈魂
獲得金球獎「最佳動畫片」及「最佳原創音樂」2 大獎的電影《靈魂急轉彎》中,主角之一「22 號靈魂」一直不相信自己能找到在地球生活的火花,甚至在化身為黑色迷途精靈時不斷喃喃自語。
一直在投胎先修班的 22 號,受到許多偉人老師指導,不斷被批評、投以失望眼光……,表面上看起來毫不在意的 22 號,其實在不斷累積的人際挫折中,發展出消極的自我評價。
你或家人,是否也有長期被批評,久而久之就變得「很難相信自己」的狀況?其實,這可能是「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徵兆,長期受到他人攻擊,可能會累積巨大的心理陰影,有一天就成為被黑暗吞噬的小怪獸……
比 PTSD 容易被忽略的 C-PTSD:「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我經歷了千千萬萬的導師,大家都討厭我」——《靈魂急轉彎》22號靈魂
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Complex PTSD) 是一種於成長期間,受到創傷後出現的精神症狀,常發生於孩童身上,在身心狀況還在發展期間,因為應對負面事件的能力不及大人,所以常見於兒童,但成人也還是有可能發生。
就如電影中,22 號靈魂在各個人生先修班老師的教導下,備受批評而累積對自己的負面意象,雖然他嘴巴上不說,表現得完全不在意,其實他的內心是很受傷的[註1]。
值得注意的是,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TSD) 相比,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Complex PTSD),不須曾經暴露於死亡或身體威脅等重大傷害,且常發展於兒童期,人們不容易發現孩童內心累積的創傷陰影,或因「還小啦,會有什麼壓力」,因此容易被忽略。
在兒時若埋下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Complex PTSD) 的陰影創傷,可能會持續影響至個體成年之後,相關人際互動、自我概念等能力在成年之後,也很可能會比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者來得更差。
長期累積埋下的心理陰影-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 3 個常見徵兆
「我的人生毫無意義」、「我不要」、「放棄吧!我是不可能變好的」——《靈魂急轉彎》22號靈魂
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一樣,「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者回想起創傷事件,會引起如頭暈般的生理反應、自我毀滅及衝動行為、抱怨、迴避任何可能引起創傷回憶的情景、絕望、退縮、與他人的關係受損或失去信任、感受到威脅等等…狀況。
不過,特別的是,我們可以從「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中最關鍵的3個徵兆來檢視自己或身邊的家人有無相關情形:

|長期被否定陰影:
在難以脫離或是無法脫離的關係中,受到長期或重複的創傷,或者是連續不斷的創傷。例如:22 號靈魂不斷的失敗,只能在先修班裡循環。
|反覆經歷的噩夢:
不斷的經驗重現,反複經歷創傷,甚至可能會做惡夢。例如:22 號靈魂跟過許多靈魂導師,但最終都以失敗收場。
|偏差或討好行為:
出現不適當的行為,甚至過度討好他人。 例如:22 靈魂在導師面前大鬧、打亂,出現看似小孩不乖的調皮舉動。
放寬心,試試專業的諮詢
每個人在生活中遇到情緒低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持續時間太長,並且可能影響到人際關係、學業、職業上的功能損傷,建議尋求專業的協助。
WHO 在國際疾病分類第十一版的版本中已經發展出符合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國際創傷問卷 (ITQ) 量表,供全球臨床工作者使用,可以有效的幫助我們面對童年時期所累積的創傷。
直接到地球試一試——停下來,等一等靈魂
「我想我找到自己的火花了」-《靈魂急轉彎》22號靈魂
原本對於地球感到厭惡的 22 號靈魂,在真正接觸到自己討厭的東西,暴露於地球當中,他開始有了不一樣的經驗,品嘗到人類的食物,居然很美味、和人談話時原來有人認同他,原來自己可以在地球中,學習到新的生活方式,原來我不討厭地球。

22 號靈魂在地球生活的做法,其實就是心理學中「漸進暴露式療法」的概念:慢慢面對痛苦的來源,從最低痛苦程度的開始,有相關證據顯示,治療「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和治療「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相同。
|直接面對嘗試:
在治療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時,常使用的是暴露式療法,讓個人「直接面對創傷的壓力源」,學習如何發展出新的應對模式,很可能可以減輕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出現的「負面的自我概念」及「人際關係障礙」。
|練習角色扮演:
正因「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出現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人際應對能力的不足,導致情感出現缺損」,所以,若能在情境中「練習角色扮演」,也許能習得在社會中與他人相處的技巧。
|正向互動技巧:
在上述角色扮演的過程中,慢慢習得調節自我情緒的技巧、和他人或這個世界正向互動的技巧,增加「正向的人際關係經驗」,或就像 22 號一樣,誤入了別人的身體,但也因此暴露其中,扭轉了對地球的負向想法,體驗到與人之間新的連接,學習建立「好」的相處。
若是身邊有人出現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症狀(無論是孩子或大人),家人的支持也可以提供一個很好的幫助。在治療期間,可以一起學習如何面對創傷,提供對方情感支持。深為受創傷者身邊的重要他人,若在處理創傷時能夠勇於面對,對於治療效果,會優於讓對方自己面對治療。「陪伴」與「引導」,將是不容小覷的力量。
註解
- 根據 WHO 的定義:當面對一種壓力事件時,最常見於兒童在成長期間內,不斷的累積創傷且重複的面臨創傷經驗,童年時期的虐待及情感忽視為最典型的創傷模式。
參考資料
- 國際疾病分類第十一版(2019)。資料取自 https://icd.who.int/en
本文轉載 雞湯來了 ,原文連結:一直覺得自己都不夠好?-長期被否定下的「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歡迎去 雞湯來了 繞繞玩玩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