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只是你的問題,然而這問題可能影響法庭的判決。英國格拉司哥大學(Glasgow University)的Roberto Caldara研究團隊利用腦電波儀(EEG)對高加索白人與東亞的亞洲人進行實驗[英],證明這種認知症狀普遍存在,但他也強調,只要常常與其他種族的人相處就能辨識得更好。而這項實驗結果也讓法院未來有可能採用腦電波來判斷證人對被告的指證是否有效力。
本文與 PAMO車禍線上律師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走在台灣的街頭,你是否發現馬路變得越來越「急躁」?滿街穿梭的外送員、分秒必爭的多元計程車,為了拚單量與獎金,每個人都在跟時間賽跑 。與此同時,拜經濟發展所賜,路上的豪車也變多了 。
這場關於速度與金錢的博弈,讓車禍不再只是一場意外,更是一場複雜的經濟算計。PAMO 車禍線上律師施尚宏律師在接受《思想實驗室 video podcast》訪談時指出,我們正處於一個交通生態的轉折點,當「把車當生財工具」的職業駕駛,撞上了「將車視為珍貴資產」的豪車車主,傳統的理賠邏輯往往會失靈 。
在「停工即停薪」(有跑才有錢,沒跑就沒收入)的零工經濟時代,如果運氣不好遇上車禍,我們該如何證明自己的時間價值?又該如何在保險無法覆蓋的灰色地帶中全身而退?

薪資證明的難題:零工經濟者的「隱形損失」
過去處理車禍理賠,邏輯相對單純:拿出公司的薪資單或扣繳憑單,計算這幾個月的平均薪資,就能算出因傷停工的「薪資損失」。
但在零工經濟時代,這套邏輯卡關了!施尚宏律師指出,許多外送員、自由接案者或是工地打工者,他們的收入往往是領現金,或者分散在多個不同的 App 平台中 。更麻煩的是,零工經濟的特性是「高度變動」,上個月可能拚了 7 萬,這個月休息可能只有 0 元,導致「平均收入」難以定義 。
這時候,律師的角色就不只是法條的背誦者,更像是一名「翻譯」。
施律師解釋「PAMO車禍線上律師的工作是把外送員口中零散的『跑單損失』,轉譯成法官或保險公司聽得懂的法律語言。」 這包括將不同平台(如 Uber、台灣大車隊)的流水帳整合,或是找出過往的接單紀錄來證明當事人的「勞動能力」。即使當下沒有收入(例如學生開學期間),只要能證明過往的接單能力與紀錄,在談判桌上就有籌碼要求合理的「勞動力減損賠償 」。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你的直覺,正在害死你
根據警政署統計,台灣交通違規的第一名常年是「違規停車」,一年可以開出約 300 萬張罰單 。這龐大的數字背後,藏著兩個台灣駕駛人最容易誤判的「直覺陷阱」。
陷阱 A:我在紅線違停,人還在車上,沒撞到也要負責? 許多人認為:「我人就在車上,車子也沒動,甚至是熄火狀態。結果一台機車為了閃避我,自己操作不當摔倒了,這關我什麼事?」
施律師警告,這是一個致命的陷阱。「人在車上」或「車子沒動」在法律上並不是免死金牌 。法律看重的是「因果關係」。只要你的違停行為阻礙了視線或壓縮了車道,導致後方車輛必須閃避而發生事故,你就可能必須背負民事賠償責任,甚至揹上「過失傷害」的刑責 。
數據會說話: 台灣每年約有 700 件車禍是直接因違規停車導致的 。這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心態,其巨大的代價可能是人命。
陷阱 B:變換車道沒擦撞,對方自己嚇到摔車也算我的? 另一個常年霸榜的肇事原因是「變換車道不當」 。如果你切換車道時,後方騎士因為嚇到而摔車,但你感覺車身「沒震動、沒碰撞」,能不能直接開走?
答案是:絕對不行。
施律師強調,車禍不以「碰撞」為前提 。只要你的駕駛行為與對方的事故有因果關係,你若直接離開現場,在法律上就構成了「肇事逃逸」。這是一條公訴罪,後果遠比你想像的嚴重。正確的做法永遠是:停下來報警,釐清責任,並保留行車記錄器自保 。

保險不夠賠?豪車時代的「超額算計」
另一個現代駕駛的惡夢,是撞到豪車。這不僅是因為修車費貴,更因為衍生出的「代步費用」驚人。
施律師舉例,過去撞到車,只要把車修好就沒事。但現在如果撞到一台 BMW 320,車主可能會主張修車的 8 天期間,他需要租一台同等級的 BMW 320 來代步 。以一天租金 4000 元計算,光是代步費就多了 3 萬多塊 。這時候,一般人會發現「全險」竟然不夠用。為什麼?
因為保險公司承擔的是「合理的賠償責任」,他們有內部的數據庫,只願意賠償一般行情的修車費或代步費 。但對方車主可能不這麼想,為了拿到這筆額外的錢,對方可能會採取「以刑逼民」的策略:提告過失傷害,利用刑事訴訟的壓力(背上前科的恐懼),迫使你自掏腰包補足保險公司不願賠償的差額 。
這就是為什麼在全險之外,駕駛人仍需要懂得談判策略,或考慮尋求律師協助,在保險公司與對方的漫天喊價之間,找到一個停損點 。
談判桌的最佳姿態:「溫柔而堅定」最有效?
除了有單據的財損,車禍中最難談判的往往是「精神慰撫金」。施律師直言,這在法律上沒有公式,甚至有點像「開獎」,高度依賴法官的自由心證 。
雖然保險公司內部有一套簡單的算法(例如醫療費用的 2 到 5 倍),但到了法院,法官會考量雙方的社會地位、傷勢嚴重程度 。在缺乏標準公式的情況下,正確的「態度」能幫您起到加分效果。
施律師建議,在談判桌上最好的姿態是「溫柔而堅定」。有些人會試圖「扮窮」或「裝兇」,這通常會有反效果。特別是面對看過無數案件的保險理賠員,裝兇只會讓對方心裡想著:「進了法院我保證你一毛都拿不到,準備看你笑話」。
相反地,如果你能客氣地溝通,但手中握有完整的接單紀錄、醫療單據,清楚知道自己的底線與權益,這種「堅定」反而能讓談判對手買單,甚至在證明不足的情況下(如外送員的開學期間收入),更願意採信你的主張 。
車禍不只是一場意外,它是認知、情緒、金錢與法律邏輯的總和 。
在這個交通環境日益複雜的時代,無論你是為了生計奔波的職業駕駛,還是天天上路的通勤族,光靠保險或許已經不夠。大部分的車禍其實都是小案子,可能只是賠償 2000 元的輕微擦撞,或是責任不明的糾紛。為了這點錢,要花幾萬塊請律師打官司絕對「不划算」。但當事人往往會因為資訊落差,恐懼於「會不會被告肇逃?」、「會不會留案底?」、「賠償多少才合理?」而整夜睡不著覺 。
PAMO看準了這個「焦慮商機」, 推出了一種顛覆傳統的解決方案——「年費 1200 元的訂閱制法律服務 」。
這就像是「法律界的 Netflix」或「汽車強制險」的概念。PAMO 的核心邏輯不是「代打」,而是「賦能」。不同於傳統律師收費高昂,PAMO 提倡的是「大腦武裝」,當車禍發生時,線上律師團提供策略,教你怎麼做筆錄、怎麼蒐證、怎麼判斷對方開價合不合理等。
施律師表示,他們的目標是讓客戶在面對不確定的風險時,背後有個軍師,能安心地睡個好覺 。平時保留好收入證明、發生事故時懂得不亂說話、與各方談判時掌握對應策略 。

從違停的陷阱到訂閱制的解方,我們正處於交通與法律的轉型期。未來,挑戰將更加嚴峻。
當 AI 與自駕車(Level 4/5)真正上路,一旦發生事故,責任主體將從「駕駛人」轉向「車廠」或「演算法系統」 。屆時,誰該負責?怎麼舉證?
但在那天來臨之前,面對馬路上的豪車、零工騎士與法律陷阱,你選擇相信運氣,還是相信策略? 先「武裝好自己的大腦」,或許才是現代駕駛人最明智的保險。
PAMO車禍線上律師官網:https://pse.is/8juv6k
發表意見

討論功能關閉中。
高智商成績分數可以用買的!?
當時,在布洛瓦郡鑑別資優生的程序在一、二年級時展開。如果老師判斷一個孩童可能有資格參加資優課程,就會轉介孩子去學校心理師那裡作一個測驗。家長也可以聘請私人心理師來進行測驗。凡是被測出智商在一百三十以上的孩童就會被評估納入資優課程。由於幼年貧困和英語能力有限已經被證明會影響標準化測驗的成績,低收入戶學生以及英語非母語的學生被判定為資優生的門檻比較低,是一百一十五。
可是該郡學生的智商分數看起來很怪。分數並非正常分布,而是在一百二十九分時人數歸零,然後在一百三十分時(亦即被認定為資優的最低門檻)人數驟然升高。而且沒有一個孩子拿到不達門檻的一百二十九分。
後來分析這些數據的經濟學家蘿拉.朱里安諾(Laura Giuliano)帶著冷冷的幽默感告訴我:「高智商分數似乎是有市場的。」私人心理師表面上是被聘請來評估孩子,可是以每次幾百美元的價格,他們實際上是被雇來確保孩子被認定為資優。朱里安諾告訴我,當她自己的孩子接近入學年齡,其他的家長低聲告訴她哪些心理師是「好的」。「好」似乎意味著掌握了「發現」智商一三〇的技巧。
這種買來的智商是理解這種差距的一條線索:大多是白人的富有家長基本上是替子女買到資優生的名額。但是這仍舊無法解釋黑人孩童和拉美裔孩童、英語非母語的孩童、低收入戶孩童被鑑別為資優的人數何以如此之少。就算富有的白人小孩被鑑別為資優的人數超出正常比例,這也不該壓低其他孩童被鑑別為資優的人數。

辨別資優生的新作法——剔除老師和家長的推薦制度
帕克懷疑篩選過程的第一步可能有問題,亦即當老師和家長推薦學生去作測驗。於是在二○○三年十一月,她把那張地圖展示給學校董事會看,並且提出了一種鑑別資優生的新做法。帕克說,關於誰該接受測驗,布洛瓦郡不該仰賴任何人的個別判斷。該郡應該對每一個孩子進行篩選。面對那張凸顯出不平等的閃亮紅色地圖,學校董事會一致投票贊成。
二○○五年,布洛瓦郡展開了全面篩選。員工得到加班費,加班對該郡兩萬名二年級學生進行測驗。由於眾所周知智商測驗和其他標準化測驗都含有偏見,所選用的測驗是一種非語言的認知測驗,把這種風險降到最低。該測驗不依靠與任何特定文化有關的文字或圖像,而是測量解決問題的綜合能力。
在學生作過測驗之後,帕克的團隊就親手把用葡萄牙文、西班牙文和海地克里奧爾語寫成的家長同意書送到每個學校,讓家長能夠同意接下來的步驟。他們有技巧地回答家長的來電,那些家長擔心這張有關「特殊學生」的書面通知乃是表示孩子有行為問題。團隊成員要他們放心,說事情正好相反,說這是個好消息。
等到篩選程序完成,結果很驚人。在全面進行篩選之後,黑人孩童和拉美裔孩童被認定為資優的人數增加為三倍。在接下來那一年裡,有資格參加資優課程的另外數百名孩童中,有八成來自低收入戶或是英語非母語的學生。這些學生當中有許多人的分數明顯高出門檻,這表示即使是資賦特別優異的孩子從前也被排除在資優課程之外。
問題不在於這些孩子的資賦不優異,而在於沒有人費心去把他們找出來。

改變篩選制度與教育環境——不同種族間的成績差距就消失了
改變不僅止於此。布洛瓦郡規定:只要學校裡有資優兒童,哪怕只有一個,該校就必須替這名學生設立一間特殊的「高成就學生教室」,配備有受過特殊訓練的教師和更進階的課程。然後這間教室就會把分數接近門檻的那些學生也收進去──例如,某個年級有四名資優生,而一間「高成就學生教室」可以容納二十四名學生,就表示分數緊跟在後的二十名學生也可以在這間教室學習。
於是這些學生就也能從更快的步調、更豐富的課外活動、更高的教師期望和同儕支持中獲益。朱里安諾及其同事大衛.卡爾德(David Card)發現:在這種特殊教室學習的黑人和拉美裔「高成就學生」在數學和閱讀的成績大幅提升。在被安排進入這些教室之前,這些學生的數學和閱讀成績比不上智商相同的白人學生。在那之後,這個差距消失了。
這些學生當中有更多人變得有資格繼續參加步調加速的課程,使他們走上新的學習道路。事實上,黑人和拉美裔學生的整體數據情況都有了改變。事實證明,在進行普遍篩選之前,這些學生不僅比較不可能被篩選為資優,而且更可能被篩選出有學習障礙。而這種加強篩選反映在智商分數的整體分布上。在進行普遍篩選之後,黑人和拉美裔學生的分數分布圖和白人學生的分數分布圖變得一致。

——本文摘自《隱性偏見》,2022 年 10 月,平安文化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發表意見

隱性偏見的概念指出偏見起作用的方式就像電路。這個電路始於我們從周圍世界吸收「文化知識」,當家人、媒體、課堂、鄰居給予我們有關不同群體的大量資訊。
這些知識當中有些是真實的,例如,從統計數字來看,男性和女性的平均身高的確有差異。有些知識則並不為真:平均而言,男孩的數學成績並不優於女孩。隨著時間,這些訊息變成深埋在我們腦中的聯想和刻板印象。
當我們遇見觸發了這些聯想的某個人或某件事,我們的文化知識就會影響我們對當下情況的反應,包括我們會有什麼行動,會說些什麼,以及會有什麼感受。因此而出現的歧視行為會助長差異,而差異又會進一步餵養引發這整個過程的文化知識。而且我們每一次所看見的並非單一層面的身分,而是多重類別的身分,包括種族、性別、年齡以及其他,每一種身分都帶有可能被融入感知者腦中的聯想。
把隱性偏見視為一種電路,這個概念有助於解釋許多遭遇。
黑人學生在學校所受到的差別待遇
以小男孩小傑.鮑威爾(JJ Powell)為例。四歲時,小傑聰明而且合群。他能熟練地寫出自己和弟弟的名字,喜歡玩上學的遊戲,通常行為良好。可是他在家鄉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市去上幼稚園的第一年春天,他母親圖妮特.鮑威爾(Tunette Powell)開始接到電話,要她去接小傑回家。他因為把口水滴在同學身上而被停學。另一次是因為他扔了一張椅子,還有一次則是在午睡時間不聽話。鮑威爾感到不解。她那個優秀、樂觀的兒子?「哇!」在一次訪談中她回憶說,「我是個失敗的家長。」
可是後來她參加了小傑班上一個同學的生日會,開始和幼稚園的其他家長交談。有一個母親說她兒子狠狠地打了一個男孩,對方因此進了醫院。她的兒子並沒有被停學,她就只接到了一通電話。更多的家長說起自家小孩的行為問題。並沒有其他小孩被停學。事實上,其他的家長甚至不知道學校會使用這種懲罰。小傑被停學了三次。就鮑威爾所知,唯一的差別在於她的小孩是黑人,而其餘的小孩是白人。

鮑威爾的兒子不是特例。德州的一項研究檢視了幾百萬份的學校成績單和懲戒紀錄,其中有每一個在二○○○年至二○○二年之間開始就讀七年級的學生一直到十二年級的在校紀錄。這些紀錄包括所有違反行為規範(例如遲到或是服裝不整)的懲戒處分。校方可以自由裁量針對這些違紀行為的反應,可以做出校方認為適當的任何處罰。這項研究發現,黑人學生在第一次犯規時就被罰停學的可能性超過兩倍。
多項研究證實了此一模式。在心理學家菲利普.阿提巴.戈夫(Phillip Atiba Goff)及其同事所進行的一組研究中,受試者得知一個男孩的故事,這個男孩有反社會的行為,範圍從輕罪到重罪。接著受試者被問了一些問題,關於這個孩子的行為責任,以及在他行為背後的意圖。
在評估同樣的行為時,如果這個男孩是黑人,受試者就認為他更應該為他的行為受到責備;他們也高估了他的年紀,多達四歲以上,例如一個十三歲半的男孩被認為是個成年人。比起一樁輕罪,黑人小孩被視為更應該為一樁重罪受到責備;對白人小孩來說,情況則正好相反:當他行為的嚴重性增加,白人小孩被認為所需負的責任更小。
在另一項研究中,研究者把一名行為不檢的學生的在校紀錄拿給幾位老師看。如果那個學生是黑人,那些老師就更可能替這名學生貼上「惹是生非者」的標籤,而且更可能把第二次違規視為一種更嚴重的不良行為模式的一部分。
按照隱性偏見的概念,小傑的老師吸收了帶有種族歧視的有關黑人兒童的刻板印象。當小傑拒絕午睡,她腦中的刻板印象影響了她對他和他的行為的解讀,使得她把這種行為看得比白人小孩的同等行為更嚴重,而把小傑視為更應該受到懲罰。
隱性偏見塑成某些族群的刻板印象
在一個名叫郭伽(Philip Guo)的年輕計算機科學學生身上,有偏見的待遇對他有利。郭伽成長於一個華裔美國家庭,家人都主修人文科學。他在六年級時嘗試自學BASIC程式語言,但因為太難而放棄。後來,他在中學修了一門計算機科學課,那門課的老師在開課前幾週才學了教材。
這激發了他對撰寫程式的興趣,可是當他在二○○一年上了大學,他基本上是個初學者,尤其是相對於他的同學而言,他的許多同學在大一時就已經擁有十年撰寫程式的經驗。他修了入門的計算機科學課程,開始做暑期實習,這時他注意到一件不尋常的事。他回憶說:「在開會時,別人似乎總是假定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其實他並不知道。當他因為感到茫然而沉默,同事以為他沉默是因為他懂了。
在學年當中,郭伽冒昧地寫電郵給教授,得到了一個研究職位。在接下來那幾年裡,他得到了一個又一個的工作,而他知道自己其實尚未擁有這些工作所需要的技能。在這些工作上,他有機會習得知識,同時還獲得報酬,一直受益於別人對於他專業能力的假定。他回憶:「技術水準與我相似的其他人並未得到我所得到的鼓勵。」
郭伽的主管可能吸收了一種刻板印象,把他那種背景的人和技術專業能力連結在一起。當他們看見他在苦思一個問題,這些刻板印象就在他們腦中跳出來,影響了他們對他的所言所行、他的疑問乃至他的沉默的解讀。郭伽的經驗凸顯出偏見的一個重要面向:偏見不僅會在某些情況下造成不利條件,也會在另一些情況下創造出優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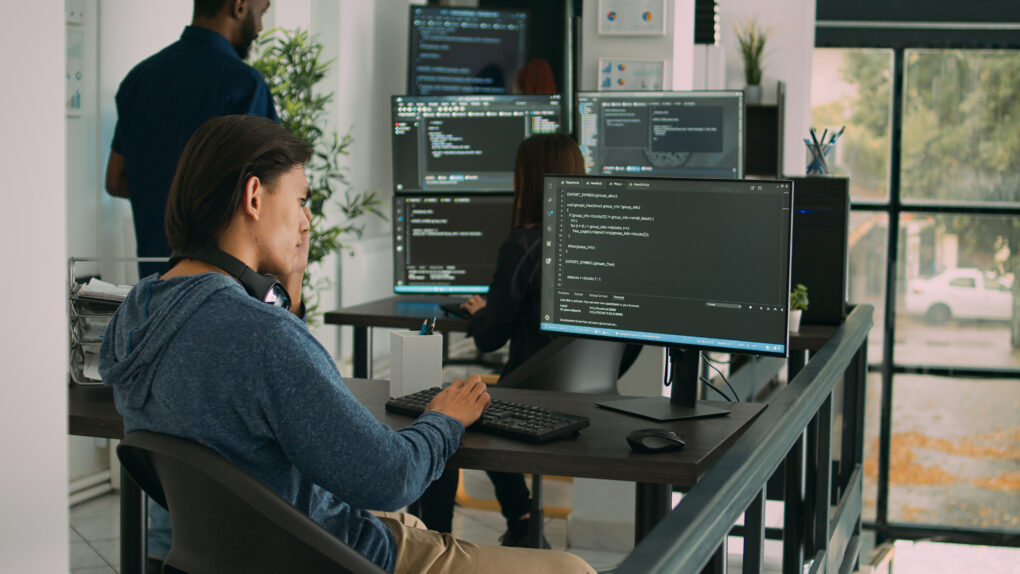
同一個群體可以受到有利於他們之刻板印象的影響,也受到有害於他們之刻板印象的影響,有時候甚至是同一種刻板印象。例如,亞裔美國人給人的「模範少數族裔」刻板印象掩蓋了諸如騷擾、種族歧視、貧窮、暴力和歧視的種種難題;這種刻板印象暗示出並不存在的同質性。
在學校裡,它掩蓋了學生對於資源與支持的需求。而且它無法保護人們不受到剝奪人性的待遇:一項針對哈佛大學入學申請紀錄的分析甚至表示亞裔申請人經常在「個性」這一項的評估中得分較低。
對生物學家本.巴雷斯來說,這個偏見迴路在他變性之前與之後發揮了不同的功能。在變性之前,別人透過對女性之刻板印象的鏡片來看待他,認為女性的科學能力比較差。這種刻板印象影響了同事對他的工作與言行的看法。
他們認為他比較缺少權威、才華和價值,於是以打斷他、質疑他、否定他的專業能力作為回應。在變性之後,巴雷斯有了相反的經驗:他被視為更有能力、更有知識、更有權威,而且比較不適合被打斷。假如巴雷斯是屬於另一個種族或族裔的科學家,或是有某種身心障礙,他在變性前後的經驗就會有所不同。

——本文摘自《隱性偏見》,2022 年 10 月,平安文化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