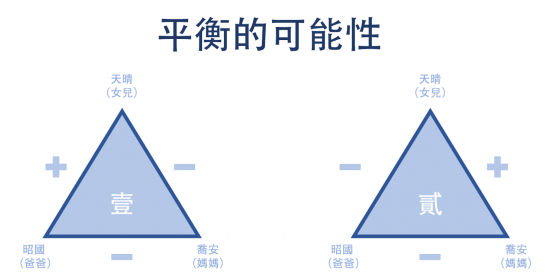- 編按:公共電視、CATCHPLAY與HBO Asia共同推出的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播出後掀起了如火如荼的討論。從無差別殺人事件展開了一系列關於加害者、被害者、加害者家屬以及被害者家屬,還有媒體以及輿論的探討,讓我們能從更多維度的面向去思考這樣的悲劇之後仍未解的那些事。
關於道德及是非對錯,很難有標準答案,戲裡是這樣、在戲外更是如此;而在這兩篇文章當中,作者試圖透過其他的事件以及書籍文本去探討無差別殺人事件被好的成因,以及他們的家庭。若有任何想法,也都歡迎跟我們一起討論。 - 從《我們與惡的距離》看無差別殺人(1):撕裂了無數家庭的事件,卻找不到關鍵的成因?
「我一天睡不到兩小時,我一直在想,到底是我哪裡把小孩教壞了?……是因為我們太自私、太忙碌,都沒時間跟孩子聊天,所以才會教出這種變態殺人魔?……全天下沒有一個爸爸媽媽,要花 20 年去養一個殺人犯!」──《我們與惡的距離》

對於《我們與惡的距離》當中的這段話,至今依然讓我歷歷在目。
每當重大犯罪發生後,社會輿論究責的對象,往往是他們的父母。這種「養不教,父(母)之過」的言論,並不是只有出現在儒家文化的社會裡。早在 1999 年科倫拜(Columbine) 無差別殺人事件發生時,兇手的家庭便曾遭遇過嚴厲的攻擊。
為什麼要譴責加害者家屬?
我們想要相信犯罪是由父母一手造成,如此一來,我們就能安慰自己,因為我們有好好教孩子,所以自個兒家不會遭殃。我之所以知道有此謬見,是因為我也曾這麼想。
——安德魯·所羅門(Andrew Solomon),《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推薦序
正如同這段推薦序所說的,一個人之所以會譴責他人的教養,乃是源自於害怕。正因為自己害怕自己也教出一個殺人魔,於是緊抓著公平世界假說不放。1於是恣意妄為地攻擊加害者家屬,對他們發黑函、對他們丟雞蛋。然而,當我們在做這些事情,把我們與他們做分隔時,我不禁想問,我們與惡的距離,到底有多遠?
2014年,秋葉原殺人事件發生的六年後,兇手的弟弟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母親因罪惡感崩潰住院,父親則離職隱居。其弟在自殺的前一周,將六年的日記手札寄給周刊,裡面提到了「加害人的家屬,只能在陰暗的角落悄悄生活,不能擁有和一般人一樣的幸福。」同時因為事件後因為記者一直上門,被迫不斷搬家換工作,原本論及婚嫁的女友也因此離開他。
無解的難題:沒有人知道這些家庭的家庭教育,哪裡出了問題?
如果真的要細究這些家庭的教育有沒有出了什麼問題,結果可能會讓你吃驚。因為事實上,如果你從頭到尾完整的讀過《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就會發現,他們的家庭,與我們的家庭無異。不過值得警惕的卻是,正因為一般人都是這樣過生活的,所以我們才沒能有機會抓住那些我們很可能遺落的小細節,進而使我們沒能有機會阻止悲劇的發生2。
在《教出殺人犯》一書中,李茂生在書序當中提到了:當我們聽到少年說「我絕對不會再犯」時,必須戒慎恐懼,因為這句話,代表其仍舊無法對他人敞開心胸,仍在自我壓抑;反倒是少年說出「我不知道將來會怎樣,你能協助我嗎」的時候,這才是成功的第一步。
而在《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當中,蘇也提到了,在血案發生的一年前,他的孩子與另一位結伴一起行兇的孩子,曾在一年前因竊盜而被逮捕。當時的她,要求孩子要避免再犯、要減少與對方的聯繫。就我看來,換做是其他的父母,也會這麼做的,對吧?這就是一般家庭會發生的狀況。然而,這樣做真的有效嗎?
張立人醫生在該書的推薦序當中寫道:
如果你想在這本書中,尋找狄倫母親如何「教子無方」的大量證據,你將感到失望。因為,狄倫的母親本身就從事心理輔導工作,在教養上更是一位「夠好的媽媽(good enough mother)」,給予狄倫充足的愛,卻不致於溺愛。
犯罪的發生,源於過度壓抑?
《教出殺人犯》的作者岡本茂樹在書中提醒我們,一場犯罪之所以會發生,其實常常是過度壓抑的結果。他舉了自己常會在國高中現場觀察到的例子3:
甲生與乙生都是時常面帶開朗笑容的孩子,但家庭背景卻大相逕庭。甲的家庭中父母關係良好,家庭對他來說是個安全的避風港;乙的家庭卻恰恰相反,父母感情不好、爭執不斷,正因為家裡氣氛低迷,乙總是努力表現得開朗,希望能緩和家中氣氛。她總是責怪自己「都是因為我不好,爸媽才會整天吵架」,同時也擔心「萬一爸爸媽媽不在一起了怎麼辦?」乙的心理是痛苦的,但不敢將痛苦掛在嘴上,「要努力讓家裡氣氛和諧一點」、「只要爸爸媽媽感情好,就不會把我丟掉。」
而其他大人看到笑容開朗的孩子,只會根據外在表現稱讚:「真是個愛笑的好孩子。」但這句稱讚,卻帶給甲生和乙生完全不同的訊息,對甲而言,這句稱讚是令人開心的,今後他自然也會成為一個總是面帶開朗笑容的女孩,甲生是一個真正的好孩子;但對於乙而言,這句稱讚給他的訊息是,要更壓抑自己的痛苦,千萬不能忘記當一個面帶笑容、活潑開朗的孩子。乙生會毫不猶豫地更加壓抑自己的情緒,而這句稱讚強化了他的行為。
如此一來,乙生只剩下兩條路──持續扮演好孩子,或者筋疲力竭放棄扮演好孩子。放棄的方式有很多,有可能用誤入歧途的方式表現出來,最後演變成犯罪;也有可能是完全失去精力,透過拒學的方式表現出來。即使沒有上述拒學的狀況,也只是把問題到延後而已:持續對活著感到痛苦,最糟糕的結果就是自殺。
不過,並不是所有走向犯罪的孩子,都是因為家庭迫使他們壓抑自己的情緒。從《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即便蘇的孩子在痛苦當中,他依然覺得父母是愛他的,但他早已深陷憂鬱所苦。我們都知道,在青少年時期,孩子本來就會漸漸地對家人保持距離,和朋友有著更多的聯繫;然而,做為父母的,或是身為這些孩子的朋友、師長,依然有機會挽回這些悲劇。
岡本茂樹在書中便提到了,透過「最近有沒有碰到什麼困難?」、「下課後要不要一起聊聊天?」取代「真是個開朗的好孩子。」這句話,或許就能拯救孩子的性命,因為你給孩子說出「其實我已經痛苦得快死掉了」的機會。
張立人醫生也在《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的推薦序中寫道:「尊重孩子說『不』是好事,但瞭解孩子說『不』的原因,同樣重要。」
我們並非樣樣都做對。研讀許多資料後,我知道跟狄倫交流有更好的方式。我希望自己當初能多點傾聽,而不是只顧說教;我希望我能靜靜坐在他身邊,而不是只顧大放厥詞,一股腦把我的想法硬塞給他。我希望我能明白他有他的感受,而不是一味要他轉念,也希望覺得不對勁時,就算他以我累了、我有功課要寫等藉口百般推辭,我也要堅持跟他談談。我希望我能放下一切雜事,把心思全放在他身上,一再追問、刺探,更常在家以覺察我所疏漏的一切。——《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P.300
我們與惡的距離,其實沒有這麼遠
從蘇·克萊柏德的書中,我們看見了,即便事情發生已經過了16年,她的婚姻以離婚收場、得了焦慮症與恐慌症,一輩子遭受自己沒有覺察愛子即將殺人與自殺的痛苦當中,相較之下,與惡一劇呈現的雖然讓人震撼,卻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我們的憤恨不平,竟推著下一齣悲劇再次上演,就如同劇中喬安姐所遭受的質疑一般:你們這麼做,和殺人有什麼兩樣?
請別忘了蘇·克萊柏德的演講,請別忘了秋葉原事件的悲劇。當我們越是區分我們與惡的距離,那將使我們變成惡的一部分。
「我們讀童話故事給孩子聽,告訴他們世上有好人也有壞人,」蘇如此對我說,當時我正撰寫《背離親緣》(Far From the Tree)。「現在我絕不會這麼做。我會說每個人都能做善事,也能誤入歧途。愛一個人,他的好壞你都必須愛。」科倫拜事件發生前,蘇工作的地方剛好跟假釋官辦公室在同一棟大樓,她覺得和前科犯一起搭電梯很恐怖,很孤立無援。悲劇發生後,她大為改觀。「我覺得他們就像我兒子一樣。這些人不過是因故誤入歧途,才會深陷可怕無望的困境中。聽見新聞上出現恐怖份子的報導時,我會心想:『那是某人的孩子。』科倫拜事件讓我覺得自己跟全人類的聯繫更為緊密,除此之外,任何事都不可能使我做此想。」
——安德魯·所羅門(Andrew Solomon),《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推薦序
參考資料:
- Lerner, M.; Simmons, C. H. Observer’s Reaction to the 『Innocent Victim』: Compassion or Reje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66, 4 (2): 203–210.
-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
- 《教出殺人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