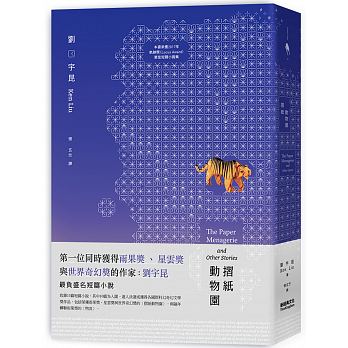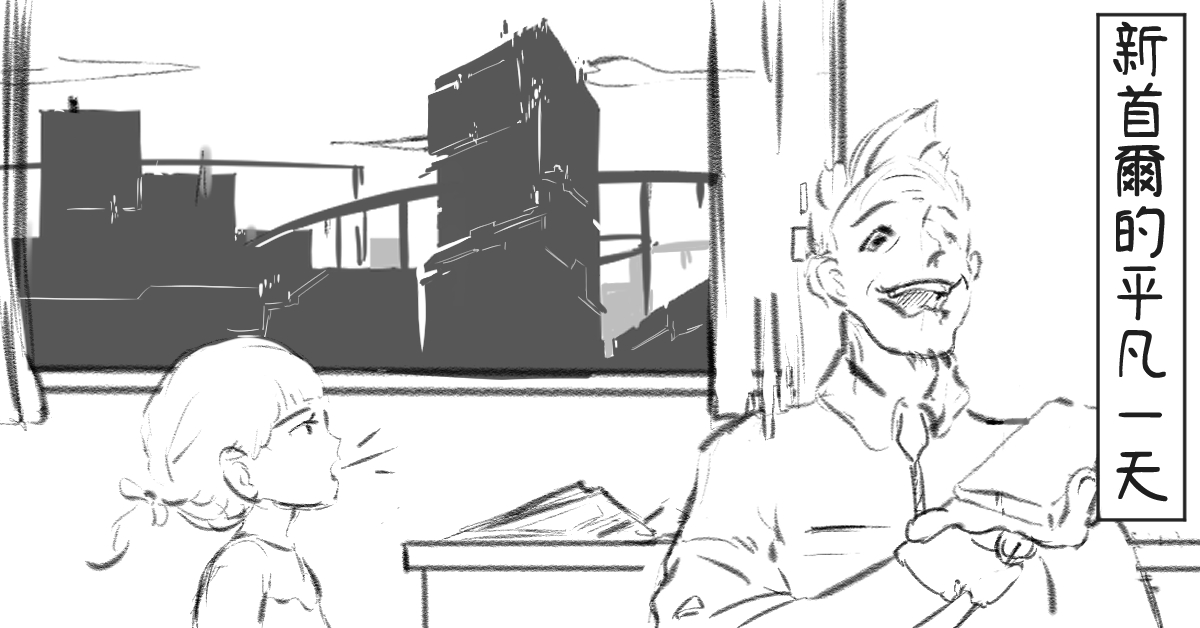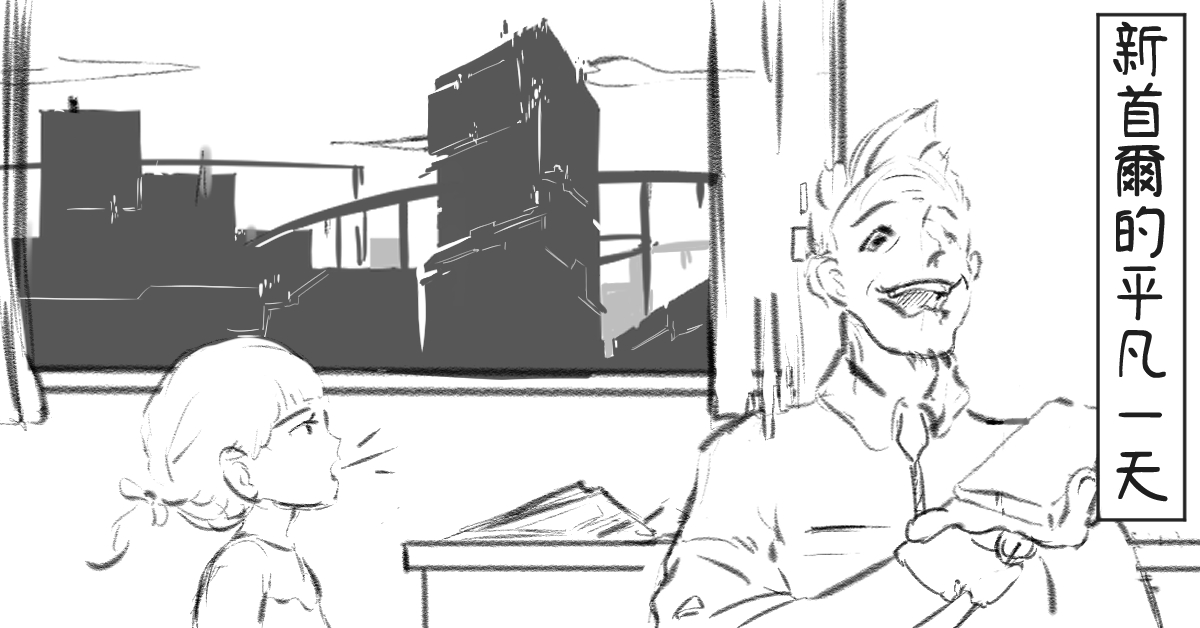編按:《摺紙動物園》集結了美國作家劉宇昆的十五個科幻/奇幻的短篇故事,應用的意象豐富,從未來世界、中日元素到歷史、神話傳說。〈物哀〉一文結合日本美學概念與乘坐太陽帆的遠離地球星際旅程,成就了含有獨特氣氛的科幻中短篇。
- 作者/劉宇昆(Ken Liu)
- 譯者/張玄竺
這世界的形狀就像漢字的「傘」,只是寫得不好,跟我的筆跡一樣,所有筆畫都不成比例。
我父親一定會對我仍然孩子氣的字跡感到很羞愧。確實,很多漢字我幾乎都寫不出來了,我在日本受的正規教育只到八歲。
但為了一時之需,這不好看的漢字還是可以的。
上面的頂篷是太陽帆,雖然那歪扭的漢字只能顯示它巨大尺寸之分毫。一千公里的旋轉圓盤風扇比宣紙要薄百倍,在太空中就像一個巨大風箏,意圖攔住每顆經過的光子。就字面上看,它遮住了整個天空。
底下吊著一條長長的奈米碳管線,有一百公里長:強壯、明亮又有彈性。管線最後吊著希望者號的心臟:居住艙,一個五百公尺高的汽缸,裡面載著世上所有居民,一千零二十一位。
從太陽傳來的光推著太陽帆,推著我們,以一種無止盡擴大、無止盡加速、盤旋飛升的運行軌道遠離太陽。加速度讓我們所有人貼著艙板,讓一切有了重量。
我們的軌道帶我們朝一顆叫「室女座61e」的星星前進。現在看不到它,因為它在太陽帆的座艙罩後面。希望者號大概三百年左右會抵達那裡,快一點或慢一點。幸運的話,我的曾曾曾—我數過總共要有多少個「曾」,但現在不記得了—─曾孫會看到它。
居住艙裡沒有窗戶,沒有星星偶然劃過的景象。大部分人不在乎,因為很久以前就看星星看膩了。但我喜歡透過星船底部的攝影機望去,這樣能看著我們的太陽、我們過去的紅色光芒漸漸模糊黯淡的景象。
「大翔,」爸爸邊說邊把我搖醒:「收拾你的東西,時間到了。」
我的小行李箱已經收好,只要把圍棋放進去就行了。爸爸在我五歲時把這副圍棋送給我,我一天中最喜歡的就是跟爸爸下棋的時刻。
媽媽、爸爸和我出門的時候,太陽還沒升起,所有鄰居也已經帶著他們的大包小包站在家門外,我們在夏日星空下逐一禮貌地打招呼。一如往常,我尋找著鐵鎚星。鐵鎚星很好找,從我有記憶以來,這顆小行星始終是天上除了月亮之外最亮的星,而且一年比一年亮。
一輛車頂裝了擴音器的貨車緩緩開到街道中間。
「久留米市居民注意!請依序前往公車站,那裡有很多公車,會把大家載到火車站,大家可以搭火車前往鹿兒島市。請勿自行開車,馬路須保持暢通,留給疏散公車和公務車輛。」
所有家庭緩緩走過人行道。
「前田太太,」爸爸對我們鄰居說:「我幫您拿行李吧?」
「太感謝了。」老奶奶說。
走了十分鐘之後,前田太太停下來靠著路燈。
「再走一段就到了,奶奶。」我說。她點點頭,但喘得沒辦法說話。我試著鼓勵她。「妳期待見到妳在鹿兒島市的孫子嗎?我也很想念阿道。妳可以跟他一起坐在太空船裡休息,他們說每個人都有位子。」
媽媽讚許地對我微笑。
「我們在這裡真是幸運。」爸爸說。他指指依序走向公車站的一排排人;指指穿著乾淨襯衫和鞋子、看起來嚴肅的年輕人;中年婦女攙扶著她們年邁的長輩;街道乾淨空曠,而且靜謐—雖然人很多,卻連一句悄悄話也沒人說。整個空氣似乎因著所有人—家人、鄰居、朋友、同事—之間的緊密連結而閃耀著,就像隱形但堅固的線。
我在電視上看過世界其他地方正發生的事:搶劫,尖叫,在街上跳腳,軍人和警察對空鳴槍、有時對人群開槍,著火的建築,疊起的成堆屍體,上將咆哮,群眾暴走,發誓就算世界末日也要為幾百年前的舊事復仇。
「大翔,我希望你記得這一切。」爸爸說。他看看四周,為之動容。「我們在面對災難的時候,展現身而為人的力量。明白我們並不是孤單的個體,而是在一張相互牽絆的關係網裡。一個人必須超越小我的需求,所有人才能和諧共處。個人渺小又力量微薄,但整體緊緊相連,日本這個國家就會堅不可摧。」
「清水老師,」八歲的博比說:「我不喜歡這個遊戲。」
學校位在圓柱形居住艙的中心,這裡的好處是對輻射電波有最強大的防護力。教室前方掛了一張大大的美國國旗,孩子們每天早上會對著它說出心裡的願望。在美國國旗兩邊是兩排小國旗,是希望者號上其他國家生存者的國旗。最左邊是一個孩子提供的日本國旗,國旗的白色邊角現在捲起來了,曾經明亮的紅色朝陽褪成橘色夕陽。國旗是我在登上希望者號那天畫的。
博比和他朋友艾瑞克坐在桌前,我拉開桌邊的椅子。「為什麼不喜歡?」
兩個男孩中間放了一張十九乘十九的直線方格,幾顆黑色和白色石子放在直線交叉點上。
每兩個禮拜,我會有一天休假。我平常的工作是監控太陽帆的狀態,還有來這裡教孩子們關於日本的事。有時我覺得這有點怪,我對日本只有小時候的朦朧記憶,怎麼能當他們老師呢?
可是別無選擇。所有像我一樣的非美籍技師覺得有義務投入文化推廣,把我們的所學傳承下去。
「這些石頭看起來都一樣,」博比說:「而且不會動。它們很無趣。」
「你喜歡什麼遊戲?」我問。
「星際保衛戰!」艾瑞克說:「那是個好玩的遊戲,可以拯救世界。」
「我是說不在電腦上玩的遊戲。」
博比聳聳肩:「西洋棋吧!我喜歡皇后,她很厲害,而且跟別人都不一樣。她是英雄。」
「西洋棋是小規模的戰鬥遊戲。」我說:「圍棋的概念更大一點,涵蓋整個戰場。」
「圍棋裡面沒有英雄。」博比固執地說。
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他。
鹿兒島市沒有地方可待,所以每個人都睡在太空中心外面的路上。我們能看見地平線上巨大的銀色避難船在陽光下發亮。
爸爸向我解釋,鐵鎚星掉下來的碎片正在往火星和月亮前進,所以飛船得帶我們到更遠的地方,到太空深處才能安全。
「我想坐靠窗。」我說,邊想像星星劃過。
「你應該把靠窗的位子讓給年紀比你小的人。」爸爸說:「記得,我們都要有所犧牲才能生活在一起。」
我們把行李箱堆成牆,用被子覆蓋在上面防風和防曬。政府的視察員每天都會來發送糧食和確認一切沒問題。
「要有耐心!」政府視察員說:「我們知道進度很慢,但我們盡力而為。每個人都會有位子。」
我們很有耐心。有些媽媽在白天替孩子們安排課程,爸爸們則議定了優先制度,等飛船好的時候,有年邁長輩和嬰孩的家庭可以先上船。
等了四天後,政府視察員的保證聽起來沒那麼堅定了,人群中開始有謠言傳開。
「船出了問題。」
「造船的人跟政府說謊,還沒準備好卻說已經準備好了。現在首相窘迫得不敢承認事實。」
「我聽說只有一艘船,而且只有幾百個最重要的大人物才有位子,其他船只是展示用的空殼。」
「他們希望美國人會改變心意,替像我們這樣的盟國多造幾艘船。」
媽媽走向爸爸,在他耳邊說悄悄話。
爸爸搖搖頭阻止她:「不要再講這些了。」
「可是為了大翔—」
「不行!」我從來沒聽過爸爸這麼生氣的聲音。他停下來,壓抑著。「我們一定要信任彼此,信任首相和自衛隊。」
媽媽看起來很不開心。我伸出手,拉著她的手。「我不怕。」我說。
「這就對了。」爸爸說,聲音和緩了。「沒什麼好怕的。」
他把我抱在懷裡—我有點不好意思,因為從我很小的時候他就沒有這樣抱過我了—指著我們周遭眼睛所能見到、成千上萬密密麻麻的群眾。
「看我們有多少人在這裡:奶奶、年輕的爸爸、大姊姊、小弟弟。任何驚慌失措和在群眾中散播謠言的人,都是自私的、錯的,很多人可能會因而受傷。我們一定要堅守岡位,永遠以大局為重。」
我和敏迪慢慢地做愛。我喜歡聞她深色捲髮的味道,像海、像新鮮鹽巴一樣濃密、溫暖、搔弄著鼻子。
之後我們躺在一起,望著我天花板上的投影機。
我一直重複播放星空遠去的畫面。敏迪的工作是操控航向,她替我錄了高解析度的駕駛艙連續影像。
我喜歡假裝監控器是一台大天光鏡,而我們躺在星空之下。我知道有些人喜歡用投影機播放地球的圖片和影片,但那會讓我太過悲傷。
「日文的『星星』怎麼說?」敏迪問。
「星。」我告訴她。
「那『客人』怎麼說?」
「お客さん。」
「所以我們是『星お客さん』,星星的客人?」
「不是這樣說啦。」我說。敏迪是歌手,她喜歡除了英文之外其他語言的發音。「不知道意思的話,就很難聽見文字背後的音樂。」她曾經告訴我。
西班牙文是敏迪的母語,但她記得的西班牙文甚至比我記得的日文還少。她常常問我日文,把日文寫進她的歌裡。
我試著幫她講得詩意一點,但不確定對不對。「われわれは星の間に客に来て。」我們是星辰中的訪客。
「描述每件事都有上千種方式,」爸爸總說:「每種方式適用不同場合。」他教會我,我們的語言充滿細微的差異和含蓄的優雅,每一句話都是一首詩。語言會自行摺疊開展,沒說出口的話和說出口的一樣有意義,話中有話、層層包裹,就像武士刀的刃紋。
我真希望爸爸在身邊,這樣我就能問他:做為自己民族的最後一位生存者,要怎麼用適當的方式在二十五歲生日時說「我想念你們」?
「我姊姊真的很喜歡日本漫畫。」
敏迪跟我一樣是孤兒,這是我們互相吸引的原因之一。
「妳記得很多她的事嗎?」
「不太記得。我登船的時候才大概五歲。在那之前,我只記得很多槍聲,我們全部人都躲在黑暗中,跑啊、哭啊、偷食物吃。她總是唸漫畫書的故事讓我安靜下來,後來……」
我只看過那支影片一次。從我們的高軌道看,小行星撞上時,那個叫做「地球」的藍白色大理石似乎晃動了一下,然後,四面八方翻滾而至的靜默海浪緩緩吞沒了整個球體。
我把她拉向我,輕吻她的額頭,安慰的吻。「我們別說這些難過的事了。」
她的手臂緊緊環著我,彷彿永遠也不會放開。
「那些漫畫,妳還記得嗎?」我問。
「我記得裡面全是大機器人。我當時還想:日本好強大啊!」
我試著想像日本充滿巨大英勇的機器人,拚命拯救人類。
首相的道歉透過擴音器轉播,有些人也從手機上看到了。
我不太記得了,只記得他的聲音很小,他的樣子虛弱又蒼老,看起來真的很抱歉。「我讓大家失望了。」
結果謠言是真的。造船的人跟政府拿了錢,但並沒有如他們承諾的那樣,造出夠堅固或承載力足夠的飛船。他們一直裝模作樣到最後一刻,我們發現真相時已經太晚了。
日本並不是唯一讓國人失望的國家。這世界上的其他國家一開始發現鐵鎚星即將撞上地球時,就忙著爭執誰該多出一點力投入聯合疏散計畫。之後,計畫失敗了,多數人卻寧可賭鐵鎚星不會撞上,繼續揮霍度日,或把時間用來跟別人吵架。
首相說完話後,群眾保持著沉默。有一些憤怒的聲音,但很快也安靜下來。人們有秩序地緩緩收拾行李,離開這個暫時的營地。
「那些人就回家了?」敏迪不可置信地問。
「對。」
「沒有搶劫、沒有開槍、沒有軍人在街上叛亂?」
「這就是日本。」我告訴她。我能聽見自己語氣中的驕傲,附和著父親的聲音。
「我猜他們都很聽天由命。」敏迪說:「他們放棄,也許是文化的關係。」
「不是,」我努力不帶情緒地反駁。她的話激怒了我,就像博比說圍棋很無聊一樣。「不是這樣。」
「爸爸在跟誰說話?」我問。
「是漢米爾頓博士。」媽媽說:「我們—他和你爸爸和我—一起在美國念大學。」
我看著爸爸用英文講電話。他似乎變成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人:不只是聲音的抑揚頓挫和音調不一樣,他的表情、手勢都比平常更激動,看起來像外國人。
他對著電話大吼。
「爸爸在說什麼?」
媽對我「噓」了一聲。她專心看著爸爸,仔細聽每一個字。
「No !」爸爸對著電話說:「No !」這不需要翻譯。
後來媽媽說:「他在努力用他的方式釋出善意。」
「他和以前一樣自私。」爸爸氣急敗壞。
「這樣說不公平。」媽媽說:「他沒有打給我,而是打給你,因為他相信你會像他一樣,願意讓所愛的女人有機會活下去,即便是和另一個男人一起。」
爸爸看著她。我從來沒有聽過爸媽對彼此說「我愛你」,但有些話心照不宣。
「但我絕對不會答應他。」媽媽微笑著說,然後走進廚房做我們的午餐,爸爸的視線跟著她。
「今天天氣很好,」爸爸對我說:「我們去散步吧!」
我們在人行道遇到其他散步的鄰居。大家互相打招呼,互相問好。一切似乎都如常。鐵鎚星在幽暗的頭頂上更加閃亮了。
「你一定非常害怕,大翔。」他說。
「他們不會想辦法造更多避難船了嗎?」
爸爸沒有回答。夏末的風把蟬聲吹向我們:唧、唧、唧唧唧。
蟬聲唧唧,
不見形影將盡,
殤輓之景。
「爸爸?」
「這是松尾芭蕉的詩,你知道意思嗎?」
我搖搖頭,我沒有很喜歡詩。
爸爸嘆了口氣,對我微笑。他看著落下的夕陽又說:
夕陽無限好,
只是近黃昏。
我默默背下這兩句,某種感覺打動了我。我試著把感受說出來:「好像小貓在輕輕舔我的心一樣。」
爸爸沒有笑我,反倒認真地點點頭。
「這是唐朝詩人李商隱的詩。雖然他是中國人,這種感懷卻非常像日本人。」
我們繼續走,我停下來看蒲公英的黃色花朵。花開的角度非常美,震懾了我。我心裡再度有了那種小貓輕舔的感覺。
「花……」我遲疑著,找不到確切的形容詞。
爸爸開口說:
殘花低垂,
蒼黃如月,
消瘦今夜。
我點點頭。這個畫面對我來說如此短暫,又如此永恆,像我小時候對時間的感受。
「一切都會消逝,大翔。」爸爸說:「你心裡的那種感覺叫做『物哀』,是對生命中所有事物皆稍縱即逝的感思。太陽、蒲公英、禪、鐵鎚星和我們所有人。我們全都臣服於詹姆斯.克拉克.馬克士威的電磁場方程式,我們都是注定會逝去的短暫生命,無論是一秒鐘還是一萬年。」
我看看四周乾淨的街道、緩慢移動的人們、草皮、傍晚微光,明白了一切事物都有它的位置,一切都會沒事的。我和爸爸繼續走著,我們的影子依靠著彼此。
雖然鐵鎚星就掛在頭上,我並不害怕。
未完待續:物哀(下)──小說《摺紙動物園》搶先看
本文摘錄自新經典文化出版《摺紙動物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