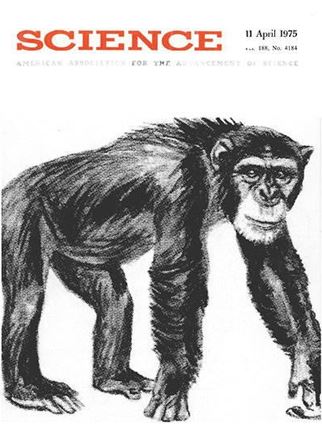編按:泛科學八月選書《基因:人類最親密的歷史》,從家庭病史出發,作者穆克吉細數百年間數以百計的科學家如何前仆後繼,破譯遺傳基因這項生命之謎;從近兩百年前在修道院裡發覺遺傳學邏輯,一路到接近基因治療的今日;既介紹遺傳基因的核心概念,亦一窺漫漫科學長河如何前進與掙扎。
人生起伏就像潮起潮落,
趁著高潮勇往直前,就可以功成名就;
若不能把握時機,人生旅程就會駛向淺灘,陷入悲慘絕境。
我們現在正在滿潮的海上。
──莎士比亞《凱撒大帝》(Julius Caesar)第四幕,第三景
我相信所有成年科學家都具有私下愚弄自己的必要權利。
──西德尼.布倫納
當心!生物性危害就在眼前!
一九七三年一月,埃里切之行的數月後,伯格決定在加州召開一場小型研討會,討論大家對基因操控技術日益增進的憂慮。會議在厄西勒瑪(Asilomar)的太平洋樹林(Pacific Groves)會議中心舉行,離史丹福約八十哩,是坐落在蒙特瑞灣(Monterey Bay)岸邊的幾棟建築。各學科的科學家,如病毒學家、遺傳學家、生化學家與微生物學家等齊聚一堂。這次的會議後來被伯格稱為「厄西勒瑪第一次會議」,雖然吸引了很大的興趣,卻並沒有提出什麼建議。

會議主要的內容是生物安全(biosafety),大家踴躍地對於使用猿猴病毒 40 和其他人類病毒發言。伯格告訴我,「那個年代,我們還在用嘴吸取病毒和化學物質。」他的助理瑪麗安.狄克曼(Marianne Dieckmann)記得有個學生不小心把一些液體灑到香菸的菸頭上(那時實驗室裡常看得到點著的香菸在菸灰缸裡空燒),那名學生根本不當一回事,照樣拿起香菸吸,任菸頭上的那滴病毒掉在菸灰裡。
厄西勒瑪這場會議創造了一本重要的書《生物研究的生物性危害》(Biohazards in Biological Research),但更重要的結論卻付之闕如。伯格說,「坦白說,最後的結果是我們明白自己所知多麼有限。」
跨越百萬年演化鴻溝的基因重組
一九七三年夏,波伊爾和科恩在另一場會議提出他們細菌基因混合體的報告,更進一步點燃人們對基因複製的憂慮。同時,位在史丹福的伯格則窮於應付世界各地研究人員對基因重組試劑的要求。芝加哥的一位研究員提議把致病性極高的人類皰疹病毒基因插入細菌細胞,創造出負載致命毒素基因的人類腸道細菌,名義上是研究皰疹病毒基因的毒性(伯格委婉地拒絕了)。抗生素抗性基因經常在細菌之間交換。基因經常在物種和屬之間移動,一躍跨越百萬年的演化鴻溝,就如不經意地踩過沙上的細線這般容易。
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注意到不確定性不斷增加,因此召請伯格領導基因重組的研究小組。

小組共有八名科學家,包括伯格、華生、巴爾的摩和諾頓.辛德(Norton Zinder)等。一九七三年四月一個春寒料峭的日子,他們在波士頓麻省理工學院開會,馬上開始集思廣益,探討控制和調控基因複製的可能機制。巴爾的摩建議培養「經破壞而殘障的『安全』病毒、質體和細菌」,但是,即使它們無法致病,這樣的安全措施也未必萬無一失。誰能保證「殘障」病毒永遠殘障?畢竟,病毒和細菌並非被動的惰性物體。即使在實驗室環境,它們也是活生生的,會移動也會演化。只要一個突變,原本殘障的細菌就可能再度充滿毒性。
辯論持續了好幾個小時之後,辛德提出了一個簡直可以說是開倒車的計畫:「好吧,只要我們有種,就乾脆告訴大家不要做這些實驗。」這個建議引起了桌前一陣低聲的騷動。這根本不是理想的解決方案──科學家要求限制其他科學家進行研究,實在沒有誠意,不過這至少可以作為暫停令。伯格回憶說,「儘管這樣做教人不快,但我們想或許會有效果。」因此,小組起草了正式函件,要求「暫停」某些重組DNA的研究。這封信衡量了基因重組技術的風險和益處,建議延後一些實驗,直到可以解決安全問題為止。
伯格說,「並不是每一個想得到的實驗都有危險,但是,有些實驗顯然就是比較危險。」其中三種DNA重組程序尤其需要嚴格限制。伯格建議,「不要把毒素基因放入大腸桿菌、不要把抗藥基因插入大腸桿菌、不要把癌基因放進大腸桿菌。」伯格和同僚認為,若能暫停下來,就能讓科學家有一點時間思考他們研究工作的意義。他們建議在一九七五年舉行第二次會議,讓更多科學家討論這些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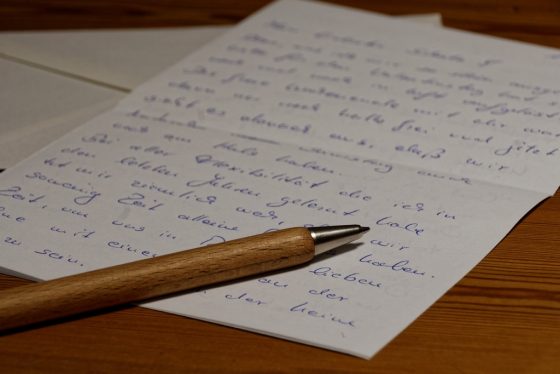
繼續實驗抑或先設定規範?
一九七四年,《自然》、《科學》和《國家科學院學報》都刊登了這封「伯格的信」,立刻引起舉世注意。英國成立了一個委員會,探討重組 DNA 和基因複製「潛在的利弊」,法國的《世界報》(Le Monde)也刊登了針對這封信的反應。那年冬天,賈克柏(因基因調控而知名)應邀審核一件研究補助金申請案,要把人類肌肉基因插入病毒。賈克柏也跟從伯格的先例,敦促擱置這樣的提案,等到國內對重組 DNA 科技有了確切的態度再說。一九七四年,德國某場會議上的許多遺傳學者重申類似的看法,重組 DNA 研究的實驗應該嚴格規範,直到可以清楚描述其風險,確定該採取什麼樣的建議為止。
不過,與此同時,研究依舊如火如荼地進行,打破了生物及演化的種種障礙,彷彿這些障礙弱不禁風,只靠牙籤撐著。在史丹福,波伊爾、科恩和他們的學生把青黴素抗藥基因由一個細菌移植到另一個細菌上,創造了抗藥大腸桿菌。理論上,任何基因都可以由一個生物體轉移到另一個生物體。波伊爾和科恩大膽提出:「將特定代謝或合成功能的基因,引入不同綱的生物(如不同的植物或動物),或許可行。」波伊爾開玩笑地說,「物種是虛假的。」
一九七四年元旦,在史丹福和科恩一起工作的一位研究員報告說,他已把青蛙的基因插入細菌細胞,就這麼輕易地跨越了另一個演化的邊界。在生物學領域,就如王爾德說的,「表現自然,其實就是一種做作。」

第二次厄西勒馬會議:該如何控制科學家重組 DNA 的實驗?
第二次厄西勒瑪會議──科學史上最不尋常的會議之一,是由伯格、巴爾的摩和其他三位科學家於一九七五年二月召開。遺傳學家再一次回到了風大的沙灘沙丘討論基因、重組及未來的展望。這是個美麗的季節,帝王蝶正沿著海岸進行一年一度的遷移,準備飛往加拿大的草原。紅杉和矮松則突如其來地化成了紅、橙和黑色的隊伍。
與會者在二月二十四日抵達,只是其中不只有生物學家。伯格和巴爾的摩十分明智地邀請了律師、記者和作家參加會議。如果要討論基因操控的未來,他們不僅需要科學家的意見,也要參考更多人的想法。他們可以在會議中心周圍的木板走道思索交談;生物學家可以在這些走道或沙灘上交換他們對重組、複製和基因操控的意見。相較之下,會議的中心──四周石牆佇立,宛如大教堂空間且映照著加州陽光的中央大廳,則即將爆發關於基因複製最激烈的辯論。
伯格首先發言,他概述了資料,提出問題的範圍大綱。在研究化學改變DNA方法的過程中,生化學家最近發現了一種較為容易的技術,可以排列組合不同種生物的遺傳信息。依照伯格的說法,這種技術「簡單得離譜」,就連業餘的生物學者也可以在實驗室做出嵌合基因。
這些混合的DNA分子(重組DNA),可以在細菌裡繁殖(即複製),產生數百萬份相同的副本。其中一些分子可以送進哺乳動物的細胞。由於大家了解這種技術深遠的潛力和風險,因此先前召開的初步會議建議暫停實驗,如今召開第二次厄西勒瑪會議,為的是要商議接下來的步驟。結果,第二次會議在影響和眼界層面,都遠遠超過第一次會議,因此被簡稱為厄西勒瑪會議,或者就叫艾斯洛瑪。

會議頭一天早上,壓力和情緒很快就爆發了。主要的問題依舊是業界自設的暫停令:科學家重組 DNA 的實驗該不該受到限制?華生表示反對。他希望有完全的自由,他呼籲:讓科學家在科學上不受拘束。巴爾的摩和布倫納則重申他們打算製造「殘障」基因攜帶者的計畫,以確保安全。其他人則意見分歧。
他們認為,眼前科學有很大的機會,如果暫停研究,可能會使進展癱瘓。一位微生物學者對會中提議的嚴格限制深感不滿,指控委員會:「你們毀了研究質體的群組。」伯格一度威脅控告華生,指他未能適度坦承重組DNA的風險。在討論到基因複製風險特別敏感的議題時,布倫納要求《華盛頓郵報》的記者關掉錄音機,「我相信所有成年科學家都具有私下愚弄自己的必要權利。」他說。結果馬上就遭指責是「法西斯」。
組委會五位成員:伯格、巴爾的摩、布倫納,理查.羅布林(Richard Roblin)和生化學家馬克辛.辛格(Maxine Singer)急切地在室內走動,評估越來越火爆的氣氛。一位記者寫道,「爭論一直持續,有些人受夠了這一切,乾脆直接離席到海邊抽大麻。」伯格坐在自己的房間,一臉怒容,擔心這次的會議不會有結論。
到了會議最後一天晚上,依舊沒有什麼正式的結果,直到律師登場。五位律師要求討論複製的法律後果,並對潛在風險提出了冷酷的看法:
如果一間實驗室的某位成員感染了重組細菌,而感染導致與某種疾病有所牽連,即使只是最微小的牽連,實驗室負責人、實驗室和所屬的機構都須承擔法律責任。整所大學也須關閉。實驗室會無限期關閉,運動人士會守在門口抗議,而大門則會由全副防護衣的化學災害處理人員上鎖。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會恐怕會窮於應付來自四面八方的詢問,一切亂成一團。聯邦政府不得不提出嚴厲的規定,不僅限於重組 DNA,而是包括更大範圍的生物研究。到頭來,各方對科學家的限制恐怕比科學家自願遵守的任何規則都嚴格得多。
律師的報告策略性地安排在第二次厄西勒瑪會議的最後一天,也是整個會議的轉折點。伯格知道如果提不出正式的建議,會議就不該也不能結束。

生物實驗的四級計畫
那天晚上,巴爾的摩、伯格、辛格、布倫納和羅布林在他們的小屋裡熬夜,吃著紙盒裡的中國菜外賣,在黑板上塗塗寫寫,並且草擬未來計畫。到了清晨五點半,他們蓬頭垢面、眼神迷茫地步出海邊小屋,全身是咖啡和打字機色帶的氣味,手上拿著一份文件。文件一開始先談起科學家不知不覺地隨著基因複製,進入了生物學奇特的平行宇宙。
「結合截然不同生物的遺傳信息,這種新技術把我們放在許多未知的生物學舞臺上。正是這種無知,使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進行這種研究時應該格外謹慎。」
為了降低風險,文件提出四級計畫,排列各種經遺傳改造生物的生物性危害潛力,並且為每個級別推薦控制層級(比如把致癌基因插入人類病毒將需要最高層級的控制,而把青蛙基因放入細菌細胞,則只需要最低層級的控制)。就如巴爾的摩和布倫納堅決主張的,它建議培養已遭破壞的攜帶基因生物體和媒介,在實驗室進一步限制它們。最後,它敦促持續審查重組和抑制程序,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放寬或收緊。
會議在上午八點半開始時,委員會的五位成員都擔心他們的提案會遭拒絕。出乎意料的是,幾乎所有的人都毫無異議地接受了。

本文摘選自八月選書《基因:人類最親密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