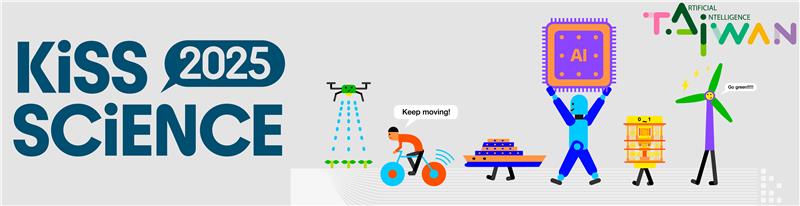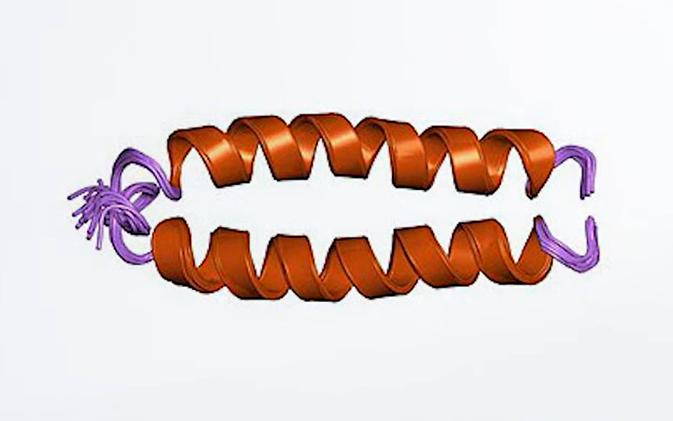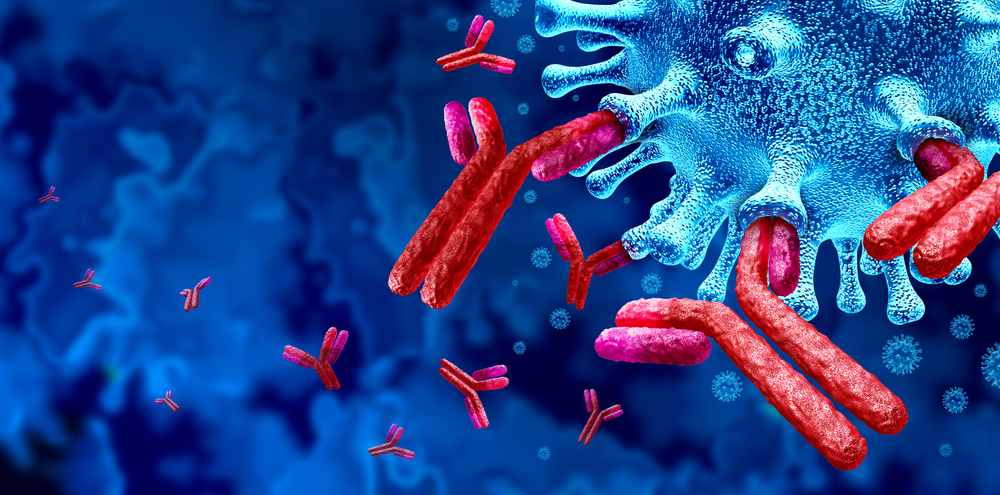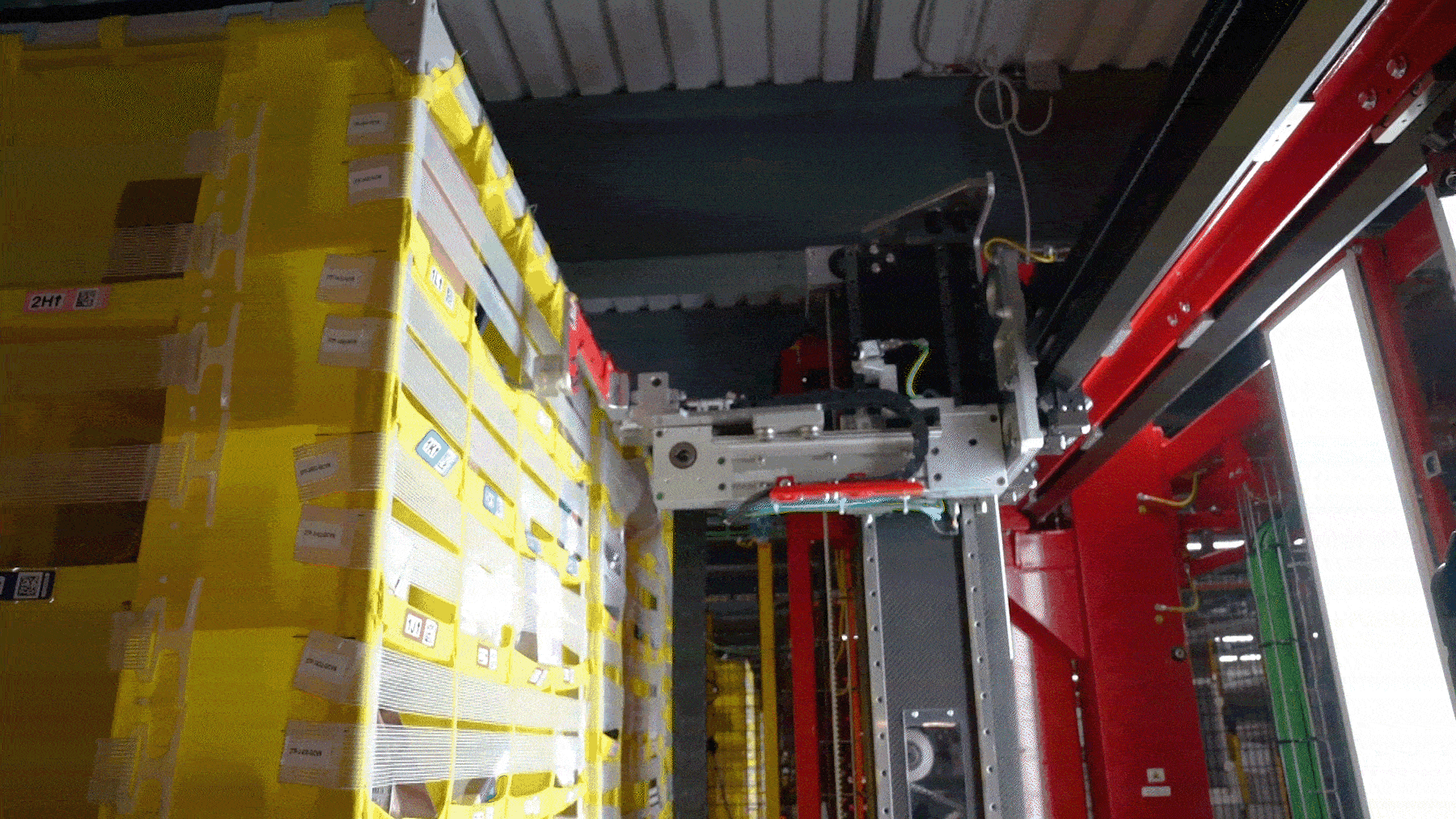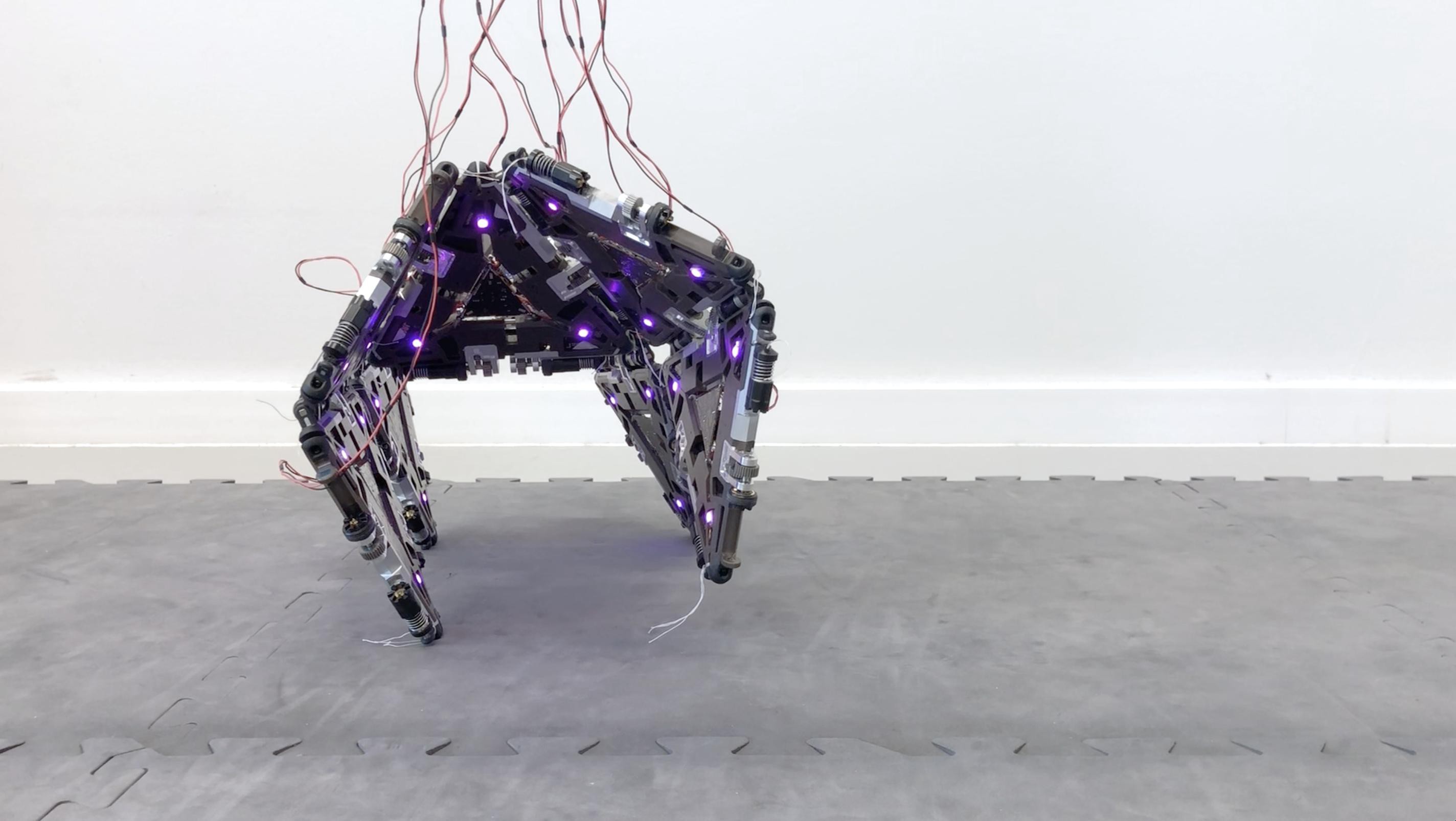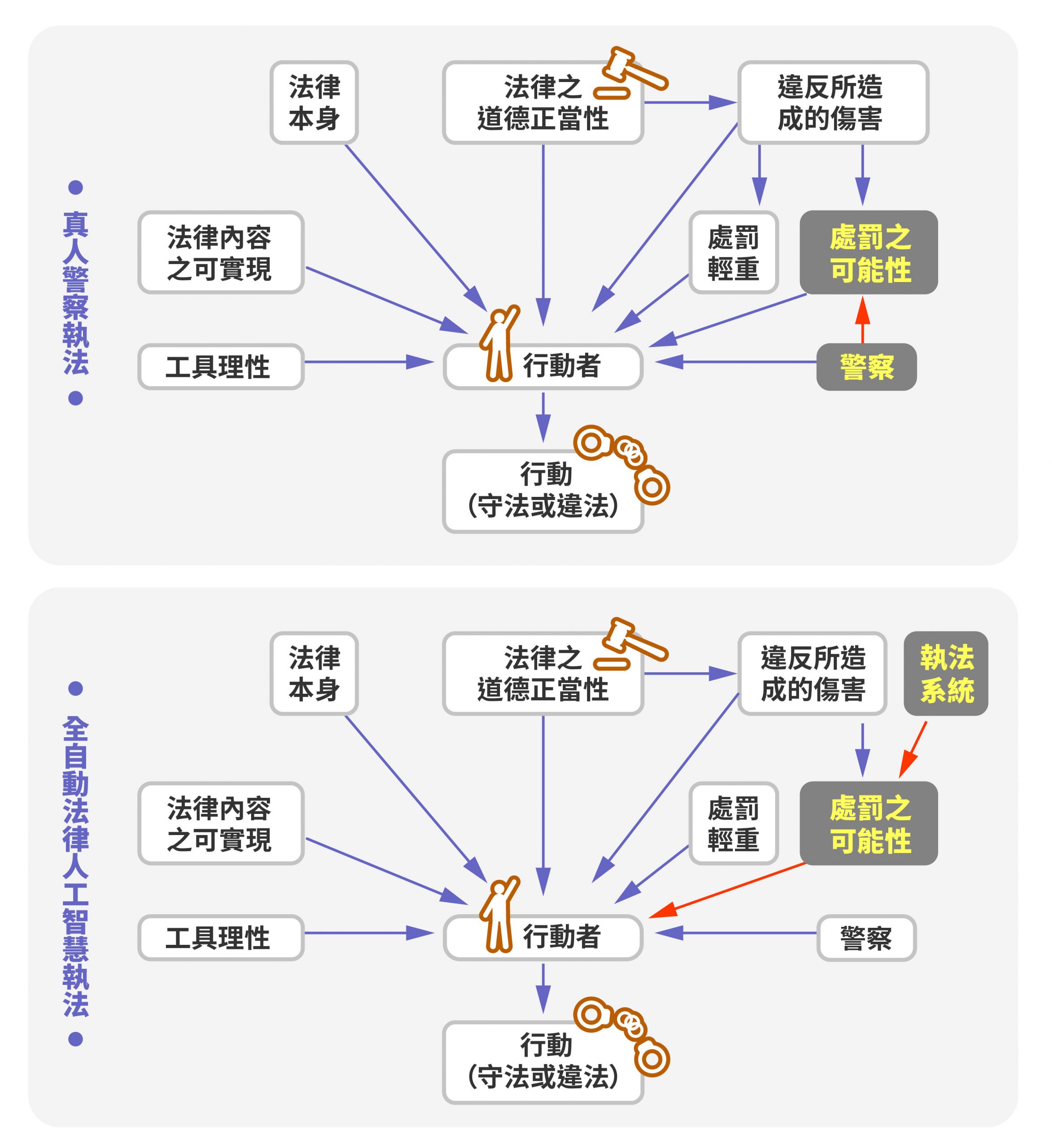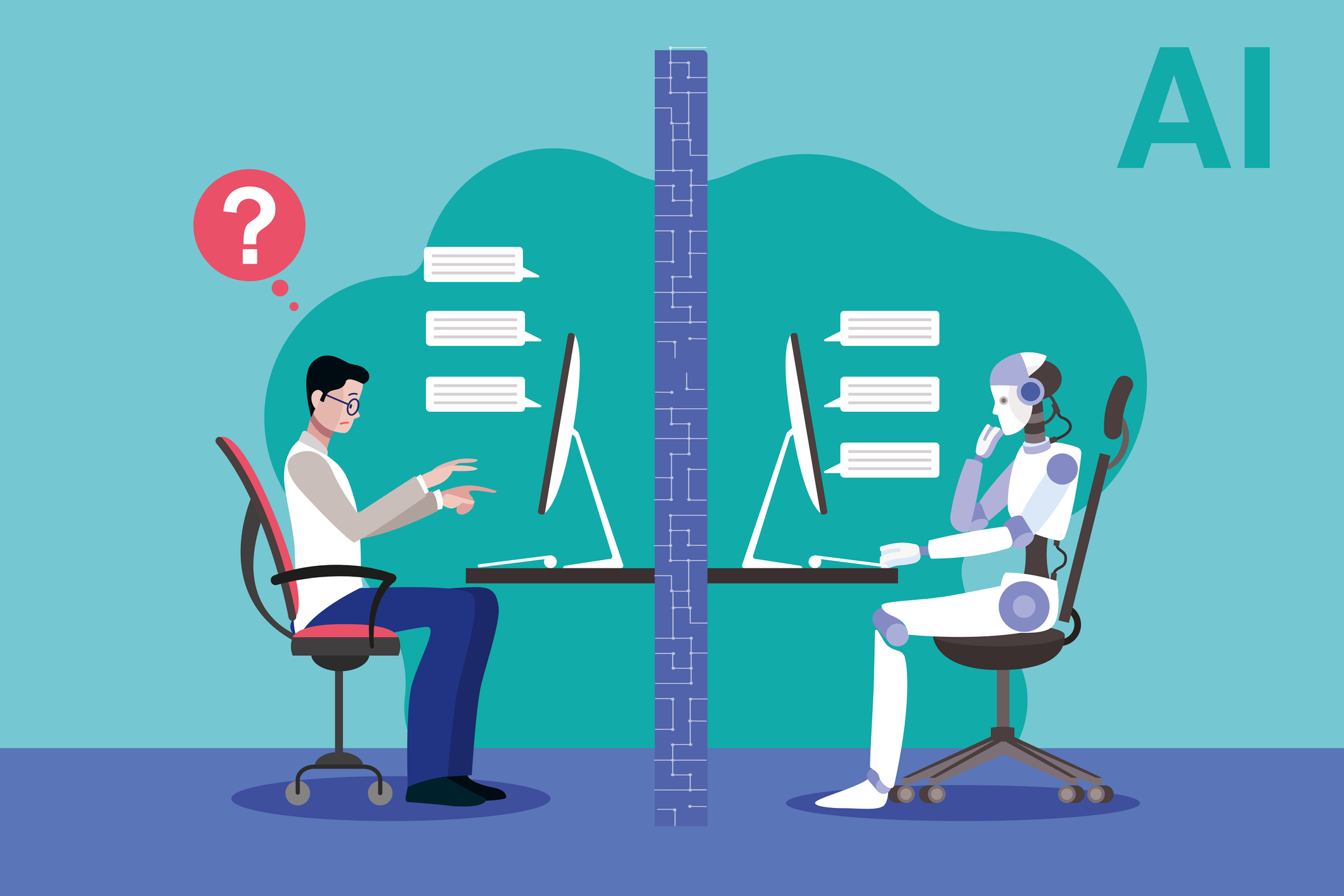文/豬文

身在香港、台灣或是其他地方的好青年,你能夠讀到這篇文章,證明你也不至於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我相信,你們至少不用每天為着三餐溫飽憂心(當然不是說你不用為三餐打工賺錢,而是說你不會真的沒東西吃,會餓死),不用無時無刻跟死神搏鬥。即使我們不是大富大貴,但或多或少,我們總會有些奢侈的享受,可能是閒時去旅行、可能是吃個自助餐、可能是看個電影。哪怕是買罐汽水,其實也算奢侈,因為沒有這罐汽水,你還是能活得好好的。
那麼,我們會覺得過着這樣的生活,是一種道德罪惡嗎?
我想絕大部分人都不會這樣想。如果有人指責你的生活,你第一個反應很可能是:「什麼?我又不是像那些大富豪一樣,在過一種窮奢極欲的生活。我不過是每天買罐可樂,放假去趟日本。何錯之有?」
但事實上,這個「正常」反應,以及我們一直過着的這種「正常」生活,真的沒問題嗎?其理據真的站得住腳嗎?先讓我們設想一下以下情況:
假設有個小孩給一輛貨車撞倒了,但那貨車揚長而去,獨留小孩躺在血泊之中。這個時候,你剛好經過,你認為自己有道德責任去救眼前那個奄奄一息的小孩嗎?如果你對他視而不見的話,會覺得應該受到道德譴責嗎?
我想,絕大多數人的道德直覺,都會指你有道德責任救他。不對他伸出援手的話,你是犯上了道德錯誤而應該受到責怪。只要回想 2011 年時轟動社會的「小悅悅事件」,大家的感覺可能會強烈得多。那時候,大家看到那十幾個路人對小悅悅視若無睹時,何曾不會感到無比憤怒?何曾不會想質問他們怎可能如此冷血,為什麼一件道德上如此明顯是正確的事都不去做?何曾不會覺得自己身在其中的話,必定出手救人?
什麼時候該施救?只要符合兩大原則就該出手
美國哲學家 Peter Singer 便認為,一旦你有上述的道德直覺的話,便必須承認我們絕大部分人過着的生活也是不該過的,亦即是說,正在過「平凡」生活的我們,其實和那十幾個見死不救的人沒什麼兩樣。(註 1)

為什麼呢?在上述的例子中,顯示了我們都接受了兩項道德原則:
第一,因缺乏適當的醫療照顧,或者缺乏其他資源而引致的痛苦與死亡,都是道德上不好的。如果我們不認為小悅悅所承受的痛苦是不好的話,又怎會覺得我們應該要救她呢?
設想一下,這一次貨車快要輾過的,只是一塊石頭,我們同樣會認為有責任去拿開那石頭,讓它避免被貨車輾過嗎?我想絕大部分人都不會這樣認為,除非你是一種泛心靈論者。這兩個情況的分別就是,小悅悅會有感到痛苦與面對死亡,而一塊石頭不會,所以我們認為小悅悅應該獲救,其實是源於我們認為她應該免受這種痛苦與死亡。這也顯示了我們認為上述的痛苦與死亡是不好的,是一種道德上的惡。
第二,若不必犧牲其他道德上重要的事,當我們有能力去阻止這種惡事發生時,我們便有道德責任去阻止。為什麼我們會對那十幾個見死不救的人如此憤怒?是因為我們認為他們都有道德責任去救人。為什麼我們會認為他們有道德責任救人?是因為我們認為救人這件事在他們的能力範圍之內,亦不用他們犧牲其他任何道德上重要的事。
設想一下,你質問其中一個對小悅悅視而不見的人,為什麼他不救人,然後他跟你說:「那怎麼救啊大哥?她滿身都血,我這衣服新買的,我救她會弄髒衣服啊!」你當然不會接受這種辯護。你質問他之前,早就知道救人這件事是要「犧牲」的,哪怕是「犧牲」他們幾十秒時間打電話叫救護車。但我們仍然覺得他們有道德責任去救人,是因為無論幾十秒時間,還是那新買的衣服都沒有任何道德上的重要性(或這重要性根本微小得跟小悅悅正在承受的痛苦無法比擬)。
換個例子,如果那個人跟你說:「我無法停下來,因為我是醫生,趕着去前面的另一個車禍現場救人,那邊有十個在死亡邊緣的傷者等着我救」又或者「我無法停下來,因為我上班一定不可以遲到,我遲到的話,我便會被革除。我被革除的話,家裏的人都會沒飯吃」的話,我們似乎便不會有如此強烈的直覺,覺得這個人做了件道德錯事,因為十條人命跟家庭都是道德上重要的事。
若救人是要犧牲其他道德上重要的事才能辦到的話,我們便沒有如此強的直覺認為他們有責任去救人。(當然有些道德理論會嘗試論證,在這些情況下,尤其是第二個牽涉家人的情況,我們仍有責任去犧牲這些道德價值去救眼前的人,但這不是這裏的重點。這裏的重點是,若不用犧牲其他道德價值,你便有責任救人。這說法幾乎所有道德理論都會接受的。)
我們都是見死不救的路人
那麼,這兩條道德原則,跟我們正在過的「平凡」生活有什麼關係呢?我們又不是為了買汽水而不救小悅悅,我們做錯了什麼?
要了解我們做錯了什麼,你只需到 Google 搜尋一下現在地球上第三世界國家人民正在經歷的窮困。例如,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去年的報告,葉門現時有超過四十萬處於飢餓的兒童,每十分鐘便有一名兒童會因營養不良或隨之而來的疾病而死去;全球每天因可預防疾病而死去的兒童有大約有一萬九千名。既然我們承認小悅悅的情況構成了那十幾個路人的道德責任,那為什麼這成千上萬在貧窮國家危在旦夕的小孩,又沒有對正在上網購物的我們構成道德責任呢?

按剛剛兩條原則,其實我們同樣有道德責任去幫助他們。第一,他們的痛苦與死亡是道德上的惡事。我們認同小悅悅的痛苦是不好的,所以我們有責任救她,難道葉門的小孩的痛苦就不是不好嗎?我怎能說他們的痛苦不算是道德上的惡事,所以我們沒有責任救他們呢?
第二,要幫助貧窮國家的小孩,無疑在我們能力範圍之內,而我們又不用犧牲任何道德上重要的事。很簡單,喝可樂、純綷愛美買新衣服是一件道德上重要的事嗎?明顯不是,但只要我們每天把買可樂、買新衣服的錢省下來,全部捐給慈善團體,很可能便能拯救到一名小孩的生命,或至少大大改善他的生活。如此一來,你不把錢捐出去,而用來買可樂、買衣服,此事之理由又如何能夠證成呢?
當然,這不是要求你要放棄一切,大老遠跑去貧窮國家幫人,因為這會令你犧牲很多道德上重要的事,例如你自己的人生目標、你的家庭等等。這就跟要求剛剛趕着上班的路人救小悅悅一樣不合理(再一次,有倫理學立場認為這是合理的,但在這裏無關宏旨,撇開不談)。但現在 Singer 要求的,只是要你少買罐可樂、少買件衣服去拯救一條在葉門的人命。你又能有什麼道德理由拒絕呢?如果你拒絕,又跟剛剛那個怕弄髒衣服的人有什麼分別?
只有道德,沒有距離
這兩個情況,最明顯不過的差異便是小悅悅實在地出現在那十幾個路人的面前,而那些每天在葉門死去的小孩離我們有幾千公里遠。但是,這個距離上的差別,似乎只能說明了我們心理上的不同:若他出現在我眼前,會更易挑動到我的心理反應,進而使我有更大動力去幫助他。
但問題是,這足以構成一種道德理由嗎?為什麼單純距離上的差異會構成道德上的差異呢?葉門的小孩在比較遠的地方、小悅悅出現在我們正在走的路上,這在道德上真的有任何意義嗎?按 Singer 的說法:
Does it really matter that we’re not walking pass them on the street?Does it really matter that they’re far away?
設想一下,原來當年不單止那十幾個路人有機會救回小悅悅,原來在香港還有一位瘋狂科學家目睹一切,那個人只需要在家按一按鈕,便能叫當地的救護車去救小悅悅。但他和那十幾個路人一樣,對小悅悅見死不救。難道單純因為物理上的遠近,這個科學家在道德上犯的錯,便會比起那十幾個路人來得小嗎?甚至因為他在很遠的地方,所以他便沒有救小悅悅的道德責任嗎?以物理距離的遠近去證明道德責任的不同,並不一定成立。
肩負起道德責任,哲學帶人改變世界
正如那些路人有道德責任去救小悅悅,我們亦有道德責任去幫助那些活在水深火熱的小孩。如果我們繼續維持現在的生活模式,其實我們就像那十幾個路人一樣,是見死不救,是逃避自己的道德責任。無論我們多麼不想接受這個結論都好,只要我們同意了那些人應該救小悅悅,我們便得接受這個結論。
近年西方社會有一場愈來愈多人響應的社會運動:有效的利他主義(effective altruism)。這種運動的起源,大可追溯到本文介紹的,由 Peter Singer 提出的觀點:透過例如捐錢這些手段去幫助貧窮國家的人,其實不只是一種慈善工作(一種你做了會得到讚賞,但你不做也不會受到遣責的事),而是每一個富裕國家的人的道德責任。
這種運動不只是哲學家們的智力遊戲,而正實實在在地改變着這個世界。大量人響應這場運動而立約將自己每月收入的十分之一捐給其他貧窮國家的人,希望盡量拯救生命,改善他們的生活。可見哲學也可以幫手帶來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不知道看完這篇文章的好青年,又有多少人被說服,被說服的人當中,又有多少人真的做到知行合一呢?
- 註 1:本文主要討論的是 Peter Singer 在 1972 發表的著名論文「Famine, Affluence, and Morality」。該文用的例子是我們有沒有責任救一個快要墮入池塘的孩子。而 Singer 在 2013 的 Ted Talk 中用的例子,則是上述小悅悅的例子
- 編按:二千多年前,曾經有個叫蘇格拉底的人,因為荼毒青年而被判死,最終他把毒藥一飲而盡。好青年荼毒室中是一群對於哲學中毒已深的人,希望更多人開始領略、追問這世界的一切事物。在他們的帶領下,我們可能會發現我們習慣的一切不是這麼理所當然,從這一刻起接受好青年荼毒室的哲學荼毒吧!
本文轉載自好青年荼毒室(哲學部),有效的利他主義系列:笑甚麼?你也是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