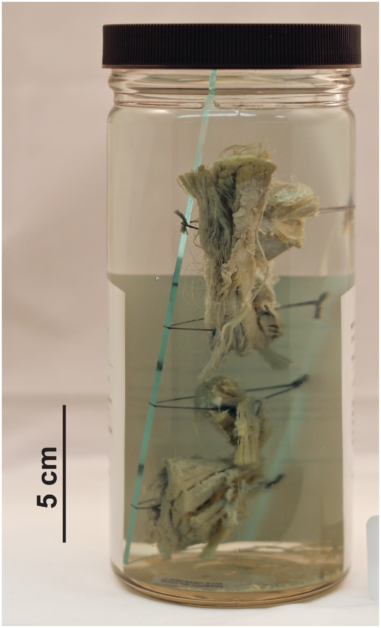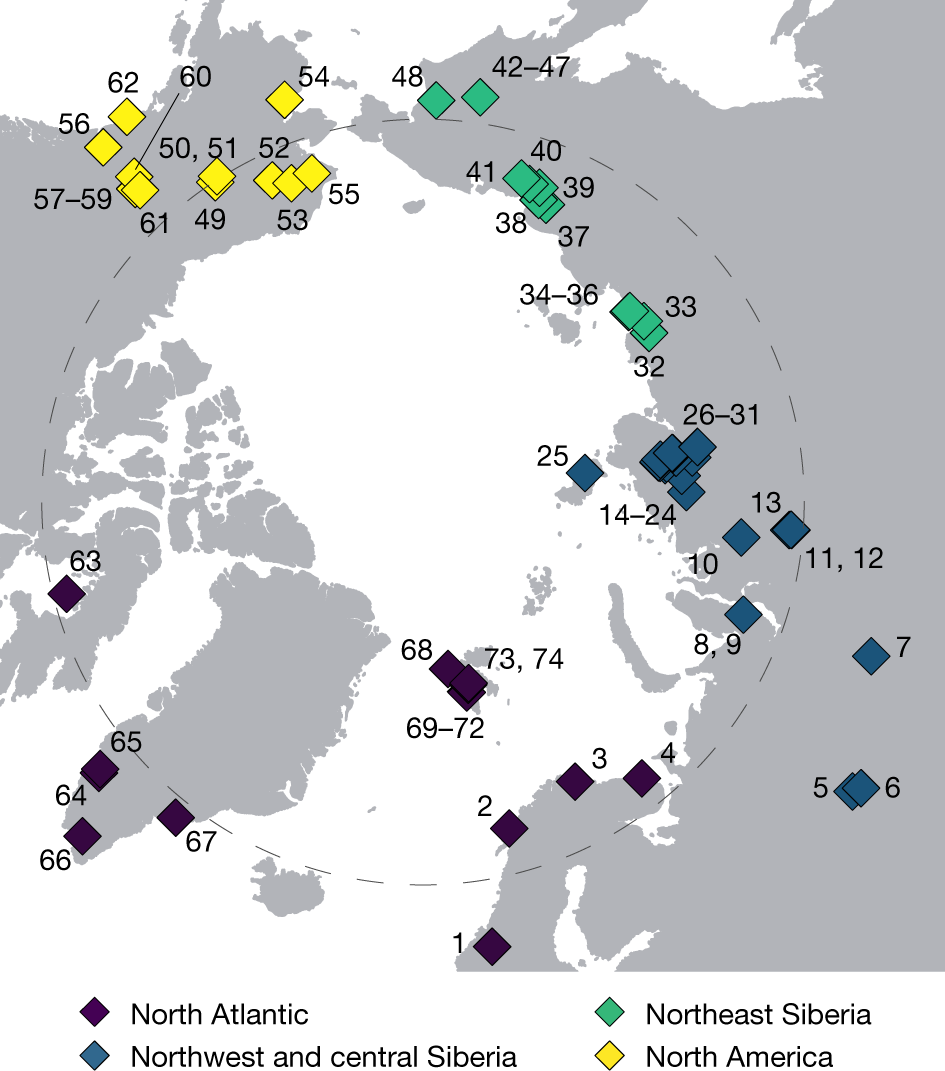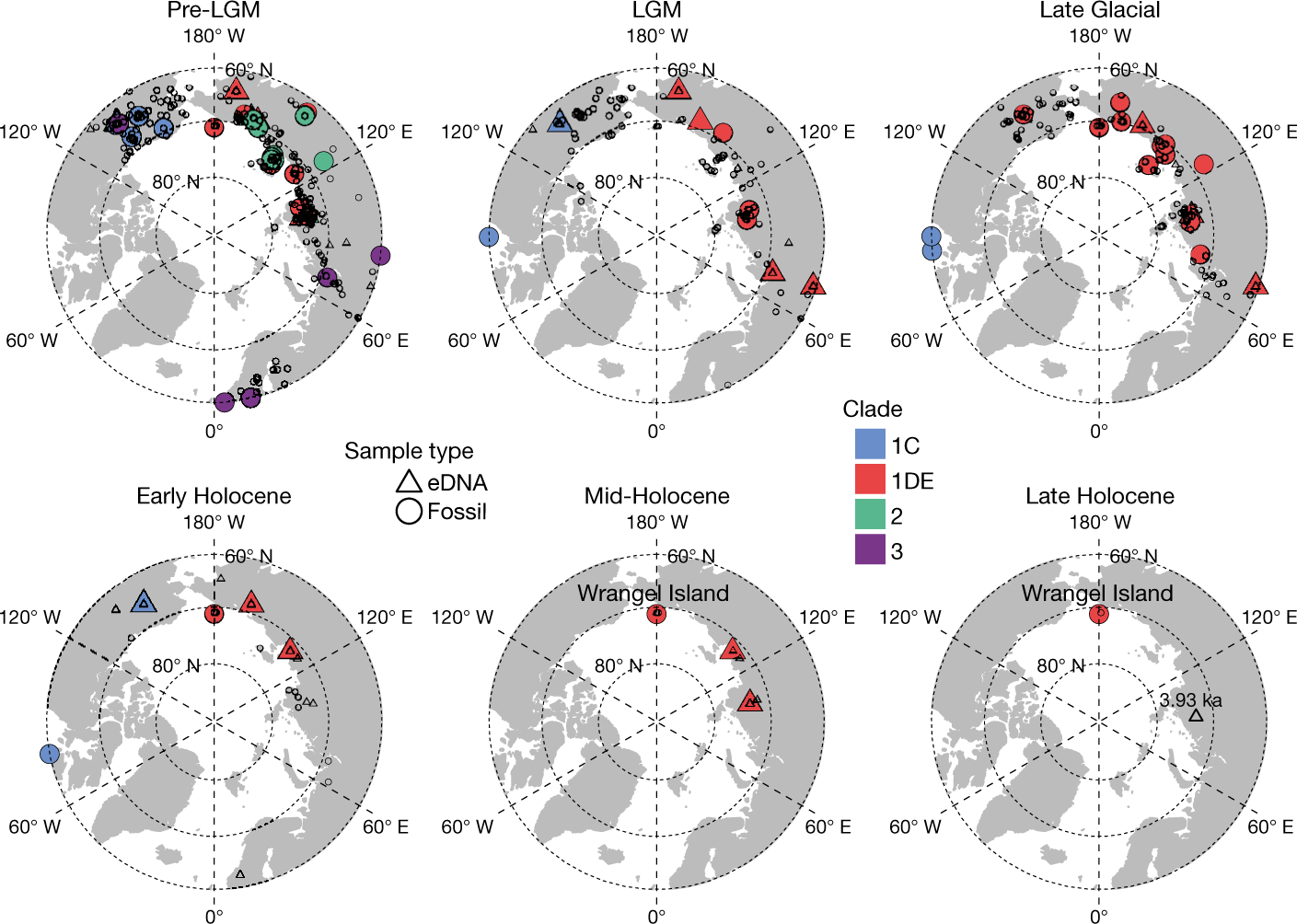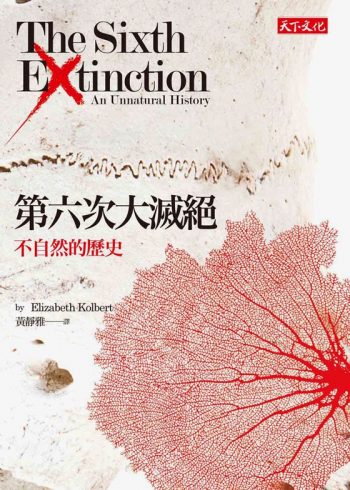 那些堅決相信是氣候變化害死大型動物群的研究人員,認為馬丁、戴蒙及強森所認定的事實並不正確。在他們看來,關於該事件的一切都尚未獲得證實,「斬釘截鐵」也罷,其餘別的說法也罷,全都太簡化了。滅絕的各個時間點並不明確;它們與人類的遷徙並非恰好齊頭並行;而且無論如何,相關性並非因果關係。也許他們最深切的疑問,是「原始人類致命性」的這整個前提。技術上還很原始的幾小幫人類,怎麼可能在澳洲或北美洲這麼大的地方,消滅這麼多巨大、強壯、有些還很凶猛的動物?
那些堅決相信是氣候變化害死大型動物群的研究人員,認為馬丁、戴蒙及強森所認定的事實並不正確。在他們看來,關於該事件的一切都尚未獲得證實,「斬釘截鐵」也罷,其餘別的說法也罷,全都太簡化了。滅絕的各個時間點並不明確;它們與人類的遷徙並非恰好齊頭並行;而且無論如何,相關性並非因果關係。也許他們最深切的疑問,是「原始人類致命性」的這整個前提。技術上還很原始的幾小幫人類,怎麼可能在澳洲或北美洲這麼大的地方,消滅這麼多巨大、強壯、有些還很凶猛的動物?
阿羅伊(John Alroy)是美國古生物學家,目前任職於澳洲麥覺理大學,他已經花了很多時間思考這個問題,認為這是個數學問題。「就繁殖率來說,非常大型的哺乳類其實活在危險邊緣,」阿羅伊告訴我:「舉例來說,大象的懷孕期為二十二個月。大象不會生雙胞胎,而且牠們要到十幾歲才開始繁殖。這些對於牠們繁殖有多快是很大很大的限制,即使一切都很順利。大象之所以能夠存在,完全是因為一旦動物體型大到某個程度,牠們就不會被捕食。牠們不再容易受到攻擊。以繁殖這方面來說,對牠們很不利,不過,以避免捕食者這方面來說,這倒是很大的優勢。可是當人類一出現,此優勢便蕩然無存。因為無論動物體型有多大,我們人類對於能吃的東西一向來者不拒。」
此乃另一個實例:幾百萬年來都行得通的妥協之道,突然間便行不通了。如同V 型筆石或菊石或恐龍,巨型動物並沒有做錯任何事;只不過是人類出現,「生存遊戲的規則」改變罷了。
阿羅伊曾利用電腦模擬來測試「過度殘殺」的假設[1]。他發現,人類可能並沒有在巨型動物身上花費太大功夫。「如果已經有某一物種可提供所謂的『可持續收成』(sustainable harvest),則其餘物種就算滅絕,人類也不會餓死,」阿羅伊指出。例如在北美洲,白尾鹿具有相當高的繁殖率,因此就算猛獁象的數量減少,白尾鹿數量也許仍然很充足:「猛獁象變成一種奢侈食物,你只能偶爾享用,就像是大松露一樣。」
阿羅伊針對北美洲進行模擬時,他發現,即使人類的初始人口很少(約一百人左右),在一、二千年的過程中,便可能倍增到足以解釋紀錄上幾乎所有的滅絕現象。這甚至是在假設人類只是「差強人意的獵人」情況下,所得出的結果。人類只需要伺機而行,每隔一段時間射殺一頭猛獁象或一隻巨型地懶,且保持這樣幾個世紀就夠了。這樣便足以迫使繁殖緩慢的物種族群開始減少,最終一路降到零。
強森針對澳洲進行類似的模擬,也得出類似的結果:假如每十個獵人一年只殺死一隻雙門齒獸,大概不到七百年,方圓幾百公里之內將找不到半隻雙門齒獸。由於澳洲不同地區被捕獵的時期可能不一樣,強森估計,整個大陸範圍的滅絕要花上幾千年。
對殺戮無感
從地球史的角度來看,幾百年甚至幾千年實際上根本不算什麼。然而,從人類的角度來看卻極為漫長。對於牽涉其中的人類來說,巨型動物的減少,緩慢到根本察覺不出來。他們不可能知道,幾個世紀之前,猛獁象及雙門齒獸曾經普遍得多。阿羅伊曾形容巨型動物的滅絕為「地質上瞬間發生的生態浩劫,卻緩慢到令引發它的人類渾然未覺。」他寫道,這表明人類「能夠迫使幾乎任何大型哺乳類滅亡,儘管他們也能夠竭盡全力,保證牠們不會滅亡。」[2]

一般認為人類世開始於工業革命,或甚至更晚,開始於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人口增長爆炸。根據此說法,隨著現代科技的引進(渦輪機、鐵路、電鋸),人類才成為改變世界的主力。但巨型動物的滅絕,表明情況並非如此。在人類出現之前,個頭大、繁殖慢是相當成功的對策,且超大型生物曾經主宰地球。後來,在相當於地質上的一剎那,此對策卻使牠們變成輸家。
現今情況依然如此,這就是為何大象、熊與大型貓科動物會處於極大的困境,以及為何蘇吉會成為世界上碩果僅存的其中一隻蘇門答臘犀牛。同時,消滅巨型動物不只是消滅巨型動物;至少在澳洲,這也掀起了一場生態骨牌效應,進而使地景改變。雖然想像「從前人類與大自然曾經和諧共存」或許很美好,但是否真的如此,沒人說得清楚。
本文摘自泛科學 2014 十二月選書《第六次大滅絕:不自然的歷史》,天下文化出版。
參考資料:
- John Alroy, “A Multispecies Overkill Simulation of the End-Pleistocene Megafaunal Mass Extinction,”Science 292 (2001): 1893-96.
- John Alroy, “Putting North America’s End-Pleistocene Megafaunal Extinction in Context,” in Extinctions in Near Time: Causes, Contexts, and Consequences , edited by Ross D. E. MacPhee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Plenum, 1999), 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