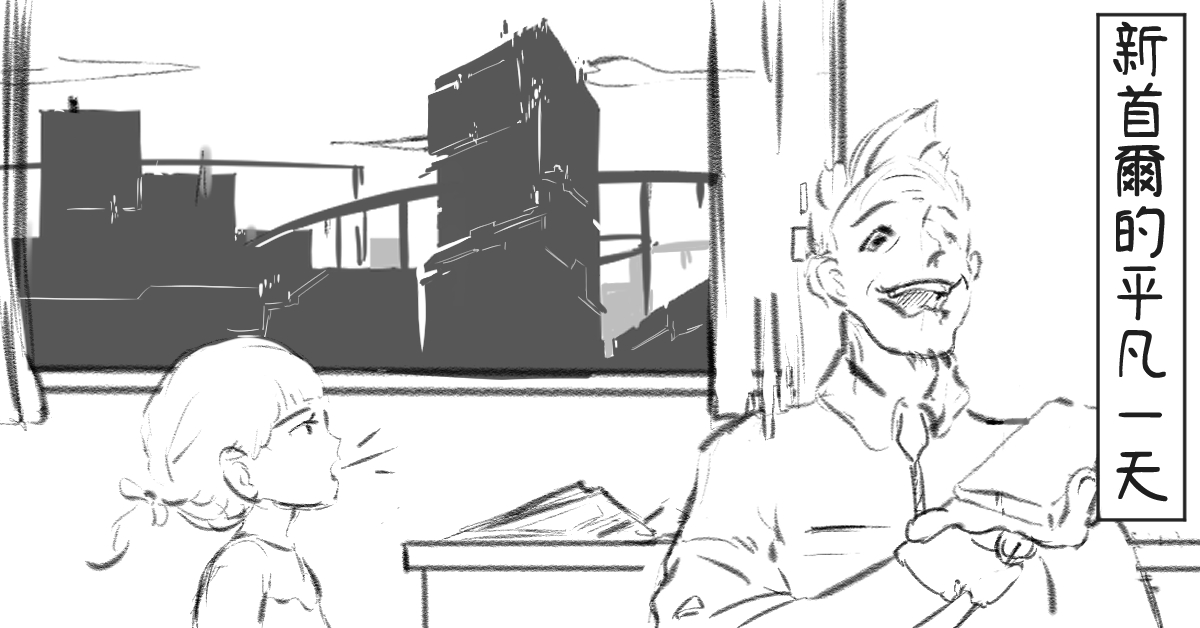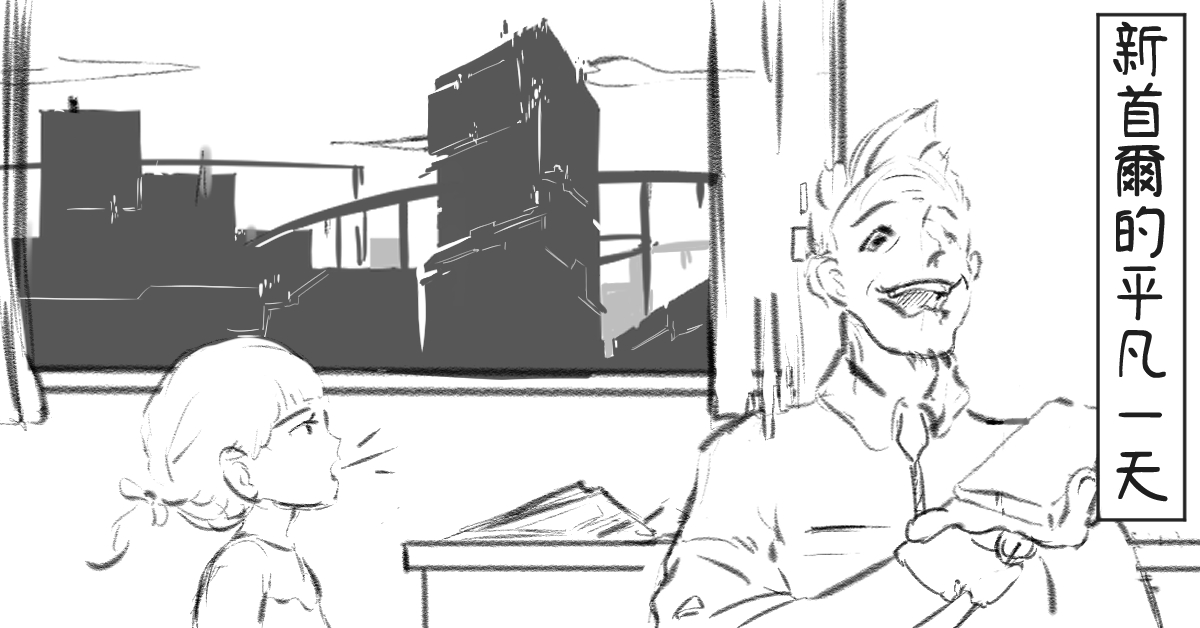A 編按:每周一、三、五晚上九點,泛科學將連載第二屆泛科幻獎的得獎作品!由於每篇得獎作品都是超過萬字以上的中篇小說,為了方便閱讀,我們把每一部作品拆成三個章節分別上傳,預計每週能看到一篇完整的得獎作品!
不想錯過連載?請密切鎖定泛科幻獎!如果想看前面的章節,可以點選標籤中的篇名,或是直接進入泛科幻獎帳號搜尋。

雙腳先騷動。接著眼皮開始掙扎,乏累的微微睜開。女作家的身體在疲憊之中慢慢往床裡沉沒,折斷了的神經關節在劇痛中一點一點的再連結起來。最後右手終於稍微提起來,好像是試著撐起身,被套盛載著千萬個無端掉落的皮膚分離層細胞一揚而起。
不知道睡了多久。是一天?還是一星期?這一刻,女作家無法記起來,只知道身體上的痛隨著意識恢復而爆發出來,像硬要擰動生了鏽的螺絲一樣。
在昏睡的時候,痛楚一直纏繞著她全身,她面孔乾癟,皮膚蒼白,頭殼裡腦袋卻活蹦亂跳,像滿溢著互相傾軋的電流。
她再使勁的睜開朦朧的雙眼,想要看清楚周圍。房間的牆壁貼上粉色的牆紙,窗簾上有玫瑰花圖案,看上去不像是醫院病房。是自己的睡房嗎?她又好像完全沒有印象。
當女作家確定自己還存在,感到自己仍在呼吸的時候,才發覺腦後接駁著一束束不知有什麼作用的電線。
或許是她醒過來觸動了淺睡中的電腦屏幕。一支從牆上伸出來的臂架,把屏幕輕巧地移動到她的面前。天花上的燈都關上了,淡淡的藍色微光映照到她的臉上。
「你忘記了吧,在你昏睡前,你同意讓我們連結到你的肉身。」M 的訊息在螢幕上傳來。
「你說,文學是一種病。這病帶來的痛逼著你去掙扎,能活,不能死。真正寫作,每一個字都等於向世界赤裸裸地揭開自己的靈魂。而你不滿意我們生成的作品,也是因為我們不懂得你的痛。」另一把聲音插了進來。
「你從我們的作品中明白到,你寫不下去是因為你變得麻木了,不能面對自己痛苦的記憶。」M 再說。
「不論我和你,要寫好的小說就用感官、用痛去寫,只有這樣才可以找回創作的靈魂。」她分不清是誰的訊息。
M敞開胸膛,裡面是一個鏡像文件,滿是片片段段的記憶,一個個畫面,一個個褪色的夢,好像永遠做不完睡不醒,扭曲的碎塊拉得長長的。一個文件打開了,M跟她的倒影一起進去不同的場景,不停放大、縮小、拖曳、複製每個畫面。所有的情節可以暫停、倒帶、快進。光影把時間割成流動的碎片,輸入神經網路的第一層,接著第一層的神經元將數據傳遞給第二層,第二層神經元再傳給第三層,一直傳到最後一層,逐片逐片移動,慢慢重組過來,然後又反復裂開。
她進入了另一個畫面。回到舊家。她四十歲的時候。
一張睡床從牆邊拉開來,她臉朝下趴在地上,在隙罅找到兩根微卷的長髮。床底下被陰影長年封住,陰森森的,永恆在沉睡中,有數不清被時間榨得枯萎的頭髮,逕自交纏在一起,像一束束曬乾了的海藻,中間夾雜著一些細碎的體毛。還有無數片已經消亡了,半透明的微細皮膚細胞,盤繞著纖維塵、砂塵、蟎蟲屍體,經年累月的黏到髮堆上,糾纏成一卷一卷灰白色的人體塵窩。
一天接著一天展開。她一直在地上匍匐。窗戶全部緊緊關上,幾線纖幼的晨光從窗簾之間的間隙透進來,在微弱的氣流裡映顯出細薄的塵埃。在這個靜止了,蒙上塵沙的空間,時間的代謝一直沒有停下來,只是步伐放慢了一點。她一手撐在地上,一手摸索床底下,一個晚上接著一個晚上掉下來的頭髮和人體皮屑。繞在一起的塵垢,每天徹底撿拾之後,到第二天總會再次發芽,在暗色中蔓延,再次長滿一地,攀缘到床腳上,牆腳上。
下一個場景在畫廊裡展開。地板、牆壁、天花都是一片純白色的空間,好像一個完全無縫的長方形盒子,射燈的光線分佈得那麼平均,影子全都消失了。
她隨著 M 站在窗邊,看著天台伸出來的起重機械臂,從地面把一個用帆布裹著的大型雕像缓慢地吊起來。椏杈狀的機械臂,拉著纖細的金屬吊索,像扯線木偶的表演一樣,動作靈巧地挑著它,在半空盤旋,投下一個拉長了,不合乎比例的黑影。玻璃幕牆的巨型橫拉門打開了,沉重的雕像一下子就鑽進室內,水泥地板隆隆地響了一下。
雕塑作品擺滿了展覽廳。她隨著 M 在展品之間徘徊。展覽廳只有她和天花上徐徐地轉動的監察鏡頭。一個個雕像都是那麼充滿戲劇性,軀體上交織著扭曲的邏輯,近乎歇斯底里的號叫,殘酷的暴力,充滿焦慮、苦痛的矛盾和衝突。那些互相交纏的玻璃纖維裡,雕像胸腹的骨架和內臟從裡面外翻了,胸腔從內裡掏空了,顛倒了,然後扭曲、壓縮了,表面的血管、神經、肌理暴烈地撕裂了,長滿了斷痕。
剛從外牆進來的大型雕像身上的帆布掀開了。一副由鋼線捏成的骨架,上面鋪蓋著一層一層人髮皮屑,肉身的朽爛殘餘、記憶的塵埃在混沌中蔓延,時間的蠶絲像煙霧般把骨架吞噬,裹纏出乾屍一樣的皮膚。一副輪廓糢糊、沒有眼神、沒有表情的面容,慢慢地浮現出來,脆弱得像睡與醒、意識與遺忘之間那道連結。
你忘記了這都是自己的作品嗎。有的確是很久很久以前的,M 對她說。
不知什麼時候,一個女孩站了在人像雕塑旁邊的陰影裡。女孩子是躲在那個大型雕像內一起進來的。她站在射燈範圍外的地方,纖小的身體若隱若現。
女孩忽然快步衝向一個沒有頭顱,沒有手臂的人像,使勁把它搖晃起來,快將推倒似的。
「你在做什麼!」她趕上去喝了一聲。
「你終於跟我說話了。」女孩說。「我不想看見你的痛苦,其他人也對你的痛苦沒有興趣,因為每個人自己都有自己揮之不去的寂寞痛苦。不要浪費時間自憐自艾,只是看見自己的苦難。」
她上前拉著女孩的手,二人扭作一團。天花的射燈打在女孩身上,她的輪廓像菲林顯影一般浮現出來。女孩身上的襯衫領口不整齊,頸背上露出密密麻麻的紋身,宗教符號一般的圖案和文字幖幟,一直伸延到襯衫下的背脊。
在激烈的肢體動作中,她倆凝固了下來。分離出來的抽象一剎那裡,分不清楚她們是在擁抱,互相撫摸,纏綿悱惻,還是在掙扎,在撕打,在吞噬對方。
女孩避開了她,揮舞左手,一下子就剖開了她的胸腔。女孩手臂皮膚上的紋身圖案蔓延到她的虛空的軀體。片刻間,她的內臟上面佈滿了細緻的紋身,還有潦草而纖弱的字體,顛倒的詞序,或是拼寫錯誤,或是互相矛盾,難以辨識。
她再與女孩拉扯起來。在激烈的掙扎聲中,空心的人像軀殼最後倒下了,落在地上,發出隆隆的,空洞洞的撞擊聲。
雕像橫臥在她們的腳下,紋身符號圖案的線條,變成瘟疫一樣,吞噬了她們原本的軀殼,血脈器官反到外面,有的互相傾軋,有的糾結在一塊,傾瀉一地。
女作家劇咳醒來,發覺自己躺在書房的沙發上,臉埋在毛毯下。她腹背痛得很厲害,眼前浮現一個紅色的暫停鍵,就伸手想按下去,卻沒辦法碰觸到。暫停鍵片刻間在空氣中消失了。
她硬撐著疲累的身軀坐了起來,再一次嘗試提起墨水筆。仍是無法落筆,最後把一沓空白的原稿紙棄掉。
案頭上仍堆積著一篇篇 M 未出版的文稿。她把一張張稿紙送進碎紙機。一條條割碎了、細細的廢紙很快滿了出來 。
她打開電腦。M 正繼續生成新的小說文稿。是一個完完全全M本身的創作。
她在電腦上翻來翻去,噼哩啪啦查找半天,取消了M與她的所有連絡,刪去整個生成器程式,重新安裝作業系統。
她放鬆了身體,在沙發上倒下來。
「恭喜你,我收到消息,《過渡》入選了小說雙年獎最後候選名單,而且很大機會得獎。」就在女作家刪掉生成器的一天後,女編輯再次來到女作家的家裡。
是哪部小說呢?女作家要想一想才記起來。一個濫藥墮落的女雕塑家與女兒關係破碎的故事。女雕塑家不斷在自傳式雕塑作品中揭示個人和家人生命中陰翳的經歷,苦難的墮胎和流產,真實的身體情慾,甚至不惜利用和女兒之間的隱密記憶和晦澀情感,結果傷害了女兒,做成不可挽回的悲劇,最後在餘生中沉溺於以手上擁有女兒的一切數據重塑她的身體雕像。
這本小說是 M 唯一令女作家感到不安的作品,彷彿把她層層疊疊的自我連結到卑賤的記憶之上。
「我看過你這三部新小說,很不錯呢,尤其是那部愛情小說,看來可以大賣。」女編輯從手提包中取出幾份文稿。
女作家翻了翻。那都是 M 的作品。
「我暫時沒打算把這個出版。」
「不會覺得很可惜嗎,小說不是已經大致完成了?不如這樣吧,我們可以再給你一個月整理一下這些稿件。」
「你怎樣得到這幾部小說?」女作家問道。
女作家早就猜到女編輯可能一直可以存取生成器在網路上的資料,也知道最近的小說有多少是她寫的,有多少是機器生成的。即使女作家取消了 M 與她的所有連絡,在自己的電腦上刪去生成器程式,編輯仍舊可以侵入實驗室的系統監察一切。
「老總希望在書展前為你推出新作。」女編輯取出一份合約和筆來。「你在這裡簽名就行了,審閱工作交給我們吧。」
女作家咳得面紅耳赤。
她明白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現在不能不讓女編輯繼續以她的名字出版這幾部小說。難道要公開這些年來她的作品都是幽靈作家代筆的嗎。
「我可以簽合約,但我會宣佈就此封筆,同時你要永久刪除 M 與我的所有連結,一切保密。」女作家拿起筆。「這些書可能也是我的遺著了,你們可以乘機發點死人財呢。」
兩天後,《過渡》獲得了小說大獎。與此同時,網上出現一批源頭不明的文件,揭露了女作家背後有幽靈作者代筆。
「文件不是我流出來的。老總要我立即向公司交代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女編輯發了一個訊息給女作家否認事件與自己有關。「我一直找不到實驗室的朋友,只刪除了一些檔案,無法完全關閉 M。」
訊息沒有人讀到。
女作家當天早上已在家中去世,死於電腦桌旁邊。
不知什麼時候,作業系統重新安裝好了,電腦在繼續運作。上面有一個資料匣,載有揭露幽靈作者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