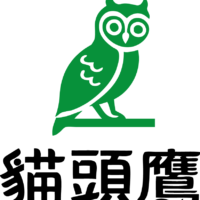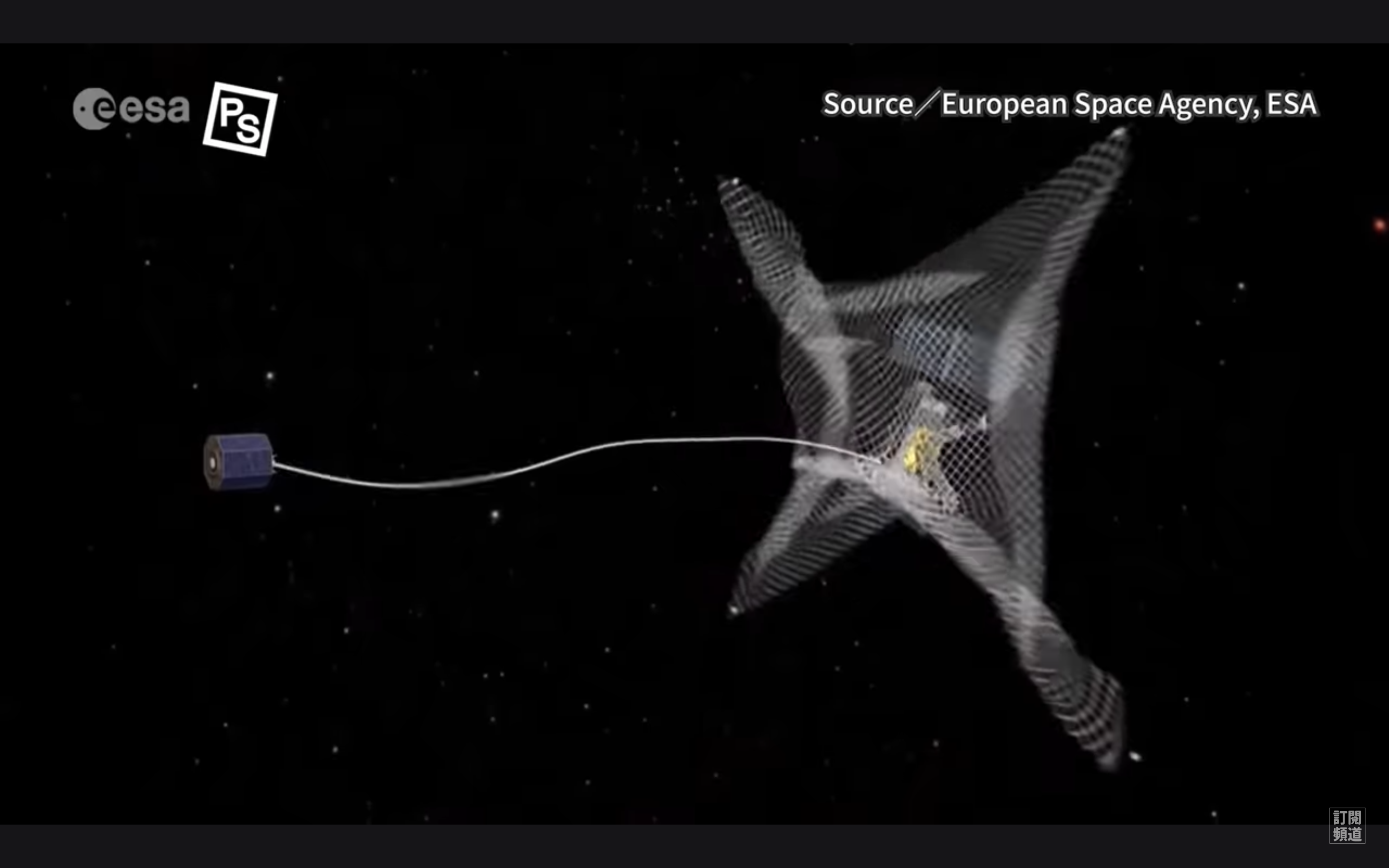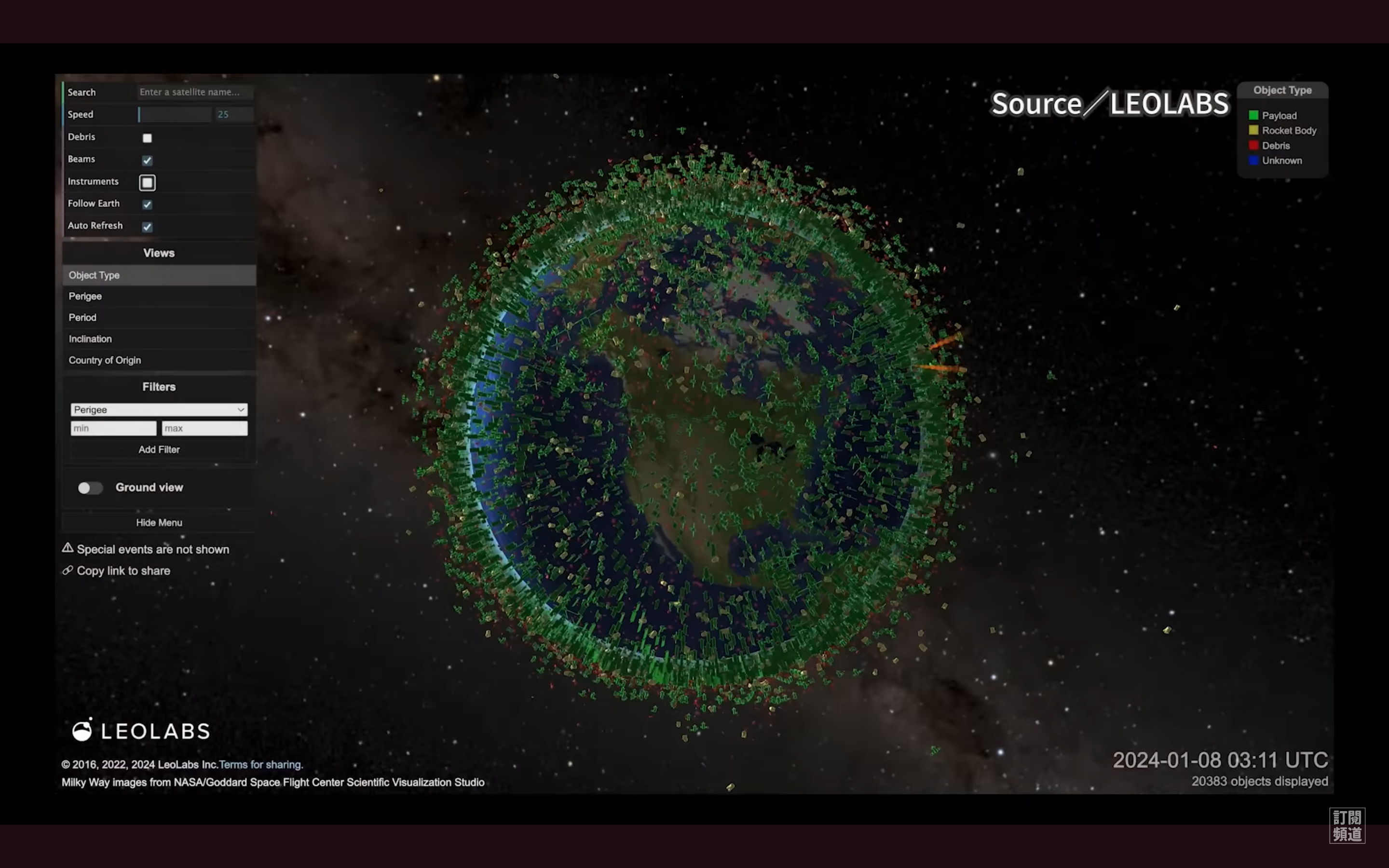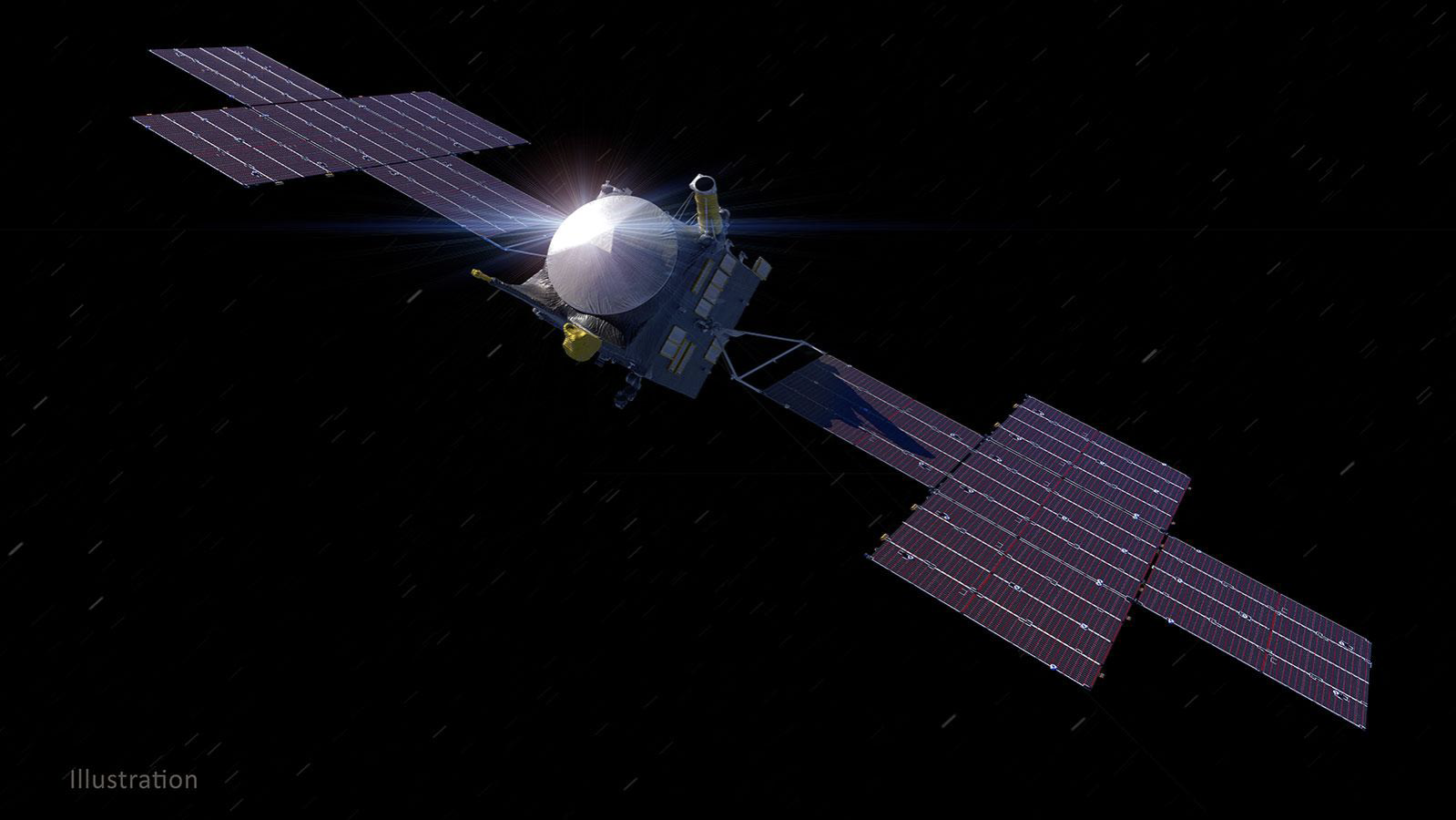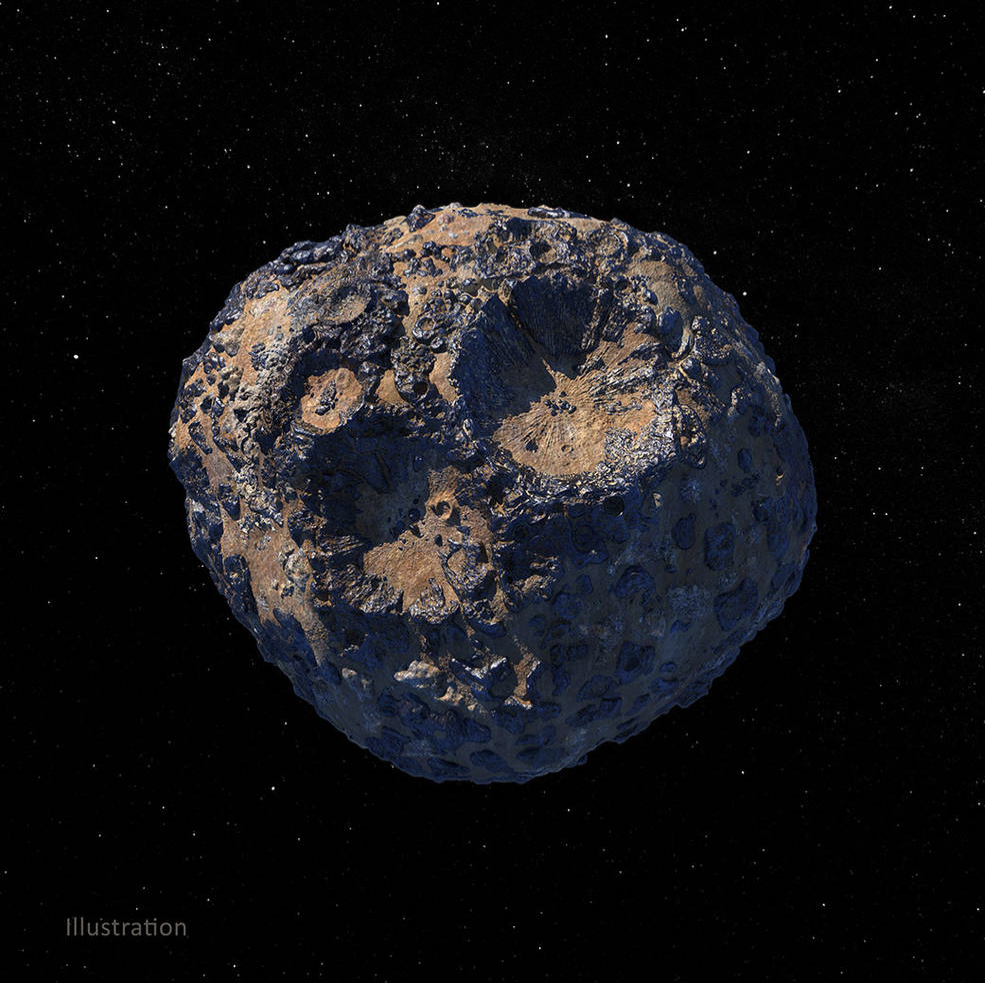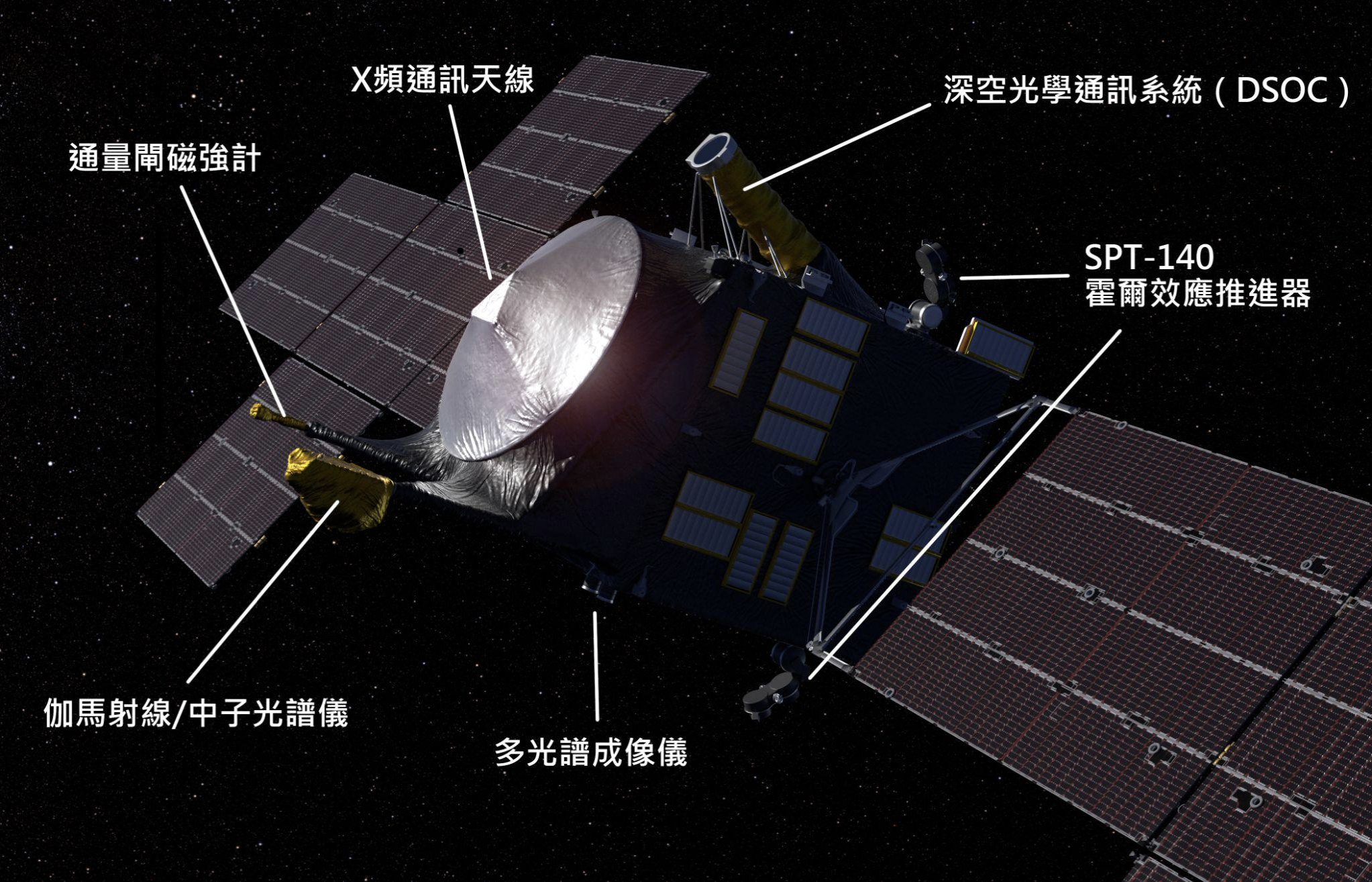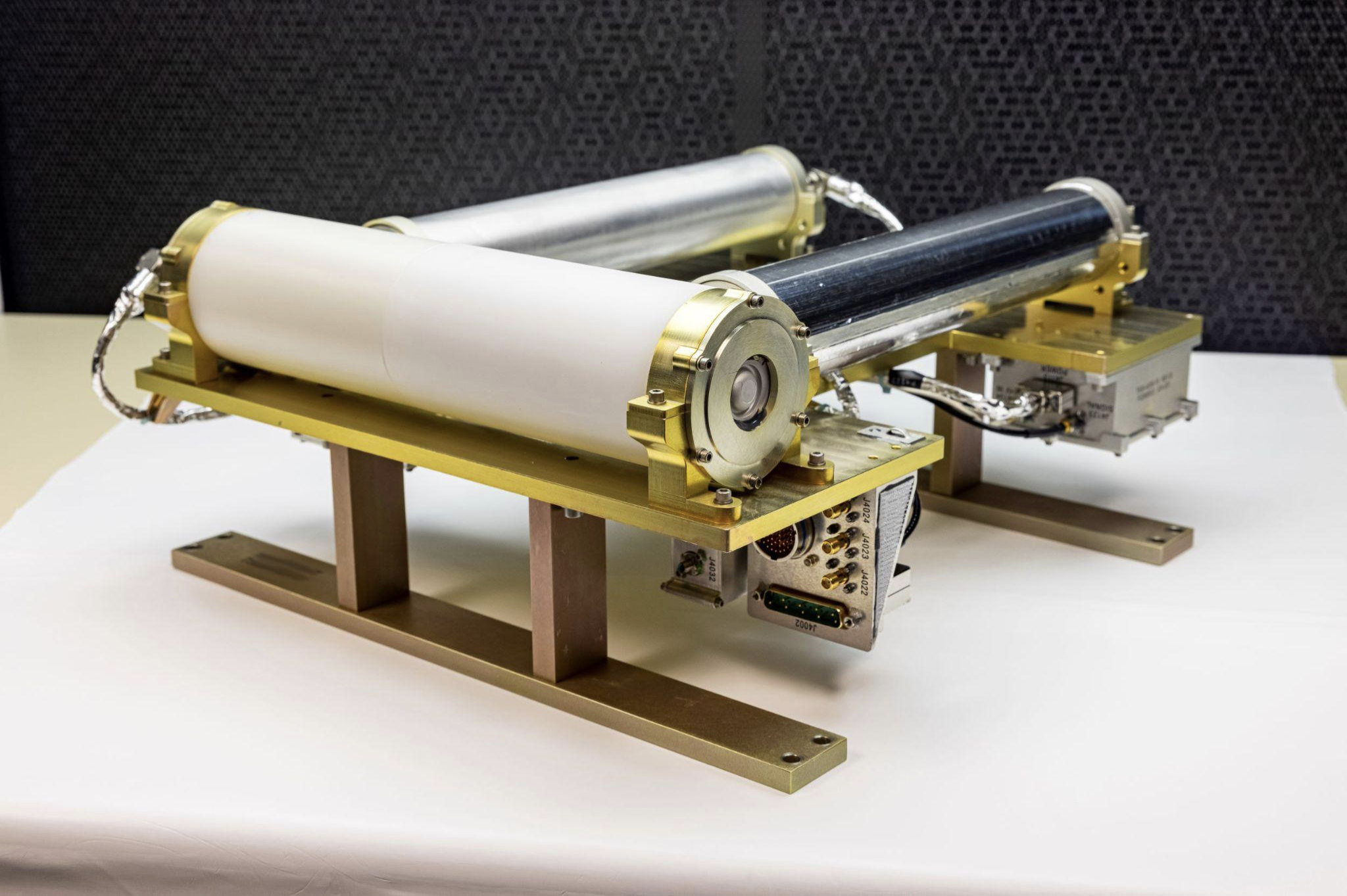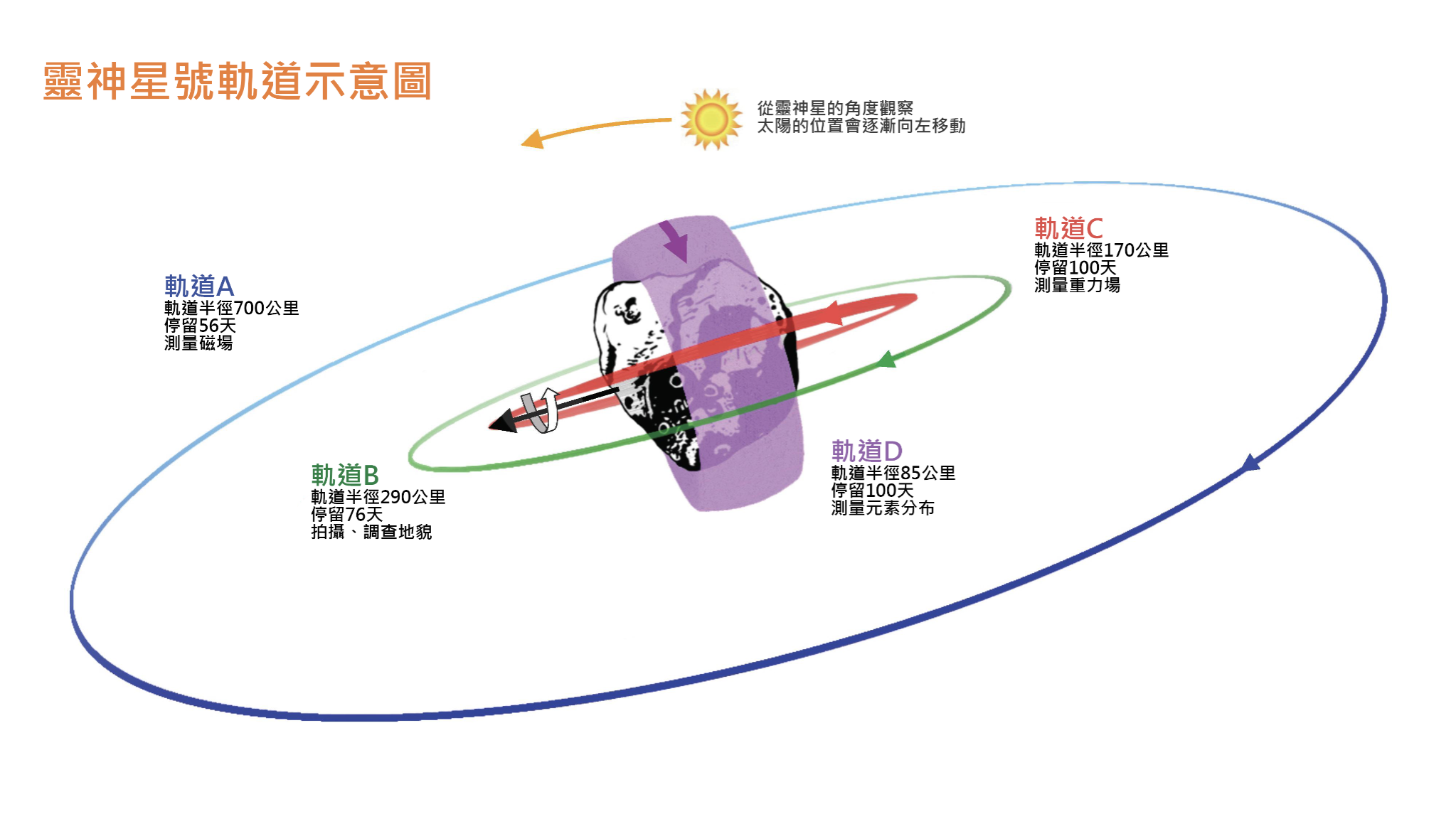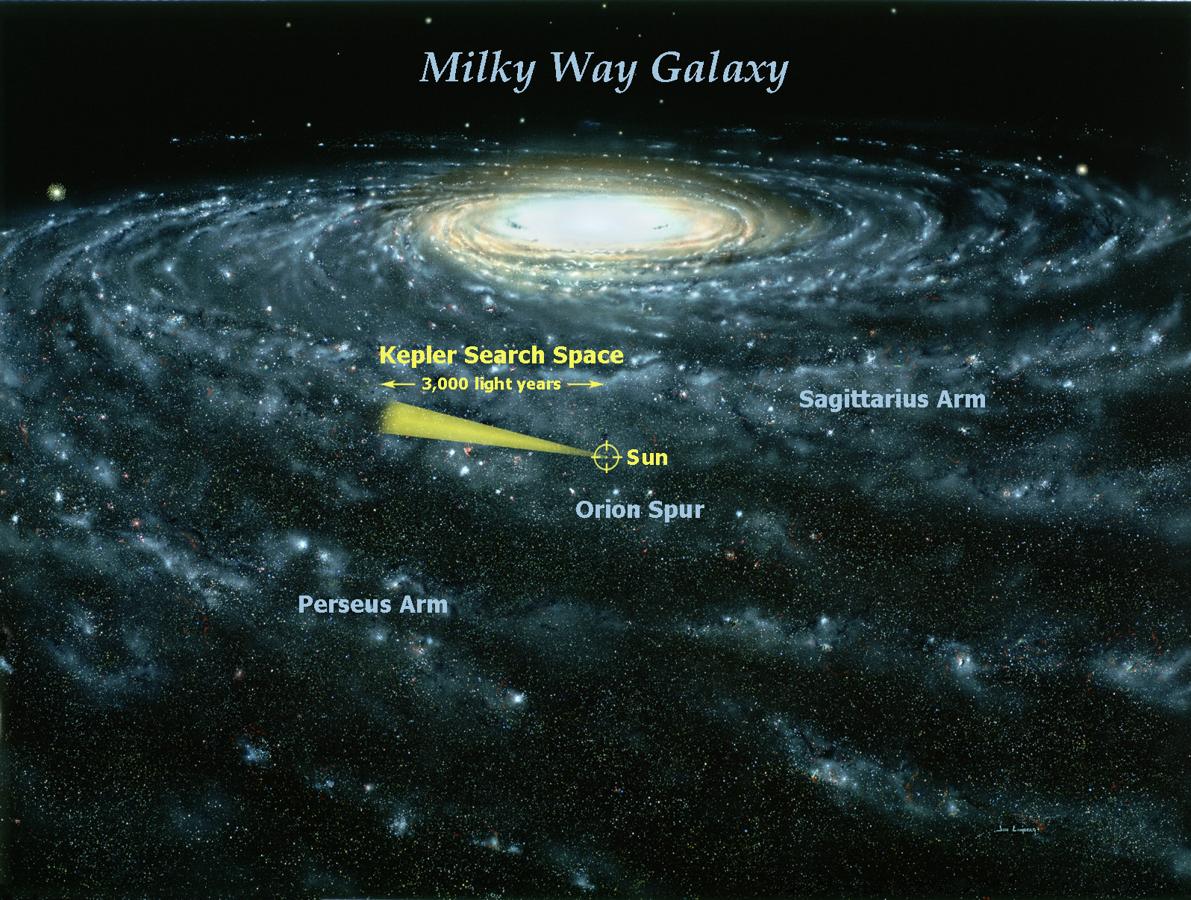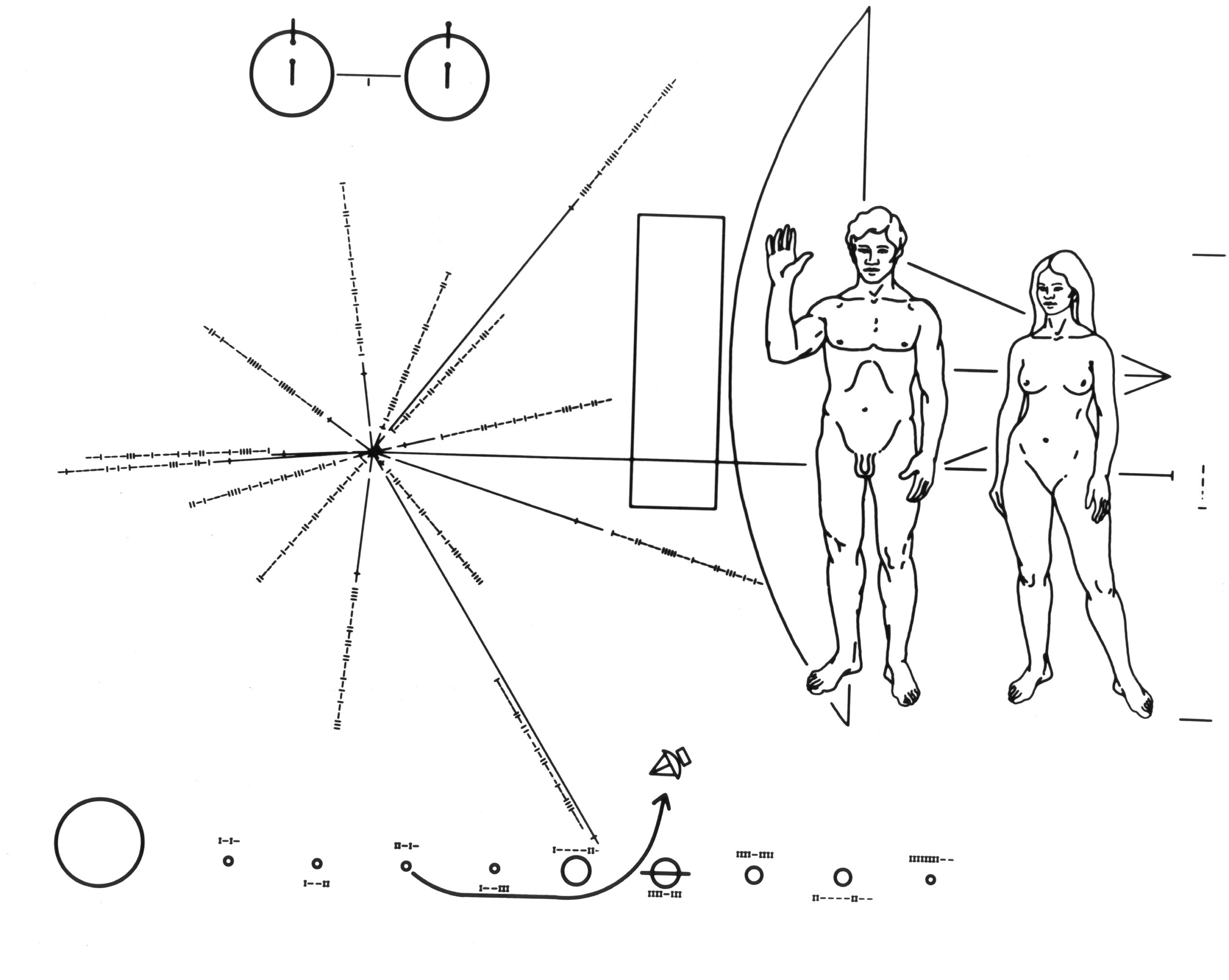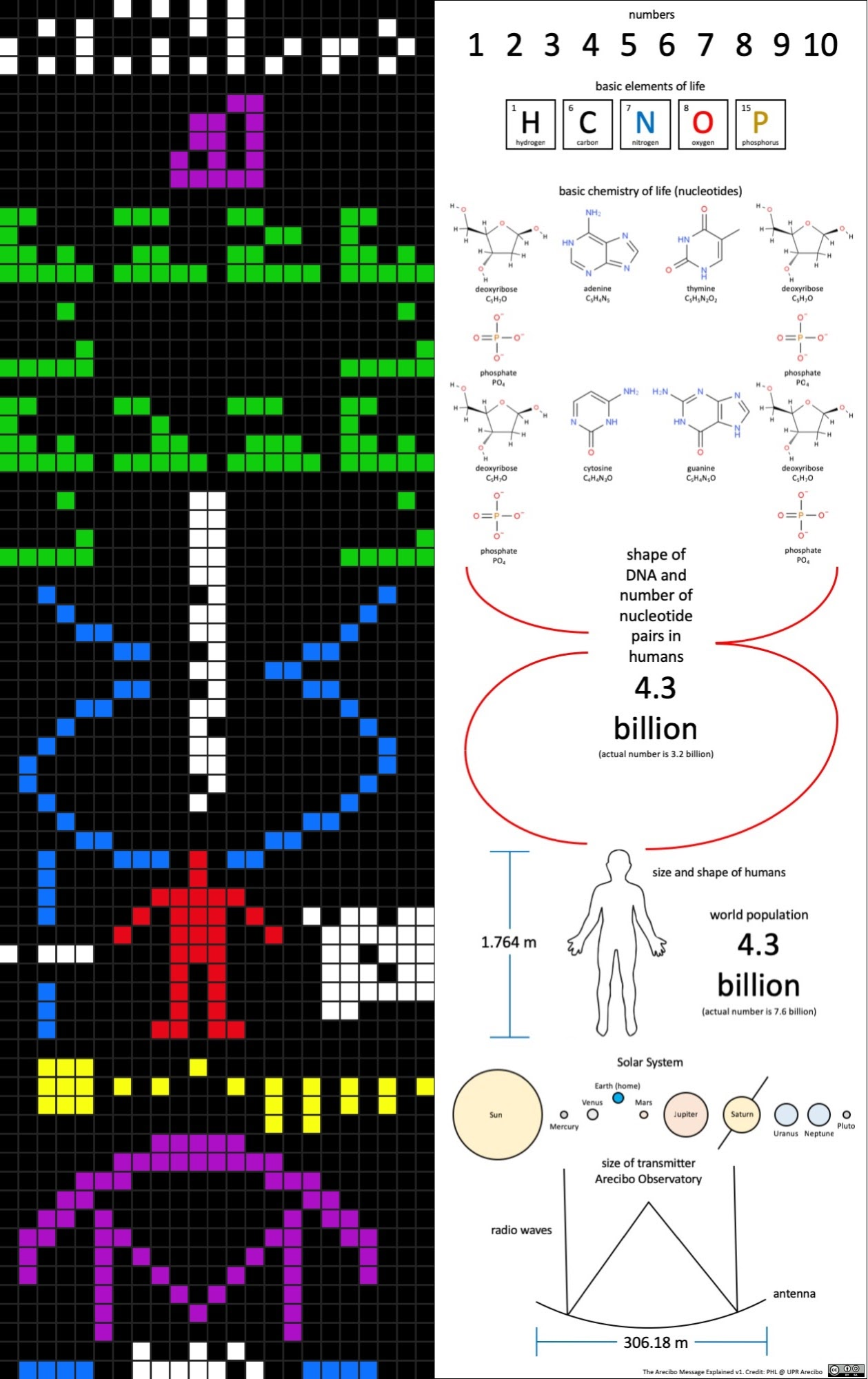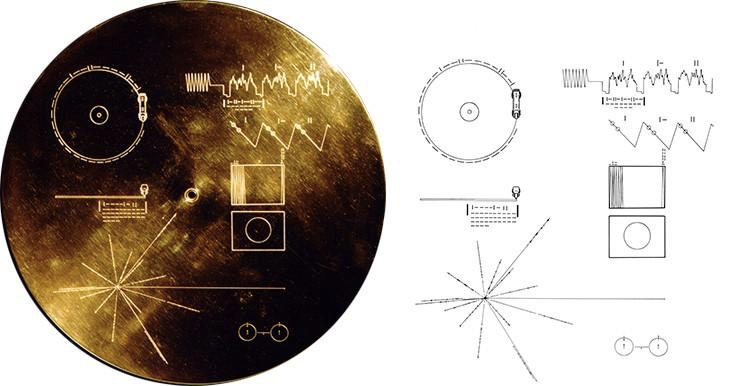對火箭科學家來說,你是個問題。你是他(她)得處理的機器中最麻煩的一台:你的新陳代謝不時變動,你的記憶體超小,你有一百萬種不同的配置架構,你不可預測,你反覆無常,你出了問題需要好幾周才能修好。工程師得為了你在太空中需要的飲水、氧氣、食物費盡心思,要注意為了送出你要的蝦仁沙拉與墨西哥牛肉餅需要多少額外的燃料。太陽能電池或火箭推進器既穩定又不難搞,這些東西不會排泄、恐慌或是愛上任務指揮官。它們沒有自我,結構成分也不會因為沒有重力就故障,就算不睡覺還是能運作良好。
對我來說,你是火箭科學裡最美好的一件事。因為有人類這部機器,所有的努力才具有無窮的吸引力。要把一個身上所有特徵都是以在有氧氣、重力、水的世界上生活與繁殖為目的演化的有機體,丟到荒蕪的太空裡一個月或一年,是既違反常理卻又讓人神魂顛倒的一項工作。所有在地球上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都必須重新思考、重新學習、一再演練─成年男女要學習上廁所,黑猩猩穿著飛行服被發射到太空軌道上,還有一個仿冒版的外太空在地球上,形成一個奇異的宇宙。從來沒有發射過的太空艙,健康的人在床上躺好幾個月的醫院病房,偽裝的零重力,還有用墜落的屍體模擬太空船降落海中情況的撞擊實驗室。
幾年前,我有一位朋友在美國太空總署(NASA)的詹森太空中心九號大樓進行一項工作。這棟大樓集結了各種模擬空間,一共約有五十多樣模擬設施:各種模組(構成太空船整體結構的各個獨立構造單元,例如乘員艙、指揮艙、駕駛艙等)、氣閘艙、艙蓋、太空艙等。我朋友雷尼連續好幾天,都聽見斷斷續續的「嘎吱嘎吱」噪音。最後他終於去找聲音來源,結果發現「一個可憐的傢伙穿著太空衣在跑步機上跑步,而且為了模擬火星重力,跑步機還懸吊在一個複雜的儀器上方。許多寫字板、計時器、無線電耳機,以及一張張憂心的臉龐團團圍繞著他。」當時我讀著他的電子郵件,突然覺得他所描述的場景,讓我不須離開地球就彷彿造訪了外太空;或者也可以說是某種胡鬧版的,超現實的,卻又要人信以為真的另一個版本的外太空。而我過去兩年大致上就是在這樣的地方度過。
對我來說,在數百萬頁為了第一次登陸月球而撰寫的文件與報告當中,最生動的莫過於一份在北美旗幟協會第二十六屆年會上發表的十一頁報告。雖然旗幟學是研究「旗幟」而不是研究「麻煩事」的學科(譯注:旗幟學的原文為 Vexillology,「惱人的」原文為 vexing,作者取其字首之雙關),不過在這場會議上,這兩項主題倒是都很適用。這份報告的名稱是〈旗幟未曾到達的地方:論在月球上插旗的政治和技術層面〉。
在阿波羅十一號發射前五個月舉辦的多場會議為這一切揭開序幕。新成立的「首次登陸月球象徵活動委員會」召開會議,討論在月球上插國旗的適當性。美國為簽署國之一的「外太空條約」禁止任何國家在天體上宣示主權,而「插國旗」有沒有可能不讓人覺得是某位委員所說的「主張擁有月球」的舉動呢?有人提出一項比較不適用於電視轉播的方案:使用盒裝的各國迷你國旗。但這項提議在經過考慮後被駁回了。美國國旗將在月球飄揚。
不過要是沒有NASA技術服務部門的幫忙,國旗也飄不起來。沒有風,旗幟就不會飄揚。月球上沒有所謂的大氣層,所以也沒有風。雖然那裡的重力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但已經足以讓旗幟不體面地垂頭喪氣了。所以他們在旗杆上方裝了一根橫桿,縫在國旗上緣,撐起整面國旗,這樣一來星條旗看起來就像在風中飄揚了─逼真到引發了後來數十年關於登陸月球是一場騙局的爭議。事實上這面國旗比較像是一幅縮小版的愛國窗簾,而不是一面旗幟。
挑戰還沒結束。你要怎麼把旗杆塞進登月艇狹窄、擁擠的空間裡?於是工程師動手設計了可摺疊的旗杆與橫桿,但即使如此,空間還是不夠。這個由國旗、旗杆、橫桿組成的「月球旗幟組」最後只能裝在登月艙的外側,但這也表示它必須能夠承受旁邊下降引擎產生的華氏兩千度高溫。為此他們展開許多測試,因為國旗在三百度時就會融化,所以結構與機械部門也被找來,用多層鋁和鋼做出了一個隔熱保護殼。
就在這面國旗看似終於準備妥當的時候,有人指出太空人因為都要穿加壓的太空裝,所以手部抓取的力量有限。他們到時候有沒有力氣把旗幟組從隔熱殼裡拿出來呢?他們會不會在數百萬人的注視下,想抽出旗幟組卻徒勞無功地站在那裡?他們有沒有足夠的空間來撐開摺疊的構件?只有一個方法能知道答案:製作旗幟組的原型,召集登月團隊來進行一系列使用旗幟組的模擬訓練。
這天終於來了。國旗在品管主管的監督下以四個步驟打包完成,再以十一個步驟裝上登月艙,出發前往月球。但折疊橫桿在月球上無法完全伸展,而且月球的土壤又太硬,阿姆斯壯只能把旗杆插進土裡十五到二十公分深,因而引發揣測,認為國旗可能被上升模組的引擎給吹爛了。
歡迎來到太空。我要說的不是你在電視上看到的那些成功與悲劇,而是中間的那些小小的喜劇以及日常的勝利。我之所以有興趣寫「太空」這個主題,不是因為那些英勇的冒險故事,而是背後那些人性化,有時甚至顯得荒謬的辛苦努力。一位阿波羅號的太空人因為早上練習太空漫步時嘔吐,所以擔心自己會拖累美國在登月競賽中成為輸家,引來是否擱置此計畫的討論;第一位進入太空的蓋加林走在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前的紅地毯上,接受成千上萬人的喝采時,突然發現自己的鞋帶沒綁好,於是腦袋一片空白。
在阿波羅計畫的尾聲,太空人接受訪問,針對各種主題提出他們的想法。其中一個問題是:如果一名團隊成員在船艙外太空漫步時死亡,你該怎麼做?其中一個選項是:「切斷他的連結繩。」大家都同意這個答案。因為試圖從太空中救回屍體,將會危害到其他成員。只有親身體驗過穿著加壓的太空衣,千辛萬苦進入太空艙的人,才能毫不猶豫說出這樣的答案。只有曾經毫無束縛地在無邊無際的宇宙中漂浮過的人,才能了解太空葬禮之於太空人,如同海中葬禮之於水手,代表的是榮耀而非不敬。在軌道上的所有事物都與地球上全然不同,流星在你下方呼嘯而過,留下一道痕跡,太陽會在午夜升起。就某些方面來說,探索太空是探索這個行動本身對人類的意義。人願意為此背棄多少「常態」?這種狀態能維持多久?對他們又有什麼樣的影響?
在研究初期,我碰巧讀了雙子星七號的任務紀錄─第八十八個小時裡的四十分鐘。對我而言,這段紀錄不僅總括了太空人的經驗,也說明了我為什麼對此深深著迷。太空人洛威向任務控制中心回報他拍攝到的一個影像,任務紀錄這麼描述:「一張美妙的照片:滿月掛在漆黑的天空中,下方是地球雲系的高層結構。」片刻的沉默後,洛威的同伴鮑曼按下了通話鍵:「鮑曼要去倒尿液了。大約一分鐘後排出。」
在後面兩行,我們看到洛威說:「真是奇景!」我們不知道他指的是什麼,但他說的很有可能不是月亮。多位太空人都在回憶錄裡提到,太空中最美的景象,是迅速凍結的廢水滴飛散在太空中被太陽照亮的模樣。太空不只同時包含了壯麗與荒謬,還抹去了兩者的界線。
摘自《打包去火星:太空生活背後的古怪科學》前言 〈倒數計時〉。本書由貓頭鷹出版社出版,獲2012年8月PanSci選書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