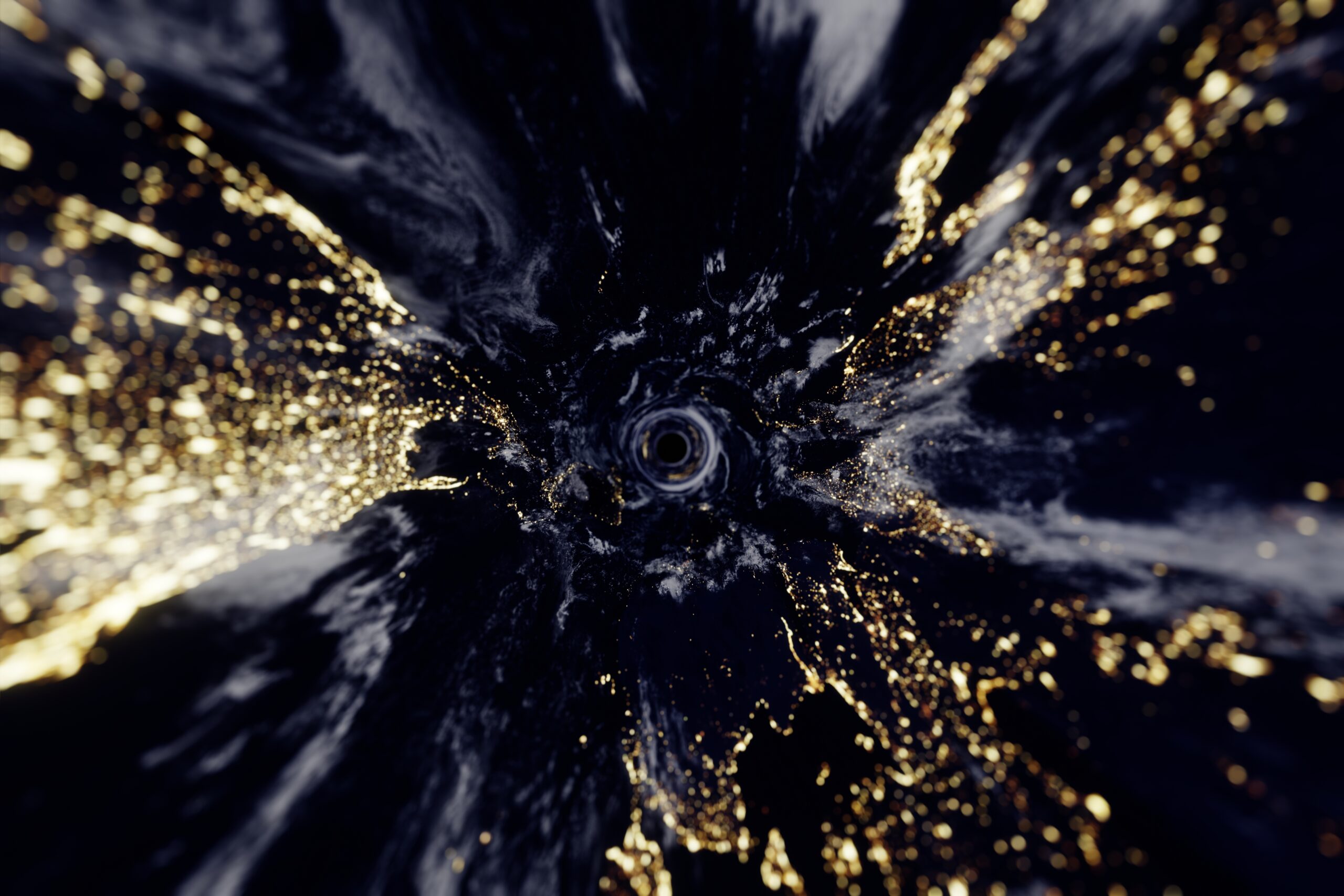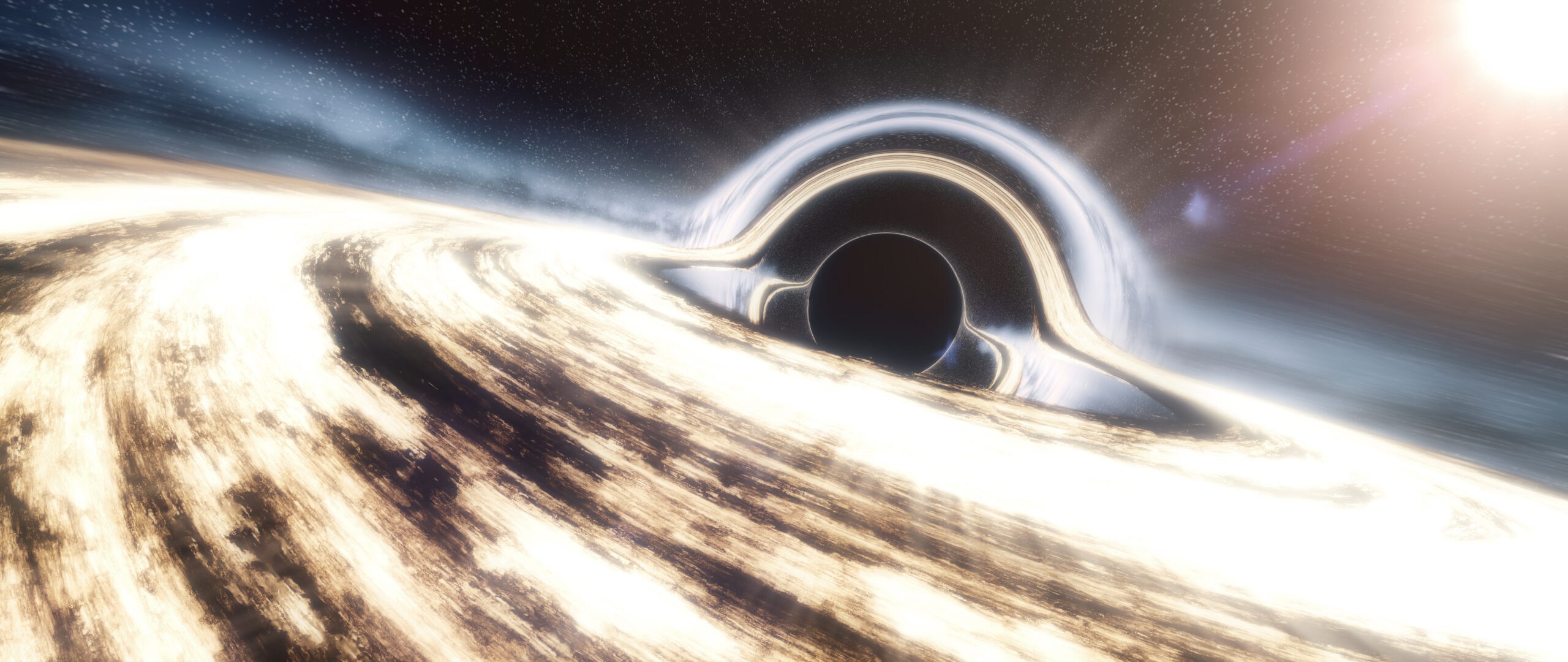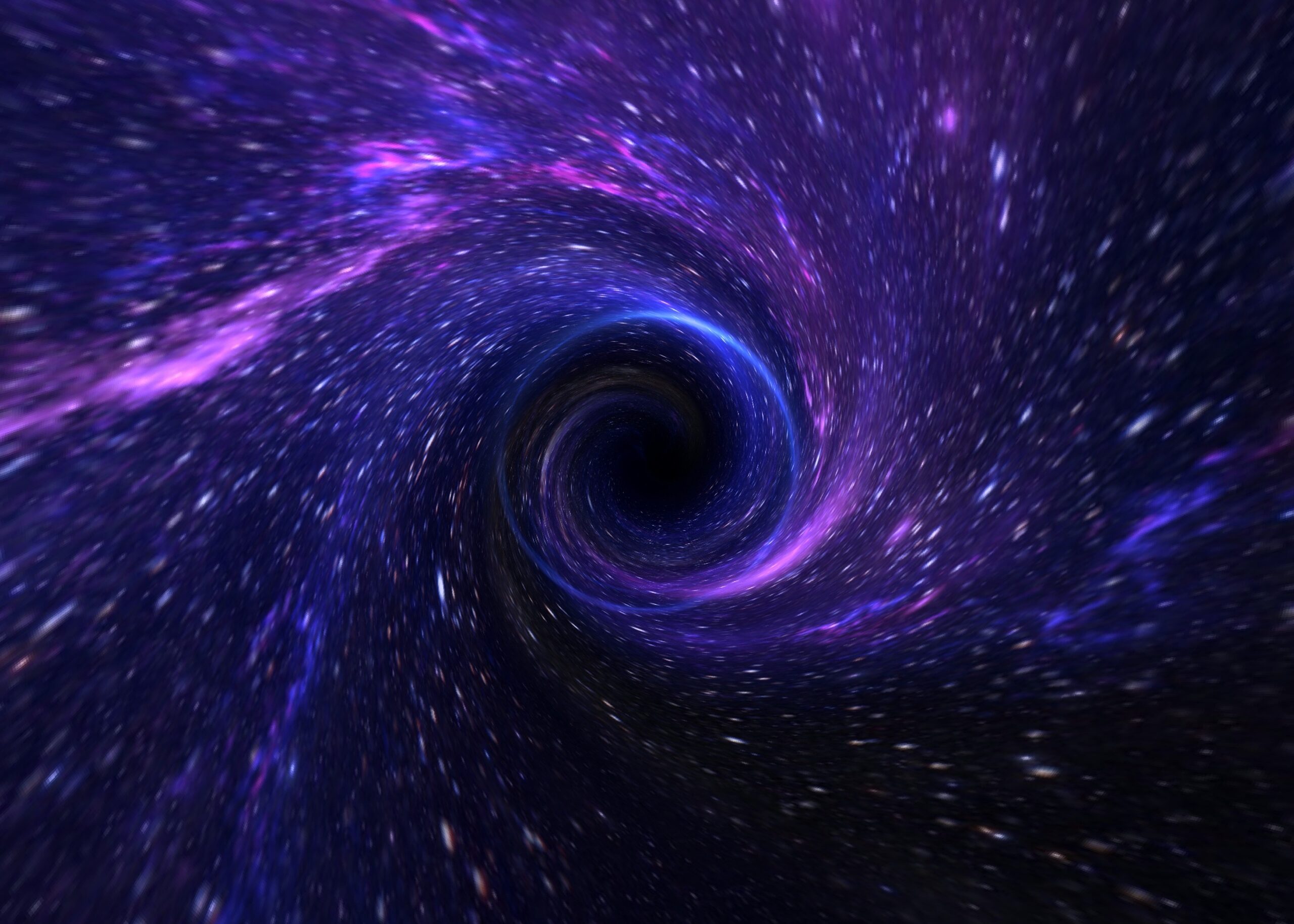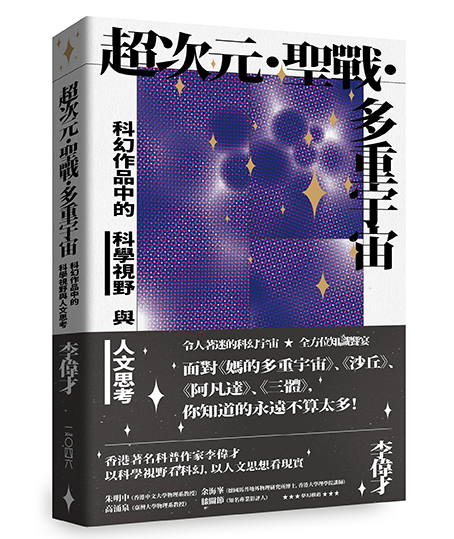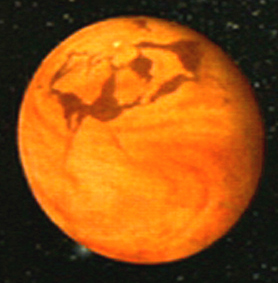- 作者: 娥蘇拉.勒瑰恩 Ursula K. Le Guin
譯者: 劉曉樺
編按:本文轉載自娥蘇拉.勒瑰恩短篇小說集《風的十二方位》,由勒瑰恩自選17個短篇,收錄每篇故事的自我點評與花絮、起源與軼事。
〈師傅〉是我所有出版作品中第一篇貨真價實、千真萬確、如假包換的科幻故事。這是指,在故事中,科學的存在與實現在某層面來說是不可或缺的。起碼我對科幻小說的定義在星期一是如此,到了星期二,可能又會有所不同。有些科幻小說家是厭惡科學的。厭惡它的精神、它的方法還有成果,有些人則很喜歡。有些作者反科技,也有些作者崇拜科技。我對複雜的科技興趣缺缺,但對生物學、心理學,以及天文學和物理學的推想性都很是著迷——只要還在我的理解範圍內。科學家的角色在我的故事裡時有所見,而且往往是寂寞的、離群索居、充滿冒險精神、勇於求新求變,探索新的可能。
這篇故事的主題後來又再次出現在我的作品中,並且是帶著更好的題材與準備。不過,這篇裡有個很不錯的句子:「他試圖丈量塵世與上帝間的距離。」

一名男子獨自佇立於黑暗之中,全身上下一絲不掛,唯有手裡舉著根冒煙的火炬。紅色的火光僅僅照亮了前方幾英尺的空氣與地面,在那之後,唯有漆黑,無止無盡。時不時會有一陣風颳過,灼亮的目光一閃而逝,嘟噥聲自四面八方響起:「舉高些!」男人遵從了,只是火炬在他顫抖的手裡簌簌哆嗦。
他將火把高舉過頂,黑暗在他身旁匆匆流竄,喃喃低語,逐漸收攏逼近。風變得更冷了,紅色火光搖曳不定,他僵硬的手臂開始發起抖,微微抽搐了一下,臉上蒙著一層汗水的油光。他只勉強聽見那輕柔又廣大的模糊低語:「舉高,再高、舉高點……」
時間停止流逝,只有低語聲越來越大、越來越響亮,直到化為吼叫,不過還是同樣令人膽顫心驚,沒有任何東西觸碰他,沒有任何東西出現在火光照耀的範圍。「現在,快走!」那雄渾的聲音咆哮,「往前走!」
他將火炬舉在頭頂,朝著看不見的地面跨出腳步。但地面消失了。他發出求救的慘叫,向下墜落,黑暗與雷聲籠罩四周。他不願鬆開手中的火炬,烈焰向後席捲,朝他雙眼燒來。

時間……時間、光芒、痛楚,全都再次襲來。他趴在某種溝穴內,四肢陷在泥濘中,不僅臉上傳來陣陣刺痛,雙眼也因明亮的光芒白霧而迷濛。
他將視線轉離自己骯髒赤裸的軀體,望向站在上方一個朦朧發光的身影。耀眼的光華灑落在白髮及白袍的長長褶層上,那雙眼凝視著甘尼爾,那聲音開口對他說:「你躺在墳墓裡。你躺在知識的墳墓裡。你的先祖永永遠遠躺在地獄之火的灰燼下。」那聲音變得更加響亮,「喔,墮落的人類,起來吧!」甘尼爾設法站了起來。
那白色的人影又指著某樣東西道:「那是人類的理性之光,它引領你來到這座墳墓。扔了它吧。」甘尼爾這才發現自己仍握著一根沾滿泥濘的黑棍,是那支火炬。他鬆開手。「現在,起來吧。」白色人影緩緩欣喜呼喊,「自黑暗中起身,走進共世時代的光芒之下!」
一雙雙手朝甘尼爾伸來,協助拉他出土坑。幾名男子跪在地上,遞出水盆與海綿,其他人用毛巾裹住他,替他擦乾身軀,直到他全身上下溫暖乾淨。現在,他肩上披了件灰色斗篷,站在一間寬敞明亮的廳堂內,身旁人來人往、笑語連連。一名光頭男子拍了拍他肩膀。「來吧,該宣誓了。」
「我——我表現得還好嗎?」
「很好!只有你能舉那根該死的蠢火炬那麼久,我還以為你會讓我們在黑暗中吼上一整天咧。來吧。」眾人領著他穿越黝黑的地面,經過一面非常挑高的白桁天花板,來到一幅純白色的垂幕之前。簾幕上有幾道筆直的皺褶,從天花板到地板足足有三十英寸長。「是祕學之幕。」有人用一副就事論事、冰冷平淡的口吻對甘尼爾說,笑聲與交談聲都靜了下來。他們全站在他身邊,一聲不響。靜默中,白幕拉開,甘尼爾恍恍惚惚地看著幕後揭露之物:一座高壇、一張長桌,還有一名白衣老者。
「志願者,你願意與我們一同宣誓嗎?」
有人用手肘頂了頂甘尼爾,低聲道:「我願意。」
「我願意。」甘尼爾結結巴巴道。
「那就宣誓吧,儀式師傅們!」老翁舉起一枚銀色的物品,那是個由鐵軸所支撐的X型的十字架。「以共世時代的十字架之名,吾發誓永不洩露所屬會所之儀式與祕密——」
「以……十字架之名……吾發誓……儀式……」甘尼爾身旁所有人都開始喃喃低語,又有一隻手肘頂了頂他,於是他跟著一起念。
「吾將擁有健全的生活、健全的工作、健全的思想——」甘尼爾複誦完後,又有個聲音在他耳畔低語:「別發誓。」
「吾將效忠教廷學院,阻絕所有異端邪說、斷離所有術士巫覡,並從此刻起遵從會所上師教誨,至死方休——」更多低語聲。有些人似乎跟著念完了冗長的句子,有些人沒有。一頭霧水的甘尼爾喃喃念了幾個字,然後便靜靜站著不動。「吾發誓永不將機械的祕學教授予任何非教徒。吾在太陽之下做此宣誓。」一陣刺耳的隆隆聲幾乎要把他們的聲音淹沒。部分的天花板開始緩緩地、顫抖地往後掀開,露出夏季雲層密布的黃灰色天空。「看吶,是共世時代的光芒!」白衣老者發出勝利的呼喊。甘尼爾抬頭仰望,顯然,那機械裝置在天窗完全打開前就卡住了。齒輪的碰撞聲轟然響起,靜默緊接而至。老者上前,親吻甘尼爾雙頰,說:「歡迎,甘尼爾師傅,歡迎來到機械祕學的祕密盛典。」入會儀式結束。甘尼爾現在也是他所屬會所的一名師傅了。

「你被燒得可真慘。」眾人走回大廳時,那名光頭夥伴這麼說。甘尼爾伸手摸了摸,才發現自己的左頰和太陽穴都紅腫灼痛。「幸好沒燒到你眼睛。」
「剛好逃過一劫,沒被理性之光燒瞎了眼,是嗎?」一個輕柔的聲音說。甘尼爾環顧四周,看見一名棕髮藍眼的白膚男子,而且他瞳孔是如假包換的藍,就像得了白化症的貓或瞎眼的馬才有的那種藍。他立刻把目光從對方的殘畸部位上轉開,但這名白膚男子只是用他那輕柔的口音繼續說道。宣誓時低聲警告他「不要發誓」的也是這個聲音。「我是米德.費爾曼。我將在李的作坊和你一同擔任師傅。離開這兒後想不想去喝杯啤酒?」
經過白天那些可怕的體驗和儀式之後,酒館內瀰漫混濁啤酒味的溫暖與潮溼感就像某種奇異的改變。甘尼爾只覺頭暈目眩。米德.費爾曼乾了大半杯啤酒,快活地抹去脣邊的泡沫,問:「你覺得這入會儀式怎麼樣?」
「很——很——」
「很令人敬畏?」
「對。」甘尼爾附和,「真的很令人敬畏。」
「甚至覺得有點羞辱?」藍眼男子試探道。
「對。非常——非常偉大的一個祕密。」甘尼爾茫然地瞪著自己的酒杯。米德微微一笑,用他那輕柔的聲音說:「我懂。喝吧。你該找個藥師治治你的燒傷。」
甘尼爾乖乖跟著他走進暮靄之中,踏上窄仄的街道。街上行人摩肩擦踵,馬車、牛車、嚓嚓作響的機動車擠得水洩不通。市集內,工匠們收拾起自己的攤子,準備打烊。主街上,作坊與會所的大門都已牢牢掩上。到處可見櫛比鱗次的突出房舍,被聖堂的黃色牆垣所隔開,空盪的牆上只有一個用閃亮黃銅做的簡單圓形標誌。
在夏季沉悶短暫的黃昏與動也不動的雲層下,共世時代古銅色肌膚的黑髮子民或群聚、或無所事事、或推擠、或交談、或咒罵、或說笑。而被疲憊、痛楚與烈酒搞得頭昏眼花的甘尼爾只是緊緊跟在米德身旁,彷彿即便自己升任成為了師傅,這名陌生的藍眼男子仍是唯一能指引他的方向。
「 XVI 加 IXX ,」甘尼爾不耐煩道,「搞什麼,臭小子,你連加法都不會嗎?」學徒一下漲紅了臉。「結果不是XXXVI嗎,甘尼爾師傅?」他小聲地問。做為回答,甘尼爾直接拿起男孩為了修理蒸汽引擎製作的桿子,卡進它該放進的位置,結果是長了一英寸。
「師傅,那是因為我做為丈量標準的大拇指太長了。」男孩舉起他指節突出的雙手。他大拇指第一與第二指節間的距離確實是超乎尋常的長。
「看來是這樣沒錯。」甘尼爾說,一張黑臉變得更加陰鬱,「非常有趣。但重點不在於你的一英寸有多長,而在於你必須保持一致性。還有,重要的是,XVI加IXX不會得出XXXVI,你這個蠢材,就算世界末日來臨,也永遠永遠永遠不可能得出這個結果——你這個白痴土包子。」
「是,師傅。這真的很難記住,師傅。」
「它就是故意設計成很難記住,瓦諾學徒。」一個低沉的聲音說道。是李坊主,一名胸膛厚實、黑眼炯炯有神的肥胖男子。「借一步說話,甘尼爾。」他領著甘尼爾來到大作坊一個較為僻靜的角落,用輕快的語調接著道,「你有那麼些沒耐心啊,甘尼爾師傅。」
「瓦諾該背好他的加法表的。」
「你也知道,就連師傅難免也有忘記加法表的時候。」李如慈父般拍拍甘尼爾肩頭。「方才吶,有那麼瞬間,你好像是要他用算的樣呢。」他發出低沉悅耳的大笑,眼裡閃耀著愉快的光芒與深不見底的精明與狡詐。「我只是要你放輕鬆點……聽說你下個聖壇日晚上要來一塊兒用餐,對嗎?」
「是我擅作主張——」
「不要緊,不要緊!很好啊,我還希望她能找個像你一樣穩定的好男人呢。但別說我沒警告你,小女可是個任性又放浪的野丫頭啊。」坊主又哈哈大笑,甘尼爾也咧開了嘴,只是笑容中似乎透著那麼點懊悔。坊主的女兒叫做拉妮,不僅坊裡大部分年輕男性都被她操弄於手中,就連父親都對她言聽計從。她聰明慧黠,性子又善變,一開始甘尼爾還挺怕她的。
過了段時間,他才發現她只有在和他說話時會帶著那麼點羞怯,有如一抹幾近懇求的暗示。他最後終於鼓起勇氣,向她母親提出晚餐的邀約,這是世人所公認的求愛首要步驟。李離開了,他仍佇立原地,回想拉妮的笑容。
「甘尼爾,你有見過太陽嗎?」是個低沉的聲音,乾啞、從容。他轉身,迎視朋友的一雙藍眼。
「太陽?我當然見過。」
「上回見到是什麼時候?」
「我想想。我那時二十六歲,是四年前的事了。你那時不在伊敦嗎?太陽是在快傍晚時出現的,那晚天上可見星辰。我記得我數到了八十一個,在天幕又關閉前。」
「我那時剛成為師傅,人在北方的科林。」米德倚在沉重蒸汽引擎的木製護欄上,那雙淺色的眼珠轉離忙碌的作坊,望向窗外晚秋的綿綿細雨。「我剛聽見你罵那個叫瓦諾的小夥子了……『XVI加IXX不會得出XXXVI……』,還有『我那時二十六,那是四年前的事……我數到八十一顆星星……』再說下去,你就是在算術了,甘尼爾。」
甘尼爾皺起眉頭,下意識地揉了揉太陽穴上泛白的瘢疤。「見鬼了,米德,就連非教徒都知道XXXI減IV等於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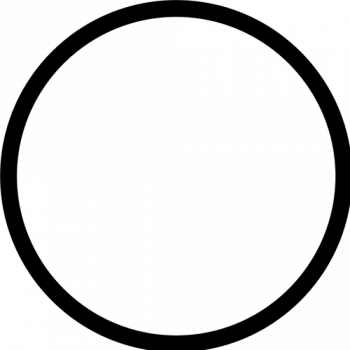
米德嘴角泛起隱隱的微笑。他手裡拿著他的度量尺,垂下手腕,在布滿灰塵的地上畫了個圓。「這是什麼?」他問。
「太陽。」
「對。但它也是個……數字。是數額。一個代表『無』的數字。」
「代表無的數字?」
「對。舉例來說,你可以把它用在減法表裡。II減I等於I,對嗎?那II減II呢?」他停頓片刻,用尺點了點地上的圓,「答案就是它。」
「對,當然是,沒錯。」甘尼爾瞪著地上的圓,這個代表太陽、祕光與上帝之臉的神聖圖樣。「這是祭司才知道的知識嗎?」
「不。」米德在圓上又畫了個X型的十字架,「這才是。」
「那——那這是屬於誰的知識——這個代表無的數字?」
「沒有人的。任何人都可擁有它,這並非祕學。」這答案令甘尼爾詫異地皺起眉頭。此時兩人緊挨著彼此低聲交談,彷彿在討論米德度量尺上的刻度。「甘尼爾,你為什麼要數星星?」
「我……我就是想知道。我一直都很喜歡數字、數數,還有各種數學表。所以我才會成為機械工。」
「對,沒錯。你現在三十歲了,對嗎?從你成為名師傅至今已經四個月了。甘尼爾,你有沒有想過,成為師傅意謂你已學會營生所需的一切知識?從這刻開始到你死前,你不會再學任何新東西,到此為止了。」
「但坊主——」
「坊主是會再學到些暗號和密碼。」米德用他那輕柔乾啞的聲音道,「而且,對,沒錯,他們還握有權力,但他們並不比你擁有更多的知識……你大概以為他們能算術,對嗎?他們不行。」
甘尼爾無言以對。
「不過這世上還是有其他事可以學習的,甘尼爾。」
「在哪?」
「外頭。」
漫長的沉默。
「我聽不下去了,米德,別再說這種話。我不會出賣你。」甘尼爾轉身離開,鐵青的臉上寫滿了怒火。他用盡所有力氣將那股掙扎困惑的怒火轉移到米德身上,那男人不僅肉體,連心智都殘缺扭曲。他是惡魔的化身、是迷途的朋友。
那是個愉快的夜晚。李眉開眼笑,他豐腴的妻子和藹親切,拉妮嬌羞憨媚、容光煥發。甘尼爾年輕的臉上掛著正經嚴肅的表情,讓拉妮忍不住開口逗他,然而就連出言取笑,她的語調都透著股溫順和懇求,彷彿只要再過一會兒,她所有的熱情與活力就會化為纏綿的繞指柔。
傳遞桌上的菜肴時,她的手一度飛快碰了他一下,他到現在還記得是哪個位置。那兒,就在他右手近手腕處,那稍縱即逝的輕柔碰觸。在城市不見絲毫光芒的漆黑夜裡,他躺在作坊上方的臥房床上,發出一聲沉醉的歡嘆。喔,拉妮,那柔軟的觸感,她的手、她的脣——喔,主啊,主啊!求愛是漫長的,尤其對象是名師傅的女兒時,他必須按部就班,起碼得花上八個月。甘尼爾必須驅散這難以忍受的甜蜜念頭。
什麼都不要想,他堅定地對自己說,睡吧,快睡吧,什麼都別想……於是他想起了「無」,那個圓,那個空盪盪的圈。I乘以0等於多少?答案和II乘以0相同。如果把 I 放在 0 旁邊呢,那會變成什麼數字?10?

米德.費爾曼在床上坐了起來,一頭棕髮直直披散在惺忪的藍眼前,試圖將視線聚焦在闖進他房裡的人影上。窗邊透進清晨的第一道濁黃曙光。「今天是聖壇日,」他氣沖沖地道,「走開,我要睡覺。」那模糊的人影凝聚成甘尼爾,他衝上前低聲呼喚:「米德!」甘尼爾又壓低音量繼續道,「你看!」他將一塊石板塞到米德鼻子前,「你看,你看我們可以拿代表無的數字來做什麼——」
「喔,那個啊。」米德回答。他推開甘尼爾和石板,離開床鋪,把腦袋浸到衣櫃上的一盆冰水裡泡了一會兒,然後帶著滴滴答答的水珠坐回床上。「我看看。」
「你看,你可以用任何數字當作基數,我因為方便所以先選了XII,XII於是變成了 1-0,看到嗎,XIII就變成了 I-I。如果再往上換作 XXIV——」
「噓。」
米德研究起石板上的數字,最後終於說:「這些你都記住了嗎?」見甘尼爾頷首,他便用衣袖抹去石板上整整齊齊又密密麻麻的數字。「我沒想過可以用基數……但是你看,用X來當基數的話,我等等就告訴你為什麼,這樣會簡單一點。現在,X就變成了10,XI就會變成II。但換作XII的話就可以寫成這樣——」他在石板上寫下12。
甘尼爾愣愣望著那數字。最後,他用一種掙扎的古怪語調問:「這不是黑數字嗎?」
「對,沒錯。甘尼爾,你所做的,就是走後門學會了黑數字。」
甘尼爾在他身旁坐下,啞口無言。
「CXX乘以MCC等於多少?」米德問。
「乘法表沒列到那麼高。」
「看好了。」米德在石板上寫下:
1200
120
甘尼爾看著,米德又寫下:
0000
2400
1200
又是良久無語。「三個無……XII乘以本身……石板給我。」甘尼爾喃喃道。房裡一片死寂,只有雨水的滴答聲和粉筆在石板上發出的摩擦聲打破沉默。然後,他問:「VIII的黑數字是什麼?」
待這寒冷的聖壇日步入黃昏,米德已把自己所知的一切傾囊相授。確實,米德已跟不上甘尼爾的思維了。「你得去見殷。」白膚男子道,「他可以教你你需要知道的一切。殷研究的是角度、三角,還有度量。利用他的三角板,可以量出任何兩點之間的距離、人類無法到達的距離。他是個偉大的學習者。數字是這門知識的核心、這門知識的語言。」
「也是我的語言。」
「對,沒錯,是你的,不是我的。我不愛數字,我只想用它們來解釋事物……比方說,如果你扔出一顆球,是什麼造成那顆球移動?」
「因為你丟它啊。」甘尼爾咧嘴一笑,露出白如床單的牙齒——比米德的床單還要白上許多——他的腦袋因連續十六小時不吃不睡地思考數學嗡嗡作響,再也容納不下任何恐懼、任何謙遜。他臉上的笑容宛如方自流放歸來的國王。
「好吧。」米德說,「它為什麼能持續移動?」
「因為……因為空氣讓它浮在空中?」
「那它為什麼最後會掉下來?為什麼它的路徑是一道曲線?哪種曲線?現在明白我為什麼需要你的數字了嗎?」此刻,換米德變得如國王一般,一名帝國龐大到無法隻手掌控的憤怒國王。「虧他們還關在那些小小的密閉作坊裡談什麼祕學呢,」他哼了聲,「來吧,我們先去吃晚餐,然後就去找殷。」
那棟高大的老屋就建在城牆邊,透過用鉛框固定的窗戶俯瞰站在下方街道的兩名年輕師傅。硫磺般的晚秋霞影低懸在雨水閃耀的陡峭石頂上
「殷和我們一樣,也是機械師傅。」米德趁兩人等在鐵柵門前時告訴甘尼爾,「他已經退休了,你等等就會知道原因。所有會所的人都會來到這裡,藥師、織工、石匠,甚至是工匠——還有個屠夫。他肢解死貓的屍體。」米德的語調中透著股饒有興味的容忍,就像物理學家說起生物學家時那樣。

大門打開,一名僕役領著兩人上樓,來到一間房中。柴薪在巨大的壁爐內熊熊燃燒,一名男子自高背橡木椅中起身,上前迎接兩人。
這人立刻讓甘尼爾聯想到他會所的那名無上尊師,也就是垂首對著墓中的他呼喊:「起來吧!」的那人。殷同樣身材高䠷,老態龍鍾,身上穿著件屬於上師的白色斗篷。但他彎腰駝背,臉上皺紋密布,疲憊有如垂垂老矣的獵狗。他伸出左手迎接兩人,右臂齊腕而斷,傷口早已癒合,殘肢表面光澤閃耀。
「這位是甘尼爾,」米德介紹,「他昨晚發明了十二進位。還請您幫我指點他有關曲線計算的數學,殷師傅。」
殷笑了起來。那是一種屬於老人的輕柔、短促笑聲。「歡迎,甘尼爾。從此刻起,無論你何時想過來都可以。這兒的人都是巫覡,全都通曉黑技藝,或起碼試著……想來便來吧,早晚不拘。想走也隨時可走。若我們遭人出賣,那也只能如此。我們必須相互信任,祕學並不屬於任何人,我們並非要保守祕密,而是要實行技藝。你明白嗎?」
甘尼爾點了點頭。話語從來不是他的強項,數字才是。他發現自己深受感動,而這令他困窘不已,因為這並非莊嚴肅穆的象徵入會儀式與宣誓,僅僅是一名老者的輕聲低語。
「很好。」殷說,彷彿甘尼爾只要那麼點一點頭便已足夠,「來些葡萄酒吧,年輕的師傅們,還是要麥酒?我的黑麥酒可是今年一等一的佳釀呢。你喜歡數字是吧,甘尼爾?」
清晨,甘尼爾站在作坊內,監督瓦諾將拖車引擎的尺寸記錄在他的度量尺上。甘尼爾一臉陰鬱,過去幾個月來,他變得更加蒼老、更加剛毅,也更加嚴厲。每晚四個小時的睡眠加上還要發明代數,的確是很有可能對一個人造成改變的。
「甘尼爾師傅?」一個怯生生的聲音響起。
「再量一次。」他命令瓦諾,然後遲疑地轉過身,望向女孩。拉妮也變了。她看起來有些惱怒、有些悲傷,和甘尼爾說話時也透著真正的膽怯。他已展開求愛的第二階段,打了三晚的電話給她,可是接著便沉浸在與殷的共同研究中,再無任何進一步發展。從來沒有男人追求拉妮到一半就撤手,也從來沒有男人對她視而不見,如此刻的他一般。當他的視線從她身上穿透而過,究竟是看到了什麼?她好想問,好想知道他的祕密,好想了解他。他說不上來,但能夠隱隱察覺這一點,也因此為拉妮感到難過,也因此有那麼點怕她。
她正看著瓦諾。「他們……你有修改過那些尺寸嗎?」她問,想要打開話匣。
「擅自修改尺寸是異端邪說,會觸犯發明之罪。」
話題於是結束。「父親要我告訴你們,作坊明日不會開張。」
「不開張?為什麼?」
「學院宣布明日將有西風,或許能看見太陽。」
「太好了!這真是拉開春天序幕的好方法,對吧?謝了。」說完,他便轉身回到度量引擎的工作上。
學院的祭司總算對了一次。儘管他們將大部分的清醒時間都耗費在天候預測上,但這是一份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然而,大約十次之中他們還是能正確預估到一次太陽現身,而這就是那一次。

待得正午時,雨勢已然停止,烏雲也逐漸轉白,開始滾滾翻騰,緩緩朝東方飄去。到了下午,所有伊敦子民紛紛走出門外,不是來到大街、廣場,就是爬上煙囪管帽、屋頂,或攀上牆頭、站在牆後的原野觀看。祭司開始他們的祭舞,在學院開闊的前庭上垂首躬身,穿梭如織。每座聖堂內都已有祭司就好定位,準備拉動鐵鍊,打開屋頂,好讓陽光能灑落在聖壇的石面。
終於,到了近晚時分,天幕終於敞開,灰黃色的天空上,烏雲參差不齊的邊緣綻開一抹湛藍。嘆息與輕柔響亮的低語聲在伊敦城內此起彼落:街巷、廣場、窗邊、屋頂、步道都可聽到有人喃喃說道:「天堂,是天堂……」
天空上的裂隙逐漸擴大,陣雨打溼城市,清新的涼風將水幕吹得歪斜。忽然間,雨滴閃閃發亮了起來,宛如夜裡被火炬照亮的水珠,但此刻,它們閃耀的是太陽的榮光。那金輪孤伶伶佇立於西方的天空之上,光芒萬丈。
甘尼爾與其他人一塊兒站在原地,抬起了頭。他能從臉上以及燒傷的瘢疤上感到太陽的熱氣。他凝望著太陽,直到淚水盈滿眼眶。那枚火之圓輪、上帝的臉龐……
「太陽是什麼?」
他想起米德輕柔的話語。在仲冬的一個寒夜裡,他、米德、殷和其他人在殷家的壁爐前侃侃而談。「它是個圓呢,還是個球體?它為什麼會橫越天空?它有多大——又有多遠?啊,想想吶,在過去,人們只要抬起頭,就能看見太陽……」
遠處,學院內傳來陣陣的笛音與鼓聲,歡欣而微弱。有時候,殘雲會飄過那輪熾烈的金烏,世界又陷入寒冷與陰暗,笛聲也停了下來。但西風吹送,雲朵遠去,太陽再次現身,每一次都再低垂一分。就在將沒入西方沉重的雲幕前,它的光芒轉為橙紅,直視它時,雙眼不再會感到刺痛。在這時候,甘尼爾覺得它看起來確實不像個輪盤,而是一顆巨大無比、霧靄繚繞、緩緩沉沒的圓球。
太陽西落,消失無蹤。
頭頂上仍可瞥見天堂在敞開的天幕上閃耀,清澈、深邃,似藍而綠。接著,在靠近太陽西沉的位置,一抹上升的雲層邊緣,有個璀璨的光點閃閃發亮——是暮星。「快看!」甘尼爾呼喊,但只有寥寥幾人轉頭望。太陽已然西沉,星辰又有什麼要緊呢?昏黃的霾靄逐漸爬升——打從十四個世代前的那場地獄之火,這一大片蜿蜒纏繞的雲層便籠罩大地,帶來無盡的粉塵與雨水——遮蔽了星子,將它隱沒。甘尼爾嘆了口氣,揉揉因仰望而僵硬的頸子,邁開腳步,與共世時代的其他子民一塊兒踏上返家之路。
他當晚就遭到逮捕。從衛兵與其他獄友(除了李坊主外,作坊內所有人都給關進了大牢)那兒,他得知自己是因為認識米德.費爾曼而身陷囹圄。米德被指控為異端分子,有人看到他在郊野用某種東西指著太陽,那是一種測量距離的裝備,他們說。他試圖丈量塵世與上帝間的距離。
學徒很快就被釋放。到了第三天,衛兵前來押解甘尼爾,將他帶到學院其中一座封閉的院落。早春綿綿的細雨輕柔落下。祭司幾乎完全生活於室外,而伊敦學院的雄偉建築其實不過是由一座座粗劣棚屋圍起的無頂院落,分別用來寢寐、寫字、祈禱、用餐或執法。他們將甘尼爾帶進其中一座院子,強迫他穿過一排排身穿白袍或黃袍的人影之間,直到站在所有人面前

他看見一塊空地、一座聖壇,還有一張雨水閃耀的長桌,而盤據桌後的是一名身穿代表至高祕學的金袍祭司。長桌另一頭站著另一名男子,他也像甘尼爾一樣,身旁兩側有衛兵包夾。男子望向甘尼爾,臉上沒有絲毫情緒,冰冷而空白,但那雙藍眼湛藍有如雲層之上的天堂。
「來自伊敦的甘尼爾.卡爾森,你有與米德.費爾曼相識之嫌,這名男子被控犯下發明與計算之罪。你是否是他的朋友?」
「我們是同一間作坊的師傅——」
「對。他是否曾和你提及不使用度量尺而做出的測量?」
「沒有。」
「黑數字呢?」
「沒有。」
「黑技藝呢?」
「沒有。」
「甘尼爾師傅,你至今已回答了三次沒有。你可知律法祕學大祭司教團(the Order of the Priest-Masters of the Mystery of the Law)是如何處理異端嫌犯嗎?」
「我不知道——」
「教團有諭:『若嫌犯做出四次否認,便可對其施行拶手之刑,反覆提問,直到嫌犯回答為止。』所以我將再次提問,除非你有意撤回其中一項否認。」
「不。」甘尼爾說,茫然望向四周的高牆與一張張空白面孔。等到他們搬出一座看起來像是木製機具的低矮裝置,並將他右手固定其上時,他依舊是困惑多過了恐懼。他們到底在胡言亂語些什麼?這就像那場入會儀式,他們竭盡所能地要他害怕,而那一次,他們成功了。
「甘尼爾師傅,做為一名機械工匠,」金袍祭司說,「你應該明白槓桿的運用。你要撤回你的答案嗎?」
「不。」甘尼爾微微皺起了眉回答道,然後發現自己的右手如今已齊腕而斷,就像殷一樣。
「很好。」其中一名衛兵雙手按在突出於木匣外的槓桿上。金袍祭司又道:「你可是米德.費爾曼的朋友?」
「不是。」甘尼爾回答。即便他已開始對祭司的問題充耳不聞,仍一次又一次地回答「不」,直到聽見自己的聲音中混雜著從庭院高牆傳來的陣陣回音,不,不,不,不。
光亮時隱時現,冰冷的雨水落在他臉上,然後停止。某人不斷試圖扶他起身。他灰色的斗篷發出惡臭,他痛到想吐,一念及此,他又幾欲作嘔。「放輕鬆。」一名衛兵低語。那一排排動也不動的白袍身影與黃袍身影還聚集在原地,臉色木然,雙眼盯視……可是現在他們並沒有望著他。
「異端分子,你可認得這名男人?」
「他和我是同一間作坊的師傅。」
「你是否和他談論過黑技藝?」
「是。」
「你是否曾傳授過他黑技藝?」
「沒,我試過。」那聲音嘶啞了些。即便在院落的死寂中,即便周遭唯有輕柔的雨聲,仍難以聽見米德的話語。「他太笨了。他不敢、也沒有辦法學會。他來日會是一名優秀的坊主的。」那雙冰冷的藍眸筆直望向甘尼爾,眼中沒有一絲同情或乞求。
金袍祭司再次轉身面向教眾。「我們沒有任何證據能將嫌犯甘尼爾定罪。你可以走了,嫌犯。明日午時歸返此地,見證判決的執行。若無現身,我們將以此視為你有罪的證據。」甘尼爾還沒會意,衛兵便將他帶出庭院,留他在學院一扇側門前,「碰」一聲在他身後關上大門。他呆立片刻,然後趴倒在馬路上,將斗篷之下那隻血跡乾涸的焦黑右手緊緊貼在身側。雨絲在他身旁喁喁呢喃。沒有任何人經過。直到黃昏時分
他才逼迫自己起身,邁開腳步,走過一條又一條的街、一棟又一棟的房舍,一步一步穿過城市,來到殷的家屋。
在門邊的陰影中,有個影子動了動,喊道:「甘尼爾!」他停下腳步。「甘尼爾,我不在乎你是否身懷罪嫌,不要緊的,和我一塊兒回家吧,父親會重新接納你的。只要我開口,他不會說不。」
甘尼爾沉默不語。
「和我一塊兒回去吧,我等你好久了,我就知道你會來。我以前就跟蹤過你。」她欣喜而緊張的笑聲逐漸散去。
「讓我進去,拉妮。」
「不,你為什麼要來老殷的屋子?誰住在這兒?她是誰?和我一塊兒回去,你非回去不可。父親不會讓一名嫌犯重回他作坊,除非我——」
殷從不鎖上他的門。甘尼爾與拉妮擦身而過,走進屋內,關上大門。沒有任何僕人上前,房裡一片漆黑,無聲無息。他們全被帶走了,所有的學習者。他們統統會接受審問、刑求,然後死去。
「是誰?」
殷站在樓梯平臺上,燈光照亮他花白的頭髮。他來到甘尼爾面前,攙扶他上樓。甘尼爾飛快道:「我被跟蹤了,是作坊裡的一個女孩,李的女兒。如果她告訴她父親,他知道了你是誰,他會找衛兵來這兒——」
「三天前,我讓其他人都走了。」聽見殷的聲音,甘尼爾頓時住口,望向老人那張皺紋密布的平靜面孔,然後像孩子般傻氣地說,「你看,」他舉起右手,「和你一樣。」
「是啊。過來坐下,甘尼爾。」
「他們判他有罪。但我沒有,他們放我走,他說他無法教我,說我學不會,他為了救我——」
「還有你的數學。過來這兒吧,坐。」
甘尼爾冷靜下來,乖乖遵從。殷讓他躺下,盡可能地替他清理並包紮好傷口。接著,他在甘尼爾與灼熱的火光間坐下,幽幽嘆了口氣。「好吧,」他說,「現在,你有崇尚異端的嫌疑了,二十年前的我也是如此。你會習慣的……不用擔心我們的朋友。但若那女孩把此事告訴李,並把你我的名字連在一起……我們最好是離開伊敦。可以分頭行動,但今晚就得走。」
甘尼爾一語不發。在沒得到無上尊師的允許下離開作坊,是會被逐出教會、喪失師傅資格的。他將不能再繼續自己的營生。少了一隻手,他還能做什麼?又該何去何從?他這輩子從未離開過伊敦。
屋裡的靜默同時在他們上下兩方蔓延。甘尼爾豎起耳朵,努力想聆聽街上有無任何動靜,像是沉重的腳步聲,揭示衛兵又將再度捉他回去。他必須離開,必須遠走高飛,今晚就要——「不行。」他忽然道,「我得——我明天得去學院一趟,正午的時候。」
殷明白他所言何意,沉默再度包圍兩人。待老人終於開口,他的聲音顯得極為乾啞、疲憊。「這是他們釋放你的條件,是嗎?好吧,那你就去吧,你不會想要被他們在四十個城鎮發布通緝,追捕你這個定讞的異端分子。嫌犯不會被通緝,只會被驅逐,這樣比較好。先睡會兒吧,甘尼爾,在我離開前,我會告訴你我們該在哪兒碰面。你也盡快動身,輕裝簡行……」
然而,待甘尼爾於近午時分離開時,他還是在身上帶了些東西。他將一綑紙捲藏在斗篷下,每張紙上都寫滿米德.費爾曼密密麻麻的工整字跡。「軌線」、「墜落物體之速度」、「動的本質……」殷在破曉前便離開了,騎著匹灰驢,從容不迫地顛簸出城。「我在可林等你。」是他唯一的道別語。在學院寬敞的前庭裡,甘尼爾沒見到任何學習者,只有奴隸、僕從、乞丐、蹺課的學童,以及帶著保姆與哀啼嬰孩的婦人,和他一塊兒站在正午黯淡的陽光下。唯有賤民和無所事事的烏合之眾才會前來觀賞異端分子死去。一名祭司命令甘尼爾站在群眾最前方,許多人都好奇地看著這名獨自站立、身穿師傅斗篷的男子。
廣場另一側的前排人群裡,他看見一名紫袍女孩。他不確定是不是拉妮。她為什麼要來看米德被處死?她根本不曉得自己恨的是什麼,或者愛的是什麼。只渴望得到與擁有的愛,猶如一頭可怕的怪物。甘尼爾心想。她是愛他的,他倆之間只隔著一個廣場的距離。她永遠也不會想看見自己與他分隔兩地,無論是因為她自身的行為、因為無知、因為放逐,或者因為死亡。

就在正午即將到來前,他們將米德帶進廣場。甘尼爾瞥見了他的臉龐,白如金紙,暴露出他所有殘畸,那如先祖般蒼白的膚色、髮色與眼珠。事情已無轉圜的餘地。一名金袍祭司舉起交叉的雙臂,向那隱而不見的太陽、那隱藏在雲幕之後的正午祈願。他一放下手臂,火炬便點燃木樁周遭的柴薪。黑煙盤捲而上,如雲層般灰黃。
斗篷之下,甘尼爾用他吊著的傷臂緊緊貼著那捆紙捲,不停無聲複誦:「讓濃煙先嗆死他,讓濃煙先嗆死他……」但乾燥的柴薪很快就著了火,他感到熱氣迎面撲來,燒灼他也曾遭火吻的太陽穴。在他身旁,一名年輕的祭司想要後退,然而圍觀、推擠、長吁短嘆的群眾讓他進退不得,只能佇立原地,微微搖晃,大口喘息。黑煙已變得濃密,吞沒了火光與烈焰間的人影。
但甘尼爾能夠聽見他的聲音,再也不輕柔了,而是刺耳,非常刺耳。他聽見了,他逼自己一定要聽,但同時間,他又凝神傾聽另一個穩定的聲音,不停輕柔地道:「什麼是太陽?它為什麼會橫越天空?……現在明白我為什麼需要你的數字了嗎?……把XII寫成12……這同時也是一個數字,代表無的數字。」
慘叫聲停止,但是那輕柔的話語還在繼續。
甘尼爾抬起頭,群眾逐漸散去。那名年輕祭司跪倒在他身邊,大聲祈禱、啜泣。甘尼爾昂首望向沉甸甸的天空,然後邁開腳步,獨自穿過城市的街道,走出城門,朝著放逐、朝著他的家,往北而去。
本文摘自《風的十二方位》,2019 年 8月,木馬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