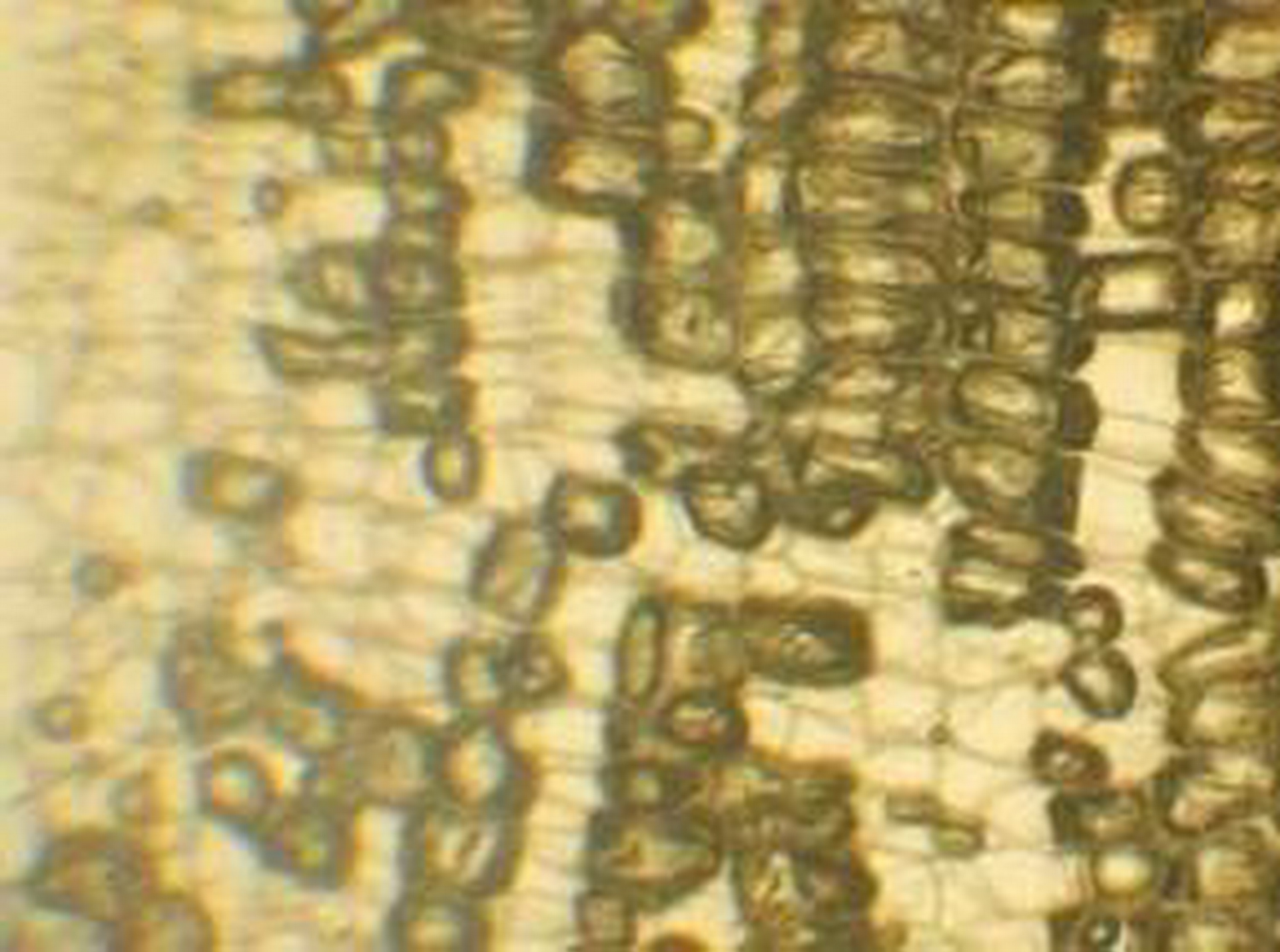臺灣近年來出現不少優質戲劇。長年經營單元劇的公共電視臺,從 2017 年開始新創電影的計劃,希望能鼓勵更多影視人才。《疑霧公堂》即為公視在 2018 年推出的電影,「2019 泛知識節」特別邀請了電影製作人陳思宇,為我們解析影像背後的各種努力。

古裝製作大不易,美術道具要考據
《疑霧公堂》是一部古裝懸疑劇,時代背景設定在清朝末期的臺灣,描寫當時大家族──霧峰林家的林文明,於公堂上被斬殺的事件。
創作團隊選擇歷史背景的題材,鎖定真實案件作為發想,因為一個案件的產生,勢必是對既有秩序的扭曲、破壞,或使其產生變化,也因此必然含有戲劇化的要素。
然而,在提交劇本時,《疑霧公堂》碰上了問題。電視臺很少接受古裝劇的提案,這是因為古裝劇、時代劇拍攝十分困難。除了在前製階段,劇組就必須花費大量工夫考究歷史之外,目前在臺灣,拍攝古裝劇也缺乏足夠資源。以前還有中影文化城,現在則根本沒有這些古裝的佈景設施可以讓劇組取景,換言之,每次拍攝都必須重新開發資源,讓拍攝的成本居高不下。
以《阿罩霧風雲》這部電影為例,因為不確定往後是否有機會拍攝同類型的作品,再加上預算的考量,拍攝期間,團隊直接請了一位從臺灣到中國發展的師傅,以較低的預算製作美術陳設和道具。拍攝完電影後,所有的道具都交給了中國大陸。中國大陸有大量的古裝戲需求,因此在資源上是十分豐沛的;反觀臺灣缺乏這種資源,所以,公視雖然通過了提案審核,但初期也很擔憂是否能夠執行整個計畫。
已被淡忘的塵封過往,如何好好訴說?
通過提案後,前製期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完成劇本。這部劇在談霧峰林家的案件。對熟悉臺灣歷史的學者而言,這個事件經常被提及,但對大多數的臺灣觀眾來說,卻十分陌生。
林文明在彰化被就地正法,引起當時社會震驚。想像一下,假如有一位將軍或總司令,走到市政府突然被關起來,並且被殺死,會是一件多麼震撼的事情。林文明身為清末臺灣中部最有權勢、最龐大家族的族長,突然遭到殺害,在那個年代非常引人矚目。當時,霧峰林家上訴纏訟了二十幾年,如果到故宮的清宮檔案去查閱,會找到一整排的文件跟這個案子有關。但這件事只流傳於學界,出了學界後,現代社會卻一概不知。學術圈跟一般社會有很大的落差。

正因如此,對於影視產業來說,最困難的莫過於將一堆歷史資料轉換為戲劇劇本。過去的臺灣,很少有編劇能夠真正進入社會事件尋找題材。《疑霧公堂》團隊的研究員提供了很多資料給編劇,但對編劇來說,讀完後往往只覺得十分疲累,除了必須把握住角色情感、情節佈局和戲劇邏輯之外,還要消化大量的背景知識,過程相當辛苦。
想忠於史實?先接受口語表達的挑戰吧!
進入拍攝階段,現場也會碰上許多狀況。《疑霧公堂》是歷史劇,必須還原當時的社會面貌。在那個年代,臺灣社會使用日語、臺語,國民政府遷來後又使用國語,語言組成相當多元。
- 從《疑霧公堂》的預告片,就可以聽到不同的語言。來源:PTS 台灣公共電視
如果戲劇的用語很複雜,現場拍戲就難以控制。比方說,演員可能會聽不懂對白,不曉得其他演員在講什麼。有些演員甚至會放棄記誦別人的臺詞,只記自己的臺詞,對戲時就容易出現奇怪的狀況。
臺詞內容方面,儘管某些導演和演員崇尚自由詮釋,但電影不像連續劇那樣,有充足的時間能建立歷史背景,因此往往只能依靠對白去交待前因後果。
舉例來說,林文明一開始不願去彰化縣公堂,但在劇中沒時間解釋歷史脈絡,只能用對白說明,他是清代官員,擁有指派代表的權利,因此他都讓家人代替他上公堂報告。像這類型臺詞本身就帶有特殊訊息,幾乎沒有發揮的空間,拍攝現場就必須和導演及演員溝通好。
而在初期挑選演員時,不懂講臺語的演員會直接被拒絕。這也反映出年輕一代演員在口語方面的侷限,沒辦法演出歷史戲。幸好,《疑霧公堂》選用的演出者,臺詞都背得很好,這點真是十分感謝。
以上談到的狀況都是改編歷史事件時可能遇上的問題。解決的方法不只一種,因為每個狀況都很獨特,而影視作品是在預算與時間壓力下折衷產生的成果。一個健全的影視產業,需要維持每個工作人員的生活,因此抓緊有限的預算跟時間,讓計畫順利開拍,對於製作人來說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