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想到喪失親友時,腦中最先浮現的通常是死亡一事在文化中的外在表飾:
棺材、墓園、反覆聽見的哀悼之詞「我很遺憾」、黑色、殯儀館。
要釐清憂鬱的歷程,就從動物的喪親之痛開始著手
愛爾蘭人在守靈時喧鬧地講述往事,或者猶太人遮蓋鏡子並進行七日服喪儀式的習俗。無論遵循什麼傳統,心情低落和憂鬱都是失去親友時會經歷的過程。要將憂鬱症研究清楚,我們需要詳細分析失去親友導致的心情變化。為了釐清整個過程的起因,我們就從研究動物著手,喪親之痛最原始也最基本的形式著手——研究動物。

以一隻失去孩子的黑猩猩媽媽為例,科學團隊在幾內亞拍攝到牠守護屍體的影片。牠照看屍體,拿著一根長滿葉子的樹枝趕走周圍飛來飛去的蒼蠅。這段影片很短,但拍攝影片的科學家證實黑猩猩媽媽在屍體旁邊待了數天。一段重要的關係終結,一般來說是很重大的事件。
也曾有人目睹圈養的大猩猩媽媽在孩子死去後,做出類似的事。德國明斯特動物園有一隻十一歲的大猩猩嘉娜,牠曾被人看見走到哪都帶著自己死去的寶寶克勞帝歐;有時候是抱著,有時候是背著。牠會對著屍體又戳又撫摸,宛如希望孩子活過來。結果並沒有如願。
大猩猩會不會悲痛?所有跡象都指出答案是肯定的。一隻大猩猩不吃、不睡、不四處探索,看似把心思放在剛剛失去的東西上;這些徵兆無疑和人類悲傷時表現出來的跡象很類似。如果我們從這隻大猩猩媽媽身上採集生物樣本,我們一定會看到類固醇荷爾蒙增加的現象,而同樣的現象在悲痛的人類身上很明顯。在所有哺乳類物種當中,與至親分離和失去至親都會造成壓力指標顯著上升。行為及荷爾蒙的跡象綜合起來便可看出,大猩猩在孩子死去後,的確會感受到低落的心情。

當社交性動物的感情聯繫斷絕時,會立即感到痛苦
然而從演化的觀點來看,為什麼「悲痛與哀傷」會如同法國作家拉馬丁所言,「比快樂更能將兩顆心緊緊繫在一起」?哺乳類物種大多是社交性動物,會與母親、同伴、伴侶形成強烈且持久的感情聯繫。最重要的聯繫若斷絕,或者有斷絕的危險,會立刻激發痛苦。如果聯繫無法復原――例如在有人死去的情況下――心情便會開始低落。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就曾經說過:「悲痛是我們為愛付出的代價。」
情感系統會監控重要的關係,因為在社交性物種當中,「關係」是不可或缺的。跟我們同族的其他成員,也就是同種的個體,會為生存和繁衍做出重要貢獻,例如尋找及提供食物、針對危險做警戒與防護,以及撫養年幼成員。有成員死去時,生存繁衍就會受到「適應性降低」的影響;適應性降低是一種簡略的說法,意思是可供生存繁衍的資源變少了。團體中若有一個成員死去,活著的成員就必須團結合作,重建這些資源。
如果有一份演化分析報告,我們大概可從中推測,失去孩子對母親而言,特別令人悲傷。因為這對適應性是嚴重的打擊,而且直接降低了母親將自己基因傳遞下去的機會。從數個人類文化收集而來的資料證實,最強烈的悲痛是由孩子死亡所引起的。此外,孩子如果是在接近生育年齡時死去,引發的反應又最為劇烈。這是另一個線索,足以顯示悲痛與適應性有關。
失去一個父母或供養者也會降低適應性,在世的親屬可能無法取得食物或避開掠食者。除非這個群體能得到幫助,否則其生存就會面臨危險。心情低落是一個強烈的信號,代表生存可能陷入危險。就連陌生的對象死去,都可以觸發低落的心情。在遠古時期,一個物種當中若有一個個體死亡,通常代表環境不利於生存繁衍:附近可能有疾病或敵人。這種時候,最聰明的做法就是至少暫時保持低調。

失去摯愛引發的強烈悲痛,是引起憂鬱症的重要因素
在人類當中,死亡是激發低落心情的一種強大因素。我們可以說每一個文化都發展出了以死亡為中心的複雜儀式以抒發、控制並掌握低落的心情。由於我們有能力用言語表達思想及情感,摯愛對象(也包括愛人以外的人)的死在我們身上,可能比在其他物種的身上更能激發情感。人類可以刻意藉由回想過去發生的事來記住一個最近死去的人。語言給了我們工具,讓我們可以思考永久失去某人的重要性及含意。確切地說,我們對死者的思念和對生活少了他們之後的擔憂,經常會在言談間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
幾乎每一個痛失摯愛的人都會經歷心情低落期,時間長短各有不同――從數小時、數天、數週到數月都有可能,有時候甚至會持續數年。因為失去至親好友而悲痛的人大多不會罹患嚴重影響健康的憂鬱症,但是其中有將近三分之一會陷入一段臨床上很顯著的發作期。沒有人能避免面對死亡,所以死亡一直都會是引起許多人憂鬱的因素。即便統計資料不完善,我們也可以推估大約四分之一的憂鬱症病例與傷慟有關。
有了這些數字,加上幾乎人人都會遭遇傷慟,我們不難提出有力的論據來支持相關研究,觀察人類對死亡的反應,以了解低落心情及憂鬱症。事實上,如果造成低落心情及憂鬱症的樣本情境是無法挽回的失落,而且還是摯愛之人死亡,那麼邏輯上來說,傷慟應該會是憂鬱症研究的一個重要主題。然而這個議題並未受到注目。

舉例來說,二〇一〇年共有四百零四篇論文發表於探討範圍遍及所有情感疾患的重要精神病學期刊《情感疾患期刊》(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但討論到傷慟的只有三篇。同樣地,近年出版的《國際憂鬱症百科全書》(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Depression)厚達五百七十四頁,關於傷慟的內容卻只占了三頁。這些數量代表了傷慟這個議題在憂鬱症研究中的地位。「傷慟」與「憂鬱症研究」極少同時被提起。
之所以有這種情況,是因為就研究領域來看,傷慟與憂鬱症一直到不久前都還分屬於兩個完全分開的學界。研究憂鬱症的人和研究傷慟的人大體而言處於不同領域,在不同期刊發表論文,出席不同的研討會,而且在根本上驅策他們的研究問題和考量也不同。
如何區分憂鬱症及傷慟?了解傷慟在憂鬱症當中扮演的關鍵角色
憂鬱症與傷慟之間存有隔閡,顯著證據就是,在面對與死亡有關的低落心情時,研究人員一直沒有找到它在現代診斷系統中的定位。舉例來說,有長達數十年的時間,在《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這本心理疾患診斷的官方聖經中, 親友死亡兩個月內出現的憂鬱情況經常不被稱為「憂鬱症」。
親友死亡引起的憂鬱症反而被歸到另一個範疇,稱為「單純傷慟」(simple bereavement),但研究人員並未指出它與心理疾患或症狀的關聯。其實,在一個人可能發生的所有不幸中,傷慟是歷史上唯一有可能推翻憂鬱症診斷的人生事件。怎麼會這樣?要了解原因,我們必須回溯這本診斷手冊的第一個前提:
心理疾患反映出來的是疾病,它們並不屬於正常的心理變化。
照疾病模型的原則來看,憂鬱症的症狀必定會反映出官能異常。問題是,DSM體系的創建者認為,人在傷慟的情況下,經歷短暫的憂鬱期,可能是很典型、甚至具有適應性的現象。與傷慟有關的憂鬱症使得這種疾病模型陷入了窘境,因為傷慟會產生和一般認定的憂鬱症相同的症狀,但不會反映出任何官能異常現象。因此,將與傷慟有關的憂鬱症(被認為具有適應性)排除在憂鬱症(被認為是一種疾病)之外,對於保持「DSM中記載的所有情感疾患都是官能障礙」的前提來說很重要。

一個人表現出來的症狀被認為是某種官能障礙,也就是從憂鬱症模型來看,是「電化學干擾」所造成的後果,這種觀點影響深遠,我們以此明顯劃分出有意義、甚至健康的憂鬱症和與其相反的憂鬱症。將傷慟引起的憂鬱症與其他憂鬱症分隔開來,並不是什麼深奧難懂的診斷實務;此舉會影響到數百萬人如何被其他人看待、治療,以及評斷。我們以為這樣的切割有其根據,也就是有大量證據證明,傷慟性與非傷慟性憂鬱症在一些重要層面上確實有所不同。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直到最近,才有科學家根據實際資料,相互比較憂鬱原因是傷慟與非傷慟的人,重新檢討是否要讓傷慟排除在心理疾患之外。如果透過這樣的試驗,我們能發現,由不同觸發事件引起的憂鬱症都很相像,就能支持這個觀點:我們的情感系統運作設定為,對於任何重大失落,都以大致類似的方式作出反應──無論失去的是至親的人,是工作,還是名譽。
我們得到的結論確實支持以下見解:無論形成原因是喪偶還是失去畢生積蓄,憂鬱症就是憂鬱症,無可否認。
有了這些新的研究發現,心理疾患委員會總算在二〇一三年發行的最新版 DSM-5 中,取消了傷慟排除條款。我們不再受此條款影響之後,便能用更一致的方式去觀察憂鬱症,並了解傷慟在憂鬱症當中扮演的關鍵角色。
本文摘自《憂鬱的演化:人類情緒本能如何走向現代失能病症》,左岸文化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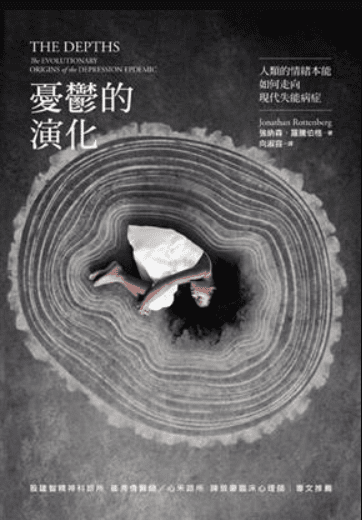
































-200x200.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