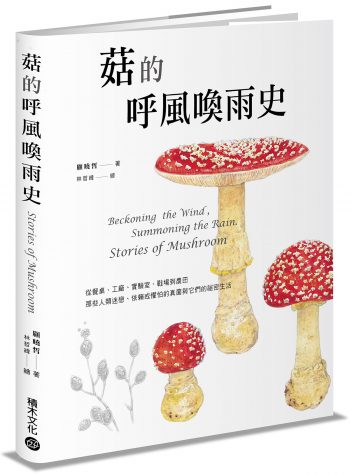拆解四川羌族神話中的厭女文化——身懷謎樣魔力的「毒藥貓」女巫傳說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四川羌族「毒藥貓」 傳說中國西南的藏羌族地區,每一村寨都住著「毒藥貓」,這些身懷謎樣魔力的女人能變身、飛行、下毒,如同西方中世紀女巫!「研之有物 」專訪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王明珂院士,他走訪中國少數民族三十年,從毒藥貓故事中,提煉出人類社會共同的恐懼、猜疑與暴力根源,更直言「臺灣就是毒藥貓」。
黑夜降臨,魔女現身
在中國四川省藏羌族區,長年流傳著神秘的鄉野傳奇「毒藥貓」。毒藥貓不是貓。她們多半是女人,有毒的女人、身懷魔法的女巫。
平日,她們生活在村寨裡,可能是隔壁的姑娘、對門的大嬸,與尋常人無異。但到了夜裡,靈魂便伺機而動。傳說,每個毒藥貓都有一只口袋,從口袋抽出哪種動物毛,就能幻化成貓、牛、羊外出害人。
毒藥貓不只孤身作案,也愛「開趴」。各地的毒藥貓定期聚首,派對上狂歡作樂、大啖人肉,聽令首領分派任務。即使住得遠,也用不著擔心,這些女人擁有能翻山越嶺的縮時交通捷徑——騎「櫥櫃」飛行!
心不狠不成魔,宴席上毒藥貓賭輸了,據說連自己的兒子、丈夫都能下手。但無論如何,絕不會下毒在自家兄弟身上,娘家就是她們最後的溫柔。《倚天屠龍記》裡有句名言:「越是好看的女人,越會騙人。」羌族的人們則說,別在毒藥貓家吃飯,越美豔的女人越毒。年輕貌美的會變身;年紀越大、毒性越弱,最後則只剩指甲裡的一點毒。但不要緊,毒藥貓的法力能在母女間傳承。
《 CCC 創作集》以王明珂的研究為藍本,推出漫畫版《毒藥貓》 。羌寨的毒藥貓故事大致有兩類:一類來自口傳,村民世代建構的歷史記憶,描述年輕男子遇上、識破毒藥貓,不時穿插超自然情節。另一種,則是村民對生活經驗的詮釋,例如到隔壁村寨吃飯拉肚子,便解釋成被毒藥貓下毒。圖/© Fengta/CCC 創作集提供 毒藥貓與它的產地
以上的羌族鄉野傳說,看似有些荒誕離奇。但在當地,毒藥貓並非只是鬼怪迷信,而是蘊含重要的本地歷史與生活經驗。
如同臺灣人對魔神仔、好兄弟深信不疑,毒藥貓形塑的歷史記憶與信念,同樣在羌族世界深深扎根。許多羌族人回憶,小時候因為恐懼毒藥貓,晚上絕不敢亂跑出門。美豔一身毒、會飛會變身的毒藥貓,是如何深入人心,成為當地文化的一部分?
一切,得從毒藥貓的產地說起。
「田野訪談時他們說,幾十年前每個村寨都有一兩個女人是毒藥貓。」中研院院士王明珂從 1994 年起深入岷江上游,走訪羌族各村寨。
羌族是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居住在岷江上游、支流兩岸。雖然被劃分為同一民族,但實際上,「羌族」是 1950 年代後才被國家政體建構出的身分,過去,這裡的人並不覺得彼此「同一族」,一村寨成一國。村寨間的共通語言是漢語(四川話),所謂的羌語差異極大,鄰近村寨覺得對方怪腔怪調,距離遠一點,彼此的羌語就成了「火星話」。
岷江切過青藏高原邊緣形成高山間的深谷,四川方言稱之為「溝」。村寨一般聚居在每個溝的半山腰。我們熟悉的「九寨溝」,意思就是一個溝中有九個寨。圖/王明珂 每個村寨都是一座孤島
語言不通、文化殊異、缺少共同認同,但王明珂走訪田野時卻發現,各地村寨幾乎都能採集到毒藥貓故事。
「毒藥貓故事存在於每個村寨,意味這是一種很普遍的生態。往深一點看,背後根基於當地的生活文化與群體認同。」王明珂分析。
羌族居住在高山深谷,幾個家戶組成「寨」,一般約五、六十戶,小寨則只有兩三戶,幾個寨共居一個山溝成為「村」。山高谷深,從一個溝到另一個溝大不易,「當地人會說,哎!翻過一座山就到了。我一試,」王明珂苦笑地說:「那山一翻都在四千公尺以上。」
村寨如同一座座懸立山腰的孤島。但孤島,並不是人們想像中的「世外桃花源」。
住在高山,討生活得和大自然拚搏,提防暴風雪、野豬狼豹、一失足就沒命的懸崖峭壁。居民種植小麥、玉米、青稞,也到更高的森林採藥、打獵,在林間放養羊、馬、旄牛,逆境求生,多管齊下養活一家子。
要搏鬥的不只自然環境,還有其他羌族人。
資源匱乏、山林險峻,可以想像住在這裡的人們,生存壓力有多大。過往,村寨間經常因草場界線起衝突,偷盜牛羊、甚至集體打劫殺人。田野訪談間有位老人回憶,有次其他溝夜裡打了過來,守夜者卻不小心睡著,那晚四十多人被趁黑割喉,部落衝突直逼小型「戰爭」!
外面世界險惡,自家裡同樣也「親兄弟明算帳」。寨裡的不同家族、鄰近村寨,一方面得同一陣線抵禦外敵,但彼此為了爭奪稀缺資源,也仍是你爭我奪。
村寨生活就像是一小群、一小群的人們,守著各自的地盤,對抗環伺的風雪猛獸、瘟疫災厄、蠻子敵人。王明珂這麼形容:每個村寨都像是一個孤島,既對外禦敵,內部又高度衝突、彼此防範。
體現村寨「孤立感」的明顯例子:傳統的羌族聚落,常見一座座石頭屋,整片牆上只開了幾扇小窗,建築底部留著一條窄道。在在顯示資源競奪劇烈,對外恐懼、提防的特徵。圖/王明珂 尋找代罪羔羊:轉移衝突、宣洩內部緊張
有句話說:要讓一群人團結,需要的不是優秀領袖,而是共同敵人。對外恐懼、內部衝突,村落生活的張力不斷拉緊又拉緊,隨時可能「啪!」地斷線。這時,「代罪羔羊」便是消解團體壓力、凝聚彼此的方法。
「夜深了,回家吧。」外頭躲著嚇人的毒藥貓,村寨更值得人們信任依靠;遇上病痛苦難、牲畜發狂、失足墜崖……與其怨天怨地怨自己,不如歸罪毒藥貓吧。有了毒藥貓,受苦彷彿都有了答案與發洩出口。
毒藥貓,如同羌寨社會的「壓力閥」,也就是那隻代罪羔羊。
在每個村寨,總有一兩個女人被貼上「毒藥貓」標籤,背負汙名,所有人都知道,但看破不說破。因為一旦身分搬上檯面,整個家族的女性便很難嫁出去,遭惹鄰寨娘家上門問罪。
毒藥貓是「不能說的秘密」,眾人只在背後閒言閒語、發洩怨怪。「一到吃飯時間,被認為是毒藥貓的女人會藉口田裡忙來送客,因為她知道,自己做的飯沒人敢吃。」王明珂一語道出「替罪羊」艱困的處境。
過去,羌族人沒有共同的民族認同,下游的人稱上游的為蠻子,上游的又稱更上游的人為蠻子,一截笑一截。嫁娶雖不會隔太遠,但常把女兒嫁往下游經濟較好的村寨,這也讓村寨隱約對這些外來的女人抱持不信任,擔心血統、認同被「蠻子」汙染。圖/王明珂 都是 they 的錯:爭產、亡國、瘟疫,為何女性常是代罪羔羊?
有趣的是,若把毒藥貓的符號拆解開來:女人、貓、邪惡,是否覺得有些眼熟?沒錯,毒藥貓圖像竟與典型的西方女巫高度吻合。
中世紀圖像經常描繪一群女巫秘密集會,狂歡作樂、與魔鬼同宴,用蜘蛛、老鼠滾煮一鍋邪惡湯藥。女巫騎掃把,身邊竄著不祥黑貓,在廚房烹煮湯藥;毒藥貓則乘坐廚房的櫃子,變身的口袋藏在灶爐。
充滿女性意象的符碼,巧妙出現在東西異文化,這些「有毒的女人」皆被指控是不幸的源頭。從東方羌族到歐洲女巫,為何女性會被視為邪惡象徵?當社群彼此猜疑對立,又是誰,總成為祭壇上的羔羊?
王明珂直指代罪羔羊的概念核心:她們既是內人,也是外人。
父權文化下,弱勢女性群體長久被連結負面象徵,每當社會動盪不安,便難逃代罪羔羊的指摘。特別在傳統社會,「嫁進來的女人」裡外不是人,最易成為標準嫌疑者——宅鬥故事中,兄弟爭產絕少不了覬覦、愛挑撥離間的媳婦。
尤其外敵環伺的羌寨生活,我群/他者的劃分,更是維繫集體安全的重要信仰。從其他家族、村寨嫁過來的女人,無形中「破壞」了敵我界線,一旦出現紛擾不安,這些社群內部的「外人」,很快被聯結到外部威脅者。
換言之,恐懼毒藥貓、施暴代罪羔羊,其實是人們把對外部的敵意和恐懼,轉嫁在眼前這些「內敵」。
恐性、厭女是另一個共同根源。毒藥貓越年輕美豔越毒,西方女巫常被指控放浪偷歡,父權社會對女性身體、貞潔抱持不安,因而也透過貶抑,維繫某種對「潔淨」的管控。圖/Luis Ricardo Falero ,1878 誰讓閒言閒語,走向集體暴力?
「各位,我可以證明她與魔鬼勾結,燒死她吧!」中世紀歐洲,數以萬計的女性被誣指為女巫,遭受殘酷絞刑、火焚,人類社會對代罪羔羊的暴力史,淵遠流長。但同樣被視為代罪羔羊,為何羌族不曾出現「獵殺毒藥貓」?
王明珂認為「上層權威是否介入」,或許是兩者走向不同歷史路徑的關鍵。
過往村寨社會的政治權威為官府系統,只管人民是否乖乖繳糧納稅。相較於基督宗教,當女巫與魔鬼誘惑之說結合,便成為具威脅性的異端信仰,促使教會動員介入,因而掀起清洗審判行動。
「我從羌族田野發現,社會其實會隱然容忍這類『代罪羔羊』,用來維持內部減壓。對照歐洲,也是直到外部權威力量介入,或者內部出現重大威脅,才開始形成大規模暴力,轉成政治鬥爭的手段。」
中世紀、近代初期,歐美都曾出現獵巫浪潮,根據文獻中的審判證詞,許多「女巫」在當地早被議論若干年。這顯示,毒藥貓等代罪羔羊模式或許是普遍的社會常態,直到有重大對立或外部權威介入,才會升高衝突,產生大規模暴力。圖/《Luzerner Schilling》 羌族地區甚至流傳著一句話:無毒不成寨。
意思是,如果沒有毒藥貓,一切會更糟,因為只有她們鎮得住瘟神。這也意味儘管社群內部排斥毒藥貓,仍隱然認同她們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婚嫁引入了聯姻勢力、增加隊友;同時,人們正是透過對代罪羔羊的非議,維繫凝聚了社群。
民族主義、種族暴力、校園霸凌:我們都可能是毒藥貓
「無毒不成寨」背後有個神話故事:傳說毒藥貓女人被丈夫發現,逼她到河中「去毒」,洗了八條河後,天神出聲警告:「再洗,毒藥貓就要斷根了!」但時至今日,羌族毒藥貓不僅沒有全然斷根,在當代社會、民族主義、種族暴力中,毒藥貓身影始終沒有斷根過。
「我會特別關注毒藥貓文化,也是因為臺灣就像毒藥貓!」王明珂直言。對於中國,臺灣人既非自己人也非外人,當中國遭受重大內憂外患危機時,臺灣便可能被推向毒藥貓的位置。
從這個視角,「毒藥貓故事」絕非羌族特殊文化,而是映射出更普世的象徵意涵。在多數人類社會裡,邊緣、弱勢群體、社會中不受歡迎者,往往被視為不被認可、潛在的叛徒,每當社會陷入重大矛盾與對立、秩序被破壞,便會激化原有的矛盾與分界,這些被拒斥者即為承受集體暴力的代罪羔羊。
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相似劇情反覆上演。
霸凌如是,種族衝突如是,疫情下的獵巫亦如是。我們守在同溫層、小圈圈內,恐懼敵意,如同羌寨裡的人們,村寨幾可說是「縮小版」的人類社會。
投入羌族田野三十年,毒藥貓映射出的文化根源成為王明珂深切關懷。他強調,縱使毒藥貓斷不了根,但反覆的論述、省思、檢視,或許能在集體陷入究責氛圍、尋找代罪羔羊之時,幫助我們自我覺察,攻擊毒藥貓只是短暫麻藥,最終可能忽略真正的恐懼核心。我們終究需要正視自己的擔憂、焦慮,才有能力解決問題。
「避免把別人當成毒藥貓,因為換一個視角,我們也可能變成那個毒藥貓。」
「毒藥貓其實是人類普遍的暴力形式。」王明珂以中國少數民族為田野對象,探討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在國族、宗教衝突頻傳的當代,他也期盼能透過村寨這類「原初社會」的各種生態,洞察人類暴力的共同根源。圖/允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