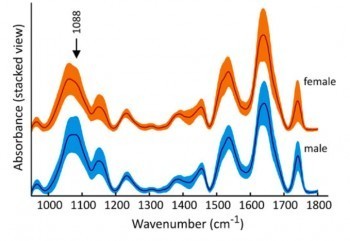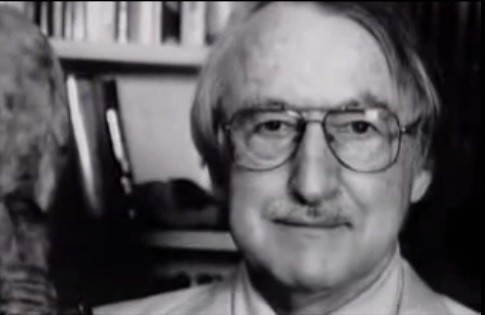【科科愛看書】我們的性別,到底是如何決定的?由天氣、運氣還是神的旨意?多年以來,我們漸漸知道性別背後的科學根據,然而,仍然有太多未知是我們不曾發現的。跟著《變身妮可 》一起走過跨性別女孩與她家庭的成長之路,相信在這條路上,唯有更多的理解方能帶來尊重及包容。
由雪若.卻斯(Cheryl Chase)成立的「北美間性人社團 」有項重要訴求是:醫生不該直接對間性嬰兒動手術,而是到適當的年齡後交由他們自己決定。之所以提出這項訴求,是因為他們認為性矯正手術常基於文化壓力而非生物因素。對此卻斯表示:
間性人不該被視為畸形、不正常或怪異的個體,因此醫生首先建議的處置不該是手術。
行為主義的大騙局:性別不是他人可以決定!
卻斯和間性人社團反對在 1960、70 年代箝制整個心理、精神及性政治圈的行為主義(behaviorism),此主義最熱切的支持者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約翰.莫尼(John Money)博士,他深信性別認同是一種社會建構,因此在面對外生殖器曖昧或不正常的嬰兒時,父母應該直接決定自己想要哪一個性別的孩子,然後提供適當的衣物並引導孩子走向特定性別道路,之後自然會得到理想的結果。
信奉行為主義的約翰.莫尼博士。圖/sophmoet
莫尼用來展示的「樣品」是一名在 1965年 8月出生的孩子:他是一個名叫布魯斯的健康男嬰──其實是同卵雙胞胎的其中一位──8 個月大時,一場手術中為了移除梗阻而進行的燒灼治療意外燒掉了布魯斯的陰莖,莫尼於是建議家長把他以「布蘭達」的身分撫養長大,所以這名男嬰被移除睪丸,得到女生的名字與衣物,並被當作女孩撫養。布蘭達進入青春期後,他們還在本人不知道的情況下進行女性荷爾蒙治療,使她在那段時間長出胸部。
布蘭達的童年總是充滿無止盡的霸凌與嘲諷,因為除了女性衣著與荷爾蒙之外,她完全不覺得自己是女生,行為舉止也不像。直到青少女時期,她滿腦子都是輕生念頭,父母才告訴她真相,讓她在 14 歲時準備變性為男生。到了 30 歲,已經改稱自己為大衛.瑞默爾(David Reimer)的布蘭達經歷了乳房切除術、睪酮注射及兩次的陽具重建手術,最後結婚也收養了孩子,但仍被莫尼醫生和父母的決定所折磨。他的雙胞胎兄弟一生都有心理方面的疾病,最後因為過度服用抗憂鬱劑身亡,兩年之後,38 歲的大衛也自殺了。
被強迫變性的大衛。圖/路透社資料圖片
這段過程中,病患都還在世,莫尼卻一直向大眾更新這個「實驗」案例的性別重建手術進度,還在 1972 年和 1977 年發表了歡慶實驗成功的文章。直到 1990 年代,米爾頓.戴蒙醫生(Dr. Milton Diamond)找到治療青少女布蘭達的精神科醫生,才揭發了這個謊言。莫尼口中的大成功其實是場無從挽回的悲劇,布蘭達在成長過程中始終想要撕爛衣服、踩壞洋娃娃,而且總是被人騷擾,還被說成「黑猩猩」或「穴居婦女」。大衛.瑞默爾備受折磨的故事被發表在 1997 年的一篇學術文章中,2000 年還出版了一本相關書籍,大程度地扭轉了「先天╱後天」論辯中的焦點,至少在大腦性別這塊領域是如此。
多樣化性別選項,讓人勇敢界定真正的自己
當時逐漸廣為接受的觀點認定性別天生,而且在出生前就已決定,但瑞默爾的案例無法解釋性解剖學與性別認同之間的落差。其實瑞默爾的處境讓許多細節更難被理解。1953 年,曾為美國大兵的喬治.約振森(George Jorgensen)從歐洲以克莉絲汀.約振森(Christine Jorgensen)的身分回到美國,他是首先接受性別重建手術的美國人,不過當時出生為男性者想變成女性並沒有被視為醫療問題,而是精神問題,因此,大眾會被給予這些人一些聳動的稱謂,像是「性倒錯者」、「類陰陽人」或「性調包怪」。
到了 1970 年代,英國作家珍.莫里斯(Jan Morris)和網球選手瑞妮.理察斯(Renee Richards)由男性變性為女性,不但出了暢銷書還登上主流媒體頭條,但這些現在被稱為跨性別者的人畢竟還是邊緣人、自然的偏查產品,或者科學上無法解釋的存在。
直到最近十年,性別才逐漸被視為一個光譜,人們並不一定全然陽性或陰性,而是兩者的混合體 :舉例來說,男孩子的女生和女孩子氣的男生比比皆是。最近臉書和約會網站「OK邱比特」都在男性與女性之外加了一個自訂的性別選欄,其中包括「無性別」(agender)、「雙性別」(bigender)、「泛性別」(pangender)、「性別酷兒」(genderqueer)和「兩性」(androgyny)等十數個選項。
現在漸漸有「性別光譜」的意識,許多機構也開始讓人們依照自己的認同去選擇性別。圖/By Nick Youngson , CC BY-SA 3.0 @The Blue Diamond Gallery
首先採取非性別二元分類的大多是學術機構,全國許多學校都在校內資訊系統內增添了性別中立選項,因此,教授拿到學生名單時,上面會包括每位學生想被稱呼的代名詞資訊,包括「他」、「她」、「他們」,或是性別中立的「xe」、「xyr」和「xem」。
身心性別不一致,是揮之不去的折磨
但對於那些性解剖構造與心理認同不相符的人而言,並沒有所謂的「性心理中立」。他們或許同意性別是光譜,但也非常清楚自己落在光譜的什麼位置。紐約石溪大學的研究在 2015 年也證實了這點。
研究者找來 32 位 5~12 歲的孩童,他們全是來自支援系統良好家庭的跨性別者,也都仍未進入青春期,在問了他們一系列足以精確檢驗性別認同的問題之後──那是一種間接連結測驗,意圖估算受試者將男性與女性的概念與「我」及「非我」連結起來的速度──結果發現跨性別組(包含由男變女及由女變男兩者)和控制組的順性別孩童(也就是性解剖結構與性別認同相符者)的反應並無差別。
正是這種身體與心靈的不一致導致折磨人的身體疏離感,順性別者當然也有喜歡或不喜歡自己身體的分別,並試圖進行改變或加強,但他們不會否認自己的身體。
那是一種大多藏於潛意識的親密認知,所以跨性別者在面對身體自我的議題時,幾乎是清醒及呼吸的時時刻刻都感覺到真我被否定。對於這些人而言,身體和他們的自我認知相左,或者說跟他們認為自己該有的樣子相左。他們對於維持自己活在世上的載體感到疏離,但沒有任何心理諮商或行為制約能處理這種衝突,唯一的出路就是使身體與心靈一致。
擁抱自己的女孩
2008 年在德國,16 歲的金姆.佩卓斯(Kim Petras)經歷了性別重建手術,她和懷特一樣出生時為男性,但兩歲就開始熱愛芭比娃娃及穿洋裝,隨著時光流逝,金姆的家長都意識到兒子堅持自己是女生是有原因的,其中父親所說的話更呼應了凱莉從一開始看待懷特的方式:「我們把金姆視為一個女孩,而不是個問題。」
世界上許多人都不同意這句話強調的概念,甚至包括許多跨性別者家長與醫界專業人士。過去(現在也常是如此)許多家長總帶著自我認同為女性的兒子到處求醫,但最後只得知自己的孩子需要密集治療,或需要被送到精神醫學機構,但仍有其他人意識到,強迫這些孩子在不是自己的身體裡經歷青春期會帶來多大的傷害。
正因如此,金姆.佩卓斯的機長終於找了一位表示可以幫忙的醫生,他是伯恩德.梅耶伯格(Bernd Meyenburg),法蘭克福醫院大學(University of Frankfurt Hospital)認同障礙之孩童與青少年的精神科特別病患門診(Psychiatric Special Outpatient Clinic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Identity Disorders)院長,他告訴他們很少有小兒科醫生理解性別不安,也請他們想像一個女孩臉上長出鬍子、聲音變低沉或一個男孩長出胸部又有了月經會是什麼情況。
金姆.佩卓斯在 12 歲時開始了女性荷爾蒙治療。在德國,性別重建手術必須滿 18 歲才能進行,但金姆得到特殊豁免,並在 16 歲時成功完成療程。之後她的父親告訴媒體,「我以為自己會比妻子更難接受這件事,但金姆是個非常有說服力的女孩,她知道自己要什麼,也知道該怎麼達成目標。我以她成就的一切為榮,包括她如何完成這趟旅程,以及無論多難、多苦都要追求夢想的決心。」
金姆.佩卓斯是到目前為止全球最年輕的變性人。圖/By Tiitanium – Own work , CC BY-SA 4.0 , wikimedia commons
21 世紀開始之前,跨性別孩童無法在青春期之前採取行動,也無法推遲青春期,以爭取身體成為徹底男性或女性之前的寶貴時間,因此,所有性別重建手術都是在完全發育的男體或女體身上執行。跨性別者想將身體與心靈同步的深植慾望促使他們接受性別重建手術,但要是結果不如預期,此時必須付出的心理後果極具毀滅性,而且大多情況確實都是如此。
被身體囚困的運動記者
40 歲的麥克.潘納(Mike Penner)是《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 )的資深運動記者,2007 年 4 月 26 日,他固定刊出的週四專欄出現了一個驚人的標題:「過去的麥克,明日的克莉絲汀。」文章的頭四段非常驚心動魄,甚至可說史無前例:
在時報的運動部門工作了 23 年,我扮演過各種角色,擁有過各種頭銜:網球賽寫手、安納罕天使隊專屬記者、奧運賽寫手、雜文家、運動媒體評論員、國家美式橄欖球聯盟專欄作家,最近則是時報「晨間簡報」的推手。
但從今天開始,我即將休假幾個禮拜,之後將帶著全新的生命回到崗位。
以克莉絲汀的身分。
我是一名跨性別運動寫作者。我花費了超過 40 年、無止盡的淚水及數百小時探索靈魂深處的治療,才終於鼓起勇氣打下這些文字。我知道許多讀者、同事和朋友讀到這裡一定非常震驚。
他們確實很震驚,但潘納心意已決,也選好「克莉絲汀.丹倪爾」作為新名字。之所以選擇「克莉絲汀」是為了向跨性別先鋒克莉絲汀.約振森(Christine Jorgensen)致敬,「丹倪爾」則是他原本的中間名。接下來就是為期 31 個月的狂喜、輿論稱讚、私生活挑戰、憂鬱,但最後終究還是性別重建回男性。潘納身高 190 公分,肩膀寬闊,聲音低沉,面對身邊所有人時總隱藏自己的性別不安,包括他的妻子。雖然公開自己的決定在心理上是一種解放,但也讓他失去了婚姻,而以女性身分過活也非常困難。
雖然獲得了許多支持,克莉絲汀的生活仍過得十分辛苦。圖/deadspin
第一個徵兆出現在他宣布變性後數週,她出席了英國足球明星貝克漢在洛杉磯的記者會,那是潘納首次以丹倪爾的新身分出席體育活動,之後她將這段經驗寫在部落格上:
他(貝克漢)穿著一身銀灰色的巴寶莉(Burberry)西裝抵達,身旁圍滿助理及支持者。我穿著羅斯(Ross)的金色調上衣及埃姆斯(Ames)的多彩佩斯利圖樣裙子出席,腳上穿著愛柔仕(Aerosoles)的開趾高跟鞋,身邊一個人都沒有。
另外一位出席的記者決定在自己的部落格上提到克莉絲汀:
我實在不想指指點點,但克莉絲汀實在不是個有吸引力的女人。她看起來就像穿著洋裝的男人,真的,就算有人曾被那些資深變裝癖唬過去,但今天只要注意看她的人都不可能受騙。或許這樣說很殘酷,但那個空間內有人出生就是女性,靈魂也是女性,而她們和克莉絲汀之間的差異在我看來實在太大了。我們簡直像在配合某人的角色扮演遊戲。
對丹倪爾來說,這一切都太殘酷、太傷人了,他攝取女性荷爾蒙、化妝、戴假髮、著女裝,但外表就各方面而言仍不幸地就是麥克.潘納。丹倪爾同意接受《浮華世界》(Vanity Fair)的專訪,也安排了攝影,事後,攝影師試圖解釋過程如何成為一場災難,他向《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表示,自己努力想說出正確的話,但「面對一個看起來就像男人的人,你要怎麼說出『你是個美麗的女人』?」書寫這篇報導的記者也為這項說法背書,並表示,因為害怕丹倪爾因此出現自殺傾向,所以在攝影浩劫之後,他決定抽掉這篇訪談。
丹倪爾的妻子提出離婚申請,許多朋友也消失了,雖然她交了新朋友,也得到許多支持者,但輿論平息後,她發現自己孤身一人住在小公寓內,還失去了幾乎陪伴他整段成年生活的夥伴。
因為被憂鬱淹沒,丹倪爾停止攝取女性荷爾蒙,也疏遠了所有新舊朋友。她覺得自己作為女性失敗了,並在寂寞的折磨下決定變回男性,甚至在《洛杉磯時報》的專欄作家姓名也改回了麥克.潘納。因此,2009 年 11 月 27 日,穿著藍色襯衫、黑色牛仔褲和黑白愛迪達球鞋自殺的是麥克.潘納。在小公寓地下車庫內那台 1997年分的豐田凱美瑞車中,他因為一氧化碳中毒而死。
本文摘自《變身妮可:不一樣又如何?跨性別女孩與她家庭的成長之路 》,時報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