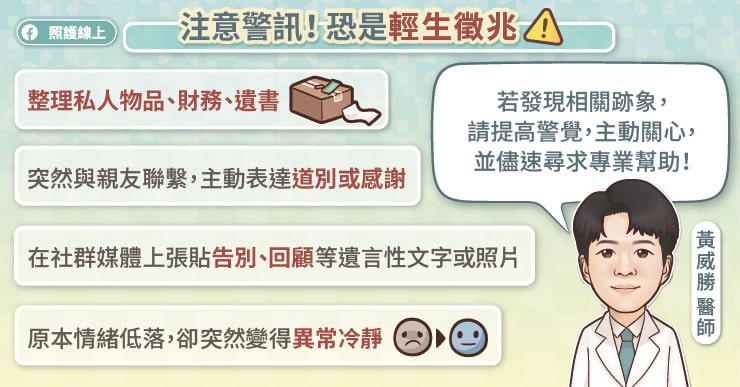- 作者/艾德華.布爾摩 (Edward Bullmore);譯者/高子梅
- 編按:文末寫到的 P 太太為類風濕性關節炎患者,也被作者診斷有憂鬱症的症狀。
在醫學上,憂鬱症比發炎還要古老。我們到羅馬時代才知道發炎的基本病徵,但古希臘時代就已經知道「憂鬱」(melancholia)這回事了。

大約西元前 400 年,在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門下的醫師就意識到憂鬱的兩個面向,我們現在稱作情緒和認知。一方面,他們看到了靈魂的痛苦,拉丁文是 angor animi,這種痛苦會透過恐懼、消沉、悲傷和鬱悶等方式來表現。
另一方面,則是悲觀又不切實際的傾向,拉丁文是 cogitatione defixus,就像古羅馬醫生蓋倫(Galen)的病人「認為自己變成了蝸牛,一定得躲開其他人,身上的殼才不會被踩扁。還有人為肩上扛著世界的神阿特拉斯(Atlas)擔心,想像他可能會愈來愈疲憊,最後消失不見」。
令人憂鬱的黑膽汁
在當時,這些情緒和認知上的症狀被認為是生理毛病,也就是身體功能異常。例如,憂鬱是黑膽汁在脾臟裡累積過多造成的。
根據希波克拉底學派的生理學,黑膽汁是四種體液(humours)之一。這四種體液掌控了病人性格、容不容易生病,以及對治療的反應程度等眾多面向。

黑膽汁、黃膽汁、黏液和血液是體內循環的基本體液。它們彼此間的平衡為臨床上的疾病病徵提供了診斷的解釋。比如說
- 黏液過多會使人變得冷漠,造成風濕和胸腔方面的疾病。
- 黃膽汁過多使人易怒,比較容易出現肝臟問題。
- 血液過多雖會讓人變得樂觀,但可能出現心臟疾病。
- 黑膽汁過多則會讓人憂鬱。
當時的抗憂鬱療法利用食療、運動、通便、放血來減弱黑膽汁所帶來的憂傷,重新平衡體液。
這些古老的觀念如今看來似乎有點可笑,因為我們知道沒有所謂黑膽汁這種東西,但這套理論主宰了歐洲醫學很長一段時間。英格蘭的醫師在 1850 年代以前,仍然普遍遵循希波克拉底學派的傳統。
鞭打刑罰治療憂鬱症,神學也有一套?
對憂鬱症患者來說,用希氏療法來治病儘管不太對症下藥,但至少是從生理學的角度出發,比基於神學的治療好得多。例如,塞爾蘇斯雖然也是古時候的醫師,但他對憂鬱症的看法不屬於希波克拉底學派。
他跟許多之前或之後的人一樣,認為憂鬱症是遭惡魔附身的鐵證,是惡靈俘虜了病人的靈魂,是對曾經做錯事或敗德的病人的懲罰。他建議的療法都相對嚴厲,包括驅魔儀式、鞭打、火刑、單獨監禁,或者用鐵鍊、手銬、腳鐐來限制行動。

從早期到整個中世紀,再到十八世紀的獵巫,無以數計的憂鬱症患者遭處以極刑,人們偏執地認為他們身體無礙,而是靈魂著了魔。
醫學界的新時代:身體機械論
在 1850 年後,醫學界的機械革命(兩百年前笛卡兒一針見血地預告)開始佔盡上風,取代了希波克拉底學派。(醫學的改革腳步總是慢很多。)只不過一直要等到 1950 年代,在笛卡兒之前或二元論之前的古代醫學理論(無論心理還是生理症狀都採同一套致病原因或因子,以體液解釋)才徹底瓦解,由身體機械論的醫學取而代之。

如今,希波克拉底學派的詞彙僅剩一點留在現代的醫學字典裡。melancholia 是目前為止精神科醫師仍然會使用的字,但它指的不再是黑膽汁,而是一種診斷名稱,更正式的說法是「鬱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簡稱 MDD)。
醫學院學生學到的發炎病徵從古時候到現在都一樣,而現代憂鬱症的症狀也跟兩千年前被診斷成憂鬱症的症狀沒什麼差別。只是發炎的典型特徵已經由全新的免疫科學深入地解析,但憂鬱症的臨床症狀卻沒有同等機械式的了解。
二元論讓憂鬱症只屬「心理」疾病
美國精神醫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出版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第五版(簡稱 DSM-5),以勾選清單的方式診斷鬱症,裡頭羅列的症狀連古羅馬醫師蓋倫也會同意,包括缺乏快感(喪失樂趣)和厭食(食欲下降)。

如果一個病人有兩個星期以上、兩年以下的時間,幾乎每天都處於悲傷或開心不起來的狀態,並符合清單上五種症狀的其中四種,就能證明這位病人患有鬱症。DSM 的編纂委員會是由幾位知名的精神科醫師組成,他們制定了這套檢測標準。
檢測過程中不需要血液檢查或身體檢查,也不需要做 X光或 fMRI 掃描。根據 DSM-5 的診斷統計,我們不需要從人體取得任何資訊來幫助我們判別鬱症。事實上,如果血液檢查或 X光顯示病人可能有身體方面的疾病,鬱症的診斷結果就不算數。
照 DSM-5 的規定,如果症狀可能「因另一種疾病的生理作用所造成」,就不算是鬱症。
所以奇怪的是,P 太太可能沒有鬱症。雖然她符合 DSM-5 清單上的所有症狀,但是她的類風溼性關節炎會把鬱症的診斷結果完全否定掉。在二元論的二分法下,憂鬱症被官方孤立在心理那一邊,就像發炎在傳統上被認定在生理那一邊,道理一樣。
——本書摘自《終結憂鬱症:憂鬱症治療大突破》,2020 年 2 月,如果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