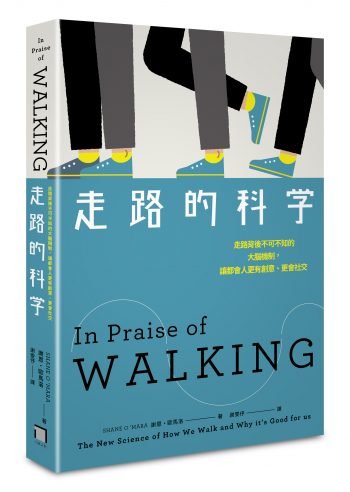- 作者/謝恩・歐馬洛(Shane O’mara);譯者/謝雯伃
我們是如何走到任何地方的?
常識告訴我們,這是走路搭配視覺功能以及動作功能的結果;不過,這忽略了一個明顯事實,那就是盲人(包括天生眼盲者)以及視障人士也能朝向特定目的與方向行走;他們可以在看不見空間的情況下,於複雜的三維空間中確定方向。他們可以在複雜環境中找到自己的路,也能找到路回到起點。至於那些視力沒問題的人,矇起眼睛也能做到這些事。
不靠視覺,我們還能到處走透透嗎?
在我上班的路上,我常遇見視障人士(通常拿著拐杖)在都柏林市中心搭公車或火車。我總是對他們心懷敬畏。視障者是如何在幾乎沒有或完全沒有視力且最少科技輔助下,完成複雜的旅程?

人行道與馬路交接處低一階的地面、修整過的行走地面,以及過馬路時燈號發出的提醒聲音,都是有用的環境信號。但我們還是需要對視力正常者以及視障者都進行精細實驗,才能完整知道這種不仰賴視覺的找路方式是怎麼發生的。
這些實驗涉及讓視力正常者矇上眼睛,走一條複雜的路徑,然後要求他返回起點;或是對他有更多要求,要他沿著特定路徑回到起點。
有時還會加入讓實驗變得更複雜的元素,包括來自四面八方的聲音、腳下地面的改變、擾亂前庭系統的身體旋轉等等。其中,最後一個可能最關鍵,因為失去前庭系統提供的穩定感以及方向感,對於我們簡單的尋找起點任務來說有著毀滅性的影響。我們會被我們對空間的感覺欺騙,這本質上又會影響我們的視覺。

事實上,對大腦來說,視覺只是我們理解空間的其中一種感官罷了——雖是重要的一種,但也只是其中一種。
我們知道這點,是因為不管我們對於環境熟不熟悉,也都能在黑暗中找到路。這種空間感(稱為「認知地圖」)是一種「沉默感官」:絕大部分是在我們沒察覺的情況下建構的,我們只會在它不管用時才意識到它。
視覺不必然是你選擇方向時的依據
數十年來,為數不少的重要研究針對一出生就眼盲以及後天眼盲病人的空間感(認知地圖)進行研究。這些研究將他們在行走任務上的表現,與同齡矇眼正常視力控制組的表現做比較。
他們使用路徑積分任務來檢驗,是否視力在動作為基礎的正常空間能力上為必要條件;參與者被要求沿著特定路徑或軌道行走,接著要走原路回到起點,或是找一條最短路徑回去。

如果我們相信視覺在發展正常空間能力上是必要條件,那麼我們可能會預測視力正常者會比那些出生後才在某個時間點失去視力的人(中途失明者)表現的更好。而中途失明者也應該比那些先天失明者表現的更好。
這三組人每一組的視覺世界經驗都不同,從視力正常組的完全經驗、後天失明組的部分以及歷史性經驗,到先天失明組的一點經驗也沒有。
在一項特別具啟發性的研究中,這三組人分別進行了一系列實驗,參與者被要求生產、重製或估算僅包含單次轉身的最短行走路徑。在更複雜的實驗中,參與者行走在多段路徑上,接著必須沿原路返回、找出回到起點的捷徑,或是以其他物件的位置做為參照地標,指出某個地點的所在地。
令人震驚的結果是,學習在擴展的三維空間中行走以及確定方向,並不需要正常的視力。
整體而言,三組成員在簡單任務中的表現大致相等,無論是矇眼正常視力組、後天失明組或先天失明組,所有參與者都能以相似程度走完被要求的簡短路徑、重新順原路走一次或是預測路徑。
至於更複雜的任務,所有組別也都表現得差不多。先天失明者可能表現最差,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視障者以及正常視力者的表現卻有一致性。

實驗也闡明了另一點,那就是要建立可用的認知地圖,必須要對空間世界擁有豐富的經驗。
視覺可能主導了我們對空間的感覺,但實際上我們的空間感是建立在我們於這世界行走的經驗,很大程度上獨立於我們與這世界互動的任何一種特定感官。
我們的空間感有點像我們的視覺、聽覺或動作感,但與其他感官相比,它更抽象也較不直接,因為它基本上建構在其他感官提供的輸入上。它提供了我們在這世界上移動的各種可能性地圖,讓你即刻知道當你前進時「你需要什麼以及要前往哪裡」。
——本文摘自《走路的科學》,2019 年 9 月,八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