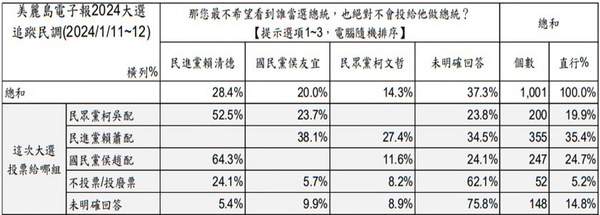明天(1/16)就要選舉了,為什麼很多一開始說不要抹黑對方的候選人,自己卻變成抹黑別人的人了呢(例如2008美國總統的選舉)[1]?既然從很早以前就有人在倡導不要再打負面選戰,可是為什麼儘管是到了今天,負面選戰卻還是沒有「絕種」呢?
負面訊息影響大
其中一個可能的答案是,因為抹黑真的有用。抹黑和造謠究竟能不能夠改變選民的支持度,其實也就是社會心理學當中研究「態度改變」(attitude and attitude change)的議題[2]。研究顯示,負面的訊息遠比正面的訊息更容易讓人家記得,甚至同樣的事情,用負面的方式說也比用正面的方式說來得影響力大[3]。
我們在這邊做一個簡單的實驗,請讀一遍下面兩個人的人格特質描述,然後抬頭看看天空想一想,你比較喜歡哪一個人:
- 安安:認真、傾聽、積極、用心、貪污。
- 熊熊:認真、傾聽。
—–(防雷線,抬頭看看天空想想,你比較喜歡熊熊還是安安)——
發現了嗎,即使熊熊只有兩個正面的特質(你甚至不知道熊熊是不是有其他的負面特徵),你還是會比較愛他,而比較不愛安安,因為他一個貪污的效果就吃掉其他的正面特質。這就是為什麼大家往往喜歡用負面訊息來抹黑敵方陣營的對手,因為一個墨魚彈炸到對方身上的效果,遠遠勝過自己端出好幾盤政策牛肉。

選前之夜最重要:新近效果
那麼,為什麼總是要在選舉之前的幾天才開始使出烏賊彈攻擊呢?同樣再來玩一個簡單的遊戲,你比較喜歡下面哪一個人?
- 安安是認真的人,做事踏實,雖然有些時候比較膽小,但肯努力、肯打拼、更為國家和人民的未來盡一份心力。
- 熊熊是個認真的人,做事踏實,而且肯努力、肯為國家的未來打拼,也願意替人民進一份心力,只可惜有些時候比較膽小。
—–(防雷線,抬頭看看天空想想,你比較喜歡熊熊還是安安)——
你是不是覺得熊熊比較弱?可是兩個候選人提供的訊息明明是一樣的啊,怎麼會這樣?發現了嗎?選前才轟炸負面訊息,是因為「新近效果」(recency effect)──相較於選戰中期的負面訊息,我們往往對最近才發生的事情記得比較清楚[4]。更多的時候,「先負後正」反而會讓人有好印象[5],畢竟誰無父母,誰無屁股阿!換句話說,如果你的子彈只有一發,最好的攻擊時間點就是選舉前的這幾天,尤其如果訊息是訴諸恐懼(支持OO就是支持死刑)[3, 6],對於不太常思考只愛用直覺投票的人來說<1>,效果更為明顯。
如果有些局勢已經無法挽回:初始效果與團體極化
當然,選前的抹黑並不是每次都有用,而且有可能搞得一身腥。奇怪了,不是說負面訊息影響多,而且新近效果威力很好很強大嗎?
其實這些效果都有一些限制——當你的態度還很不明確的、搖搖擺擺不知道要支持誰的時候,的確很容易收到這些訊息影響;但如果你一開始就已經篤定要支持某一個候選人(初始效果,primary effect)[7, 8],甚至已經到他的競選總部幫忙、到他的臉書按讚(反串的除外)、那麼你投入的這些時間和精力,就會變成你的防禦力。當你唾棄的候選人又丟出炸彈來找你支持的候選人的時候,你有兩個可能仍然還會誓死支持護衛你的候選人:
- 你對自己支持的候選人有很多的了解(包括他的優點和缺點),甚至比黑函還要了解,知道敵方陣營的「抹黑」只是部分的事實,或者根本不是事實。
- 你已經在這個你所支持的候選人身上花了太多的時間和心力了,如果這個時候下線中離,或者是改變態度去支持地方的候選人,一定會讓你感覺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9],所以就算對方說的是事實,你也會塢起耳朵說:我不聽!我不聽!
最後,如果兩方陣營口水戰已經是常態,那麼通常你就會選一邊站,然後透過團體極化的過程(group polarization),更相信自己陣營所說的,然後唾棄對方陣營的意見(你看又是那些藍吱吱/綠疽疽在搞分裂了!)透過臉書的篩選過程,我們更容易看到看自己以前相同或是價值觀相似的推文,這樣的團體極化過程也會比以往更加明顯。

分裂是常態的世界
總而言之,抹黑到底有沒有用呢?端看收到黑函或是訊息的人對於原本候選人的支持程度,以及負面訊息的強度多寡而定,而且也和接收者的性別<2>、訊息傳遞方式有關[5]。抹黑或許對於舉棋不定的中間選民有一部分的效果,但對於已經誓死支持某一個陣營的鐵票選民來說,可能不但沒有辦法搶到票,還會強化兩個陣營之間的對立和分裂。
我覺得,我們似乎活在一個「分裂是常態」的社會,因為「你團/我團」(us-them divide)的思考方式,很容易讓我們在其中一團找到安頓的感覺。有些人厭惡這種分裂的狀況,於是跳脫出來乾脆不投票、不想要淌這場渾水,這樣的好處是,不論到時候是誰當選,做得不好,自己總有理由可以去罵上幾句,但是他們卻忘記了,在決定了不做出任何選擇的同時,其實就是已經做出了選擇——換句話說,如果你不去投票又愛在選後罵,某個程度上你也罵到了,一部分的自己。
註解
<1>深思可能性模式(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當你不太關心,或是覺得事情跟你沒有太大關係、或缺乏投入動機的時候(阿~便選選就好了啦!反正選誰都一樣爛阿!)就會走認知的邊緣途徑(peripheral route),更容易受到正或負面訊息的影響[10]。
<2>若根據訊息網站口耳相傳的研究,「女性訊息接受者對於負向訊息之新近效果顯著性優於負向訊息之初始效果,男性則沒有顯著差異」[11]
<3>刊首感謝 陸子鈞協助P圖,原圖連結
<4>本文多以態度改變理論來討論抹黑的有效性,但態度改變的研究其實繁雜、影響因素又多,所以尚須考慮到許多其他因素的限制。至於實際的「政治抹黑實驗」操作,也還有賴後人驗證之。
延伸閱讀
- 汪萬里, 2008年美國總統選舉中負面選戰所帶來的影響. 選舉評論, 2010(8): p. 47-66.
- Eiser, J.R., Social Psychology: Attitudes, Cognition and Social Behaviour. 198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周穆謙 and 林以容, 癌症篩檢宣導海報之說服效果探討. 資訊傳播研究, 2015. 6(1): p. 1-27.
- Miller, N. and D.T. Campbell, Recency and primacy in persuasion as a function of the timing of speeches and measurements. Th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59. 59(1): p. 1.
- 徐淑如, 董和昇, and 柳雅婷, 網路論壇口碑強度、雙面訊息與口碑順序對說服效果之影響-產品涉入之干擾效應. 電子商務學報, 2011. 13(1): p. 135-167.
- 汪志堅, 楊運秀, and 李明倩, 拒菸廣告的恐懼訴求對年輕族群的說服效果:調控焦點與訊息框架之影響. 臺灣公共衛生雜誌, 2013. 32(1): p. 62-74.
- Hogarth, R.M. and H.J. Einhorn, Order effects in belief updating: The belief-adjustment model. Cognitive psychology, 1992. 24(1): p. 1-55.
- Murdock Jr, B.B., The serial position effect of free recall.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962. 64(5): p. 482.
- Festinger, L., Cognitive Dissonance. Scientific American, 1962. 207(4): p. 93-&.
- Petty, R.E. and J.T. Cacioppo, The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of persuasion. 1986: Springer.
- 李威龍, 留淑芳, and 劉明宗, 網路口耳相傳訊息數量、訊息方向暨性別對訊息說服效果之影響. 行銷科學學報, 2005. 1(2): p. 165-201.